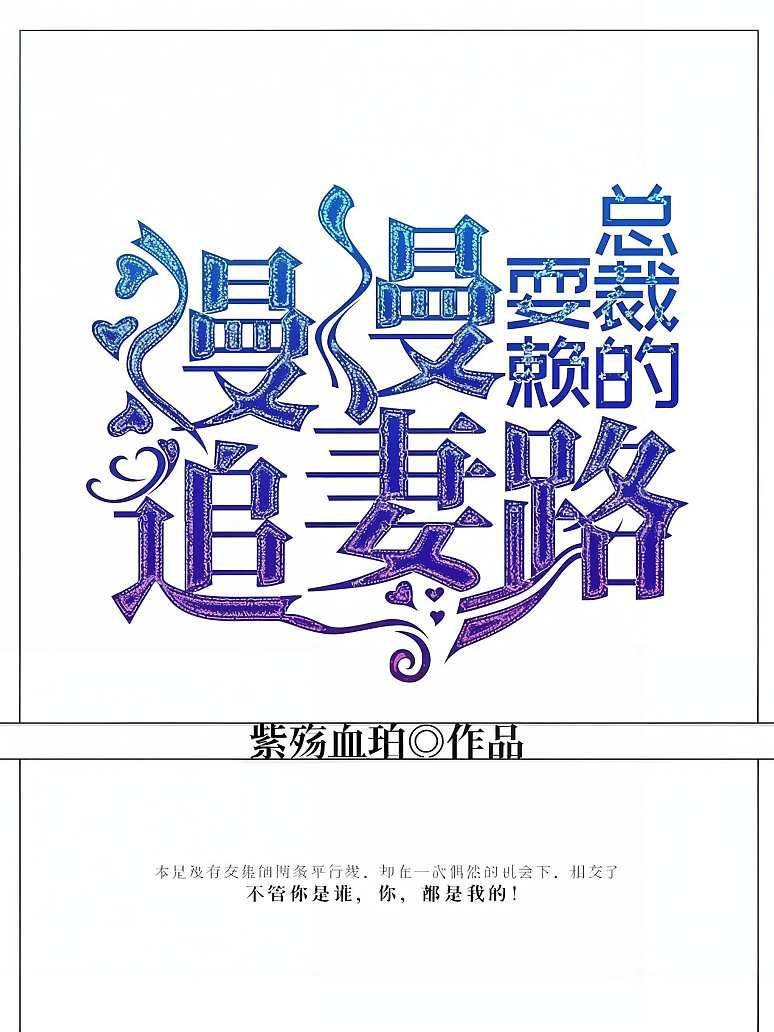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成了霸總的心尖寵》 第28章
很看到賀霖的溫,基本沒有吧。
或者說有,但是這點溫一直屬于詩。
沈伊也從來沒有想過,他也會溫地問這樣那樣。
沈伊一時有點不好意思,回道:“我一時沒想到,沒事的,哥哥。”
賀霖挑了挑眉,子靠了回去,道:“去拿藥箱過來,傷口再理一下。”
一想到那酒的疼痛,沈伊反地搖頭。
賀霖:“嗯?”
沈伊:“……好的,我去。”
說完就不不愿地轉,走之前手想拿劇本,賀霖的指尖繼續著劇本,淡淡地道:“拿了藥箱回來后上好藥再來拿劇本。”
厲害啊我的哥。
沈伊的心思全被他看了。
出了書房,就看到詩的房門開了,也走了出來,兩個人一面,立即又是一種尷尬的說不上來的氣氛,沈伊喊道:“姐姐。”
詩笑了下:“嗯,手還沒好?”
“沒呢,再一會藥就好了。”沈伊應道,然后就下樓,詩也跟著下,這會詩倒是主地問沈伊:“最近學校里排戲?”
沈伊愣了下,樓梯上只有們兩個人,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后面,詩自然地問了,沈伊也不好不回答,應:“是啊。”
詩笑著道:“你們排什麼啊?”
“雷雨。”
“等上了大二,排的戲會更難。”
“噢,這樣。”
尬兩分鐘去掉半條命,終于到達一樓,沈伊立即去拿醫藥箱,詩著頭發去了影映廳。
拿了醫藥箱后,沈伊往影映廳看一眼,詩一個人坐在跟前,熒幕上是一部電影,沈伊看一眼就上樓。
再推開書房門,賀霖偏頭正在看電腦。
沈伊進去,他抬眼,后站起來,往沙發走去,沈伊只能乖乖地拎著醫藥箱走過去,他坐下,沈伊遲疑了下,坐在他旁邊的沙發,賀霖偏頭看一眼,“坐那麼遠,隔空上藥?”
Advertisement
沈伊無奈,坐過去時嘀咕:“你要是有這個本事也好的。”
賀霖挑眉,低聲問:“你說什麼?”
沈伊立即閉,推著醫藥箱給他。
賀霖打開,低頭拿起里面的藥,說道:“把手抬起來,過來。”
沈伊只能乖乖地過去,賀霖看著眼前白皙的手腕,手腕小得他一手指可以折斷,他抬手,住,手腕和得很,一就能碎似的,他上藥,沈伊一直吸氣,賀霖看一眼,“我還沒。”
沈伊睜眼,道:“我先吸著。”
賀霖挑眉。
這次沒有第一次那麼痛了,等上完了藥,沈伊發現被賀霖握著的地方都有點發紅了,可見他握得有點用力,收回手,用手了下那個紅圈,賀霖合上醫藥箱,視線在的手腕上掃了一圈,眼眸微深。
沈伊看著這位哥哥的側臉,其實有點好奇他對詩是什麼看法。
現在什麼打算?
不過這都是他的事,沈伊自然不會多。
這時賀霖的手機正好閃了一條微信出來,沈伊不經意一掃,發微信的人正好是詩。
容自然是看不到的,沈伊起,道:“哥,我先回房了。”
賀霖將醫藥箱推給:“嗯。”
沈伊拎走醫藥箱,跑過去拿走自己的劇本,后就出了書房。
房門關上,賀霖手杵在膝蓋上,指尖點開微信。
詩:【哥,來看電影嗎?我們好久沒一起看電影了。】
賀霖:【不了,還有工作沒做,你自己看,也早點睡。】
詩:【哦。】
賀霖站起,書房的電話就響了,他靠在書桌上,偏頭拿起來,來電是賀崢。
賀崢:“下來我書房。”
賀霖:“好。”
他掛了電話,下樓。
賀崢站在窗邊,聽見兒子進門,微微側頭,賀霖關上門,父子倆對視了一會,這些年,兩個人既是父子也像兄弟,賀崢婚太早,賀霖太早懂事,十六歲就去軍校。
Advertisement
在那戰場上幾番喪命。
賀崢也不是沒有怕過,但是男兒志在四方,賀霖想當兵,賀崢沒理由反對,他點了點書桌,道:“你該退伍了吧?”
賀霖靠在父親的書桌,把玩了下地球儀,道:“還沒定。”
賀崢:“我不反對你繼續往上,但是你的安全要。”
賀霖這麼年輕就擁有軍功,都是拿命換來的,賀家也不是特別在乎這些,可是孩子有出息嘛,總是好的。
賀霖:“到時再看。”
賀崢點點頭,后道:“詩……”
賀霖這會就沒吭聲了,等著賀崢繼續往下,賀崢繞著桌子,也來到賀霖側,目落在兒子的指尖上,賀崢道:“我本來好幾個設想,第一詩進戶口,為真正的賀家人,第二嫁給你,為賀家的媳婦,第三嫁出去,我們為尋一門好的夫家,第四他回來了。”
“但是現在,第一被掐斷,第四還是一個未知數,那麼只有第二跟第三,我偏向第二。”
說完這話,賀崢直接停頓。
賀霖:“嫁給我,不可能。”
“爸,我對從來就沒過心思,我的潛意思里詩就已經是我們賀家人了,如果我遭遇不測,是第一個繼承人。”
這樣的心思下,怎麼產生得了?
賀崢看著兒子:“也許你從今天開始,把當可以娶回家的對象,你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待,會發現適合當你的妻子。”
賀霖偏頭看賀崢,眉眼間帶著不贊同:“不想勉強。”
“這怎麼能是勉強,你只是沒把當一個人。”
賀霖沉默半響,道:“你糊涂了。”
賀崢頓了下,后嘆口氣。
賀霖道:“我分得清對妹妹跟對人的。”
Advertisement
賀崢擰眉:“你的意思是你有過這樣的?”
賀霖推開地球儀,站直了子,從書桌上拿了一煙,點燃了叼上,道:“有啊,想吻,想囚,這算不算?”
賀崢很詫異,半天沒有說話。
……
只是趕回來幫詩過一個生日,第二天沈伊還是要回學校的,一大早收拾了書包要走,詩也從樓上下來,說要一起去學校,沈伊看了眼站在側的詩,頓了頓,想著一起去就一起去。
結果送們去的,還是賀霖。
黑SUV開到家門口,沈伊立即拉了后座的車門上去,詩看了眼沈伊,選擇了副駕駛。
今天還有點綿綿小雪,路面一早就掃過了,賀霖調轉車頭,一路開出去。
以往詩跟賀霖在一個空間,一般詩都蠻有話講的,會喋喋不休地跟賀霖聊一些話,賀霖大多數應得很,但會聽,今天詩不吭聲,賀霖自然也不會主吭聲。
沈伊在后座撓了撓臉,撓了撓頭發,向來在這種場合都是安靜的那一個。
但是今天尤其尷尬。
不過自己尷尬而已,賀霖神清淡,完全沒有一點影響,看這個樣子,當真有點冷。
也是,上輩子,詩應該也是告過白的,后期賀霖因為工作的關系,在外面置辦了公寓,回來時間就比較,至于詩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常年到飛,基本也很回家。
沈伊大概也只知道這些,的不太清楚。
車子沉默地到達學校門口,賀霖看沈伊一眼,囑咐道:“手腕別再水了。”
沈伊從后視鏡跟他對視,點點頭:“知道了。”
詩側頭看賀霖,嗓音低低:“哥哥,我進去了。”
“嗯。”
Advertisement
副駕駛的車門跟后座的車門一同打開,詩下了車,沈伊也跟著下車,姐妹倆走的方向是一樣的,學校門口正好也停下一輛黑的保姆車,停了一會車門打開,秦晟笑著喊道:“沈伊。”
沈伊正想著走快一點,不跟詩一起,就聽到秦晟的喊聲,轉頭一看,笑了起來,沖秦晟揮手,結果腳下一,沈伊嚇了一跳就要當眾劈叉,秦晟驚到了立即加快腳步,沖這里來。
在沈伊劈叉之前,拉住沈伊的手,把拉了起來,沈伊踉蹌了幾下,秦晟小小地環了下的腰。
沈伊才站穩,并趕跟他道謝。
秦晟搖頭一笑,說:“沒事就好。”
沈伊低頭一看,地面上有結冰的一小塊地方,都沒鏟干凈。
好氣,就這麼一塊小結冰差點讓的子撕裂。
幸好今天穿的是子。
又激地說一聲:“謝謝你啊,秦晟,今天是六號啊,你不是說七號再來嗎?”
秦晟松開握著的手,笑了下:“忙完了就先過來幫你們排戲。”
“太謝謝你了,中午請你吃飯。”沈伊笑著眨眼,秦晟撓撓耳朵:“好呀。”
隨后兩個人結伴進了校園,走了沒多遠的詩上下看了下這兩個人的互,又看了眼那門外的那輛黑的SUV,這才跟著簇擁的同學,往大二的教學樓走去。
賀霖按在駕駛位車門的手輕輕地一個用力,砰地一聲。
關上了。
男人眼眸淡淡地看著校門口,沈伊那件黃的外套仍然格外顯眼,旁邊的那個男生的白外套,因走在一起而有些融似的。
他低頭點了煙,靜坐一會,這才啟車子,調轉出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98 章

那一夜,她帶走了江城首富的孩子
【萌寶+總裁+甜寵+雙潔】頂著私生子頭銜長大的南宮丞是一個冷漠陰鬱的男人,不婚主義,厭惡女人。 一次偶然的機會,沈茉染上了他的床,醒來后卻被他扔在一邊。 四年後。 沈茉染蛻變歸來,南宮丞把她堵在牆角,「原來那一夜,是你」 「你不是說了嘛,數字隨意填,忘了這一夜」 南宮丞不上當,「孩子呢,是不是我的?」 「孩子跟你無關」 恰此時,一個男孩兒跳出來,「放開我媽媽,」 旁邊還有熟悉的沈柒柒。
122.1萬字8 221877 -
完結55 章

蝕骨寵溺
《蝕骨寵溺》六年前,楚聽顏遇到了那個不可一世的狂妄少年—江肆沉。在她被欺負時,他會挺身而出,也會因為她隨口的一句話,跑遍整個湘城買她最喜歡吃的鳳梨酥,甚至為了能和她上一個大學,發奮學習。多年後,楚聽顏混跡成了一個娛樂圈十八線小明星,而她的前男友卻成了她新戲的投資方。空無一人的廊道里,高大的男人壓著她,指尖捏著她的下巴,嗓音暴戾沙啞,“當年為什麼要跟我分手?”楚聽顏緊咬紅唇:“沒有為什麼,江肆沉,當年是我對不起你,過去六年了,把那些事都忘了吧!"他嗤笑一聲,“楚聽顏,你未免太自信了,以爲我對你舊情難忘?”楚聽顏:“沒有最好!”酒局上,他故意給她施壓。“我覺得楚小姐不適合《盛夏餘年》的女3一角,王導,您說呢?”王導汗顏,不敢有任何意義,“江少說得對,楚小姐是不太適合。”楚聽顏:明顯是故意針對她。後來,爲了爭取角色,她被迫去討好江肆沉,甚至還失了身。他需要一個乖巧聽話的假女友應付家裏的催婚,偏偏找到了走投無路的她,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她同意了他提出的條件。
16萬字8 9241 -
完結286 章

寵妻攻略:墨太太又在撒嬌!
替姐姐嫁給一個變態狂,結果自盡了。重生回來,沒嫁給變態,但要嫁給殘廢?老天,這人設沒咋變啊,你玩我呢!!!嫁而死,虞清霜好不容易重生一回,人設沒咋變啊!未婚夫陰測測地盯著她:“我得了癌癥,活不過三個月。”虞清霜默:這婚可以結。等男人一翹辮子,她就升級為單身貴族,還有大把遺產可以繼承,劃算!N個日夜后,虞清霜怒了,“墨臨淵,你怎麼還沒死?”“小東西,要乖,我死了,誰護著你作天作地?” 【甜寵,必戳哦!】
53.5萬字8 22640 -
完結99 章

錯撩:厲太太日常虐夫
阮薇曾深愛厲斯奕,為了他,她甚至可以付出生命,可他只愛她的妹妹。
8.9萬字8 115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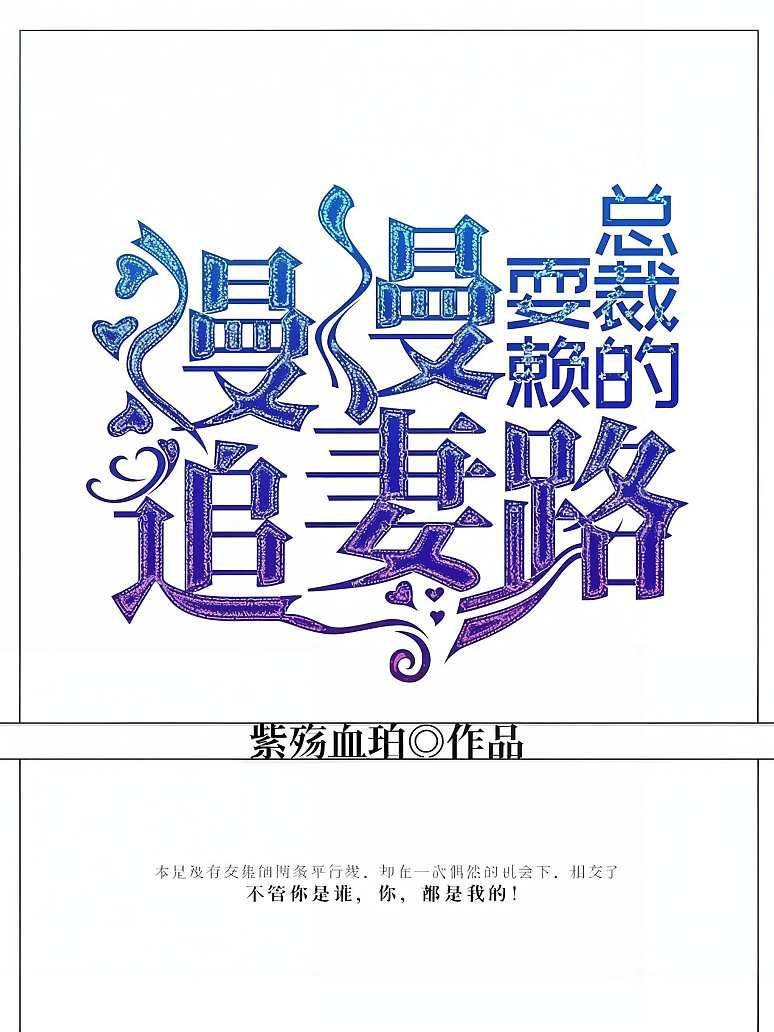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
完結318 章

插翅難逃:沈總的金絲雀只想跑路
新作品出爐,大家可以前往番茄小說閱讀我的作品哦,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你們的關注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會努力講好每個故事!
41.3萬字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