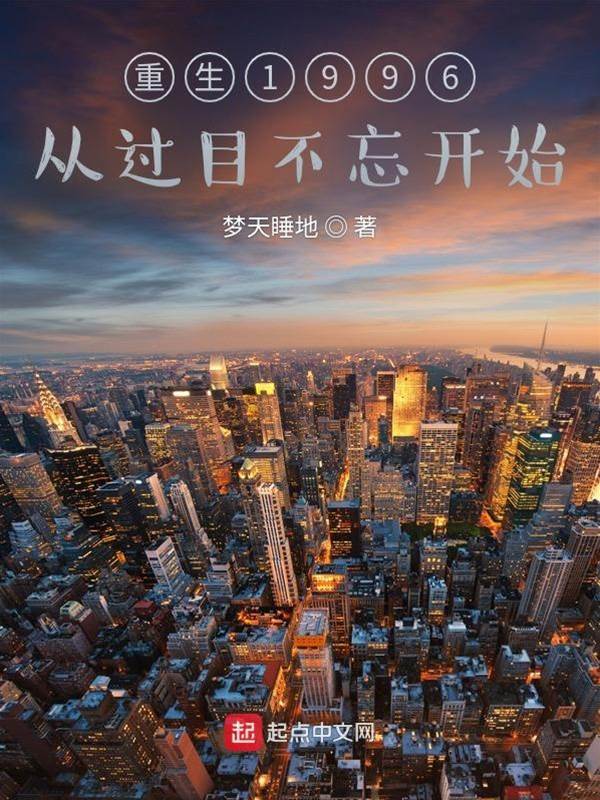《我全家都帶金手指》 第二百八十五章
秀花他們也不嫌棄冷,就好奇地站在路兩邊數啊,有多抬嫁妝,好幾十臺。
這娘家要有多富裕才能做到。
換咱家,除非給豬和牛塞進去能湊齊。
還從旁觀的百姓中聽聞,這才哪到哪。
限于品級,有些大戶人家,明明能給兒準備出幾百抬,卻不敢超額,那都是有定數的,只能往里面塞。
而與之相反是落魄的大戶人家,表面看起來熱鬧,里面有可能裝的稀松。還不如中等的富戶陪嫁。
以前,秀花們去哪里能了解到這些,沒想到剛進城就能聽聞接不到的八卦。
看了好一會兒熱鬧才隨著人群離開。打算將這場面記住,回村講給老姐妹們開開眼。
離開前,秀花輕拍了拍甜水的臉蛋,一咬牙,無比暢想道:“等俺們甜水嫁人,太姥姥也給你準備最至二十四臺嫁妝。”
朱興德心想:那必須的。
他剛才看到別人家嫁,聯想的也是甜水。
秀花又喜滋滋說道:“要讓甜水念書的,誰說娃認字是白花錢。回頭我讓你們里正爺爺想想辦法,擱咱游寒村弄個小學堂。讓甜水背著小包混在里面去識字。”
雖然沒見識過那些大戶人家的婚喪嫁娶流程,但是卻知道一個恒古不變的道理:
別小看人家嫁的好,人家除了有個好爹,自己也要有點兒本事。咱家現在還不能讓甜水學習琴棋書畫,但最起碼要認字吧。
……
一盞茶時間過后。
白玉蘭指著朱興德他們落腳的院子,讓娘別做夢了:“還想陪送幾十抬嫁妝呢?快醒醒,這才是現實。”
甜水東瞅瞅西道:“太姥姥,這里還不如咱家好。”
只看,城里的住,院落倒是大,就是房屋矮矮趴趴的,還全是草房泥墻,屋里很黑。
Advertisement
楊滿山陪同回來的,朱興德和左撇子他們直接去了鋪子。
聞言,滿山有些赧然道:“以前賃的那間房子好,鄰居大娘還能幫忙做飯,那一個胡同里住的也全是面人。但就在前幾日,人家把房子賣了,又是年下,不好找新房子,先搬來對付住。”
白玉蘭打聽問:“這個房子付了幾個月的租金。”
“仨月的,城里最要仨月。大姐夫說,等年后小妹夫能定下來去哪家書院,再定去哪里租房。想要離書院近,以免小妹夫再莫名招到點兒什麼,我們不能及時趕到。反正我們有車代步倒是不怕遠。”
白玉蘭聽完,心里只翻來覆去一句話,老頭子還讓買金豆子戴耳朵上。還買什麼呀?咋那麼心大,家里都沒有房子。
商業街上的酒鋪子是一口氣租了三年。
花出去不租金。
多虧著縣城那大鋪子是李知縣賞的,要不然家每日一睜眼就全是租金。這一天里要是沒賣出去十壇子酒,就是虧錢。
而孩子們的住又是租賃的,甭管好孬,也得買個房啊。
最好能將那間鋪子買下來,不用算計日日花出去多租金錢。
白玉蘭也知道,不是著急的事兒,家里還要蓋住房和酒坊,做買賣更要有活錢跟著,不能全花空。更不是家里人過日子節省就省出來的,需要多掙。
底子太差了,只能一點點置辦家業。
這功夫,白玉蘭倒是忽然理解羅婆子為什麼摳門了,因為正向滿山打聽:“就這破草房加個院子,府城一般賣多銀錢。”
“別看破,對方還要一百八十兩的。”
哎媽呀,白玉蘭在心里合計,這才是府城。
要是將來小姑爺去了京城,真要是有了那大造化留京,比照著這樣的破房子買,估麼也要至三四百兩。搞不好奔五百兩去了。
Advertisement
現在這銀錢水分大啊,自從朝廷頻繁和邊境打仗,早不像前些年一兩銀子能買不什。
就在這時,屋里傳出秀花哎呀一聲。
老太太差些摔個大前趴,那門牙就會掉了,是被小黑板給絆倒的。
秀花倒是沒后怕,看著板子上紙張上的字,還有那些自制的沙盤,很是欣的對后的滿山道:“這就對啦,你們空在認字啊?”
滿山告知,羅峻熙晚上有空就。用紙太浪費,他們就用沙盤和小木劃拉著學。連二柱子都會寫自個的名字、府城縣城的名字,有事、著急、回家、去鋪子等數十個字了。
“出息大發了”,秀花點點頭道:“你爹在縣里也沒閑著,現在六子也會寫簡單的字了。這回吉文去了縣里,吉文本就念了三年書,記賬沒問題,你爹才放心將縣里那一攤子給他們。”
“聽說,吉文是我們舅舅?”
秀花一擺手道:“啥也不用,我只是不想讓他我母親,讓改口我姨,你們往后喚他名字就行。”
楊滿山咽下:外婆,你二嫁那里又來一家。
他怕麻煩,還要回話。
想著老丈人跟著大姐夫已經去了鋪子,那一家子在鋪子后的存酒倉房里落腳,想必等老丈人回來時,外婆就能知道了。
恰巧白玉蘭召喚滿山,讓出來卸車,先將餃子包子等吃食,找個妥帖不招耗子的地方凍上。
與此同時,府城的花清釀鋪子里,左撇子果然在參觀。
邊參觀邊在心里對比,說實話,租金這麼貴,卻屬實不如縣城的酒鋪子又大又面。
但縣里的人,也不如城里顧客多。難怪寸土寸金。
你瞅瞅,烏央烏央的,外面三胖子和常喜就沒招消停,不停地接待顧客。
Advertisement
左撇子跟在大姑爺后,來到隔開的小間。
小間里,連搭個熱炕的地方都沒有,想午睡是不可能的。
只一張上鎖的桌子,大姑爺收錢放里面,一把木頭椅子,桌子上擺了一套茶,洗茶的,泡茶的,泡茶的杯碗很多。
左撇子:能想象出來,真泡起茶來,還顯得文雅的。
墻上著羅峻熙給寫的大字小字。
左撇子沒空細看,像是一套詞。最下面卡了羅峻熙的名。
桌子對面擺放兩把椅子,想必那是大客戶進來談訂單坐的位置。大婿會給泡點兒好茶喝。
再然后屋里就是一個爐子,爐子燒城里人賣的煤炭,上面坐著水壺。
要說屋里最打眼的,就是兩個供臺。
一個柜子上面,供著關二爺。
另一面挨著墻壁的柜子,供著……十二生肖。而且擺在最前面的是蛇、接下來說豬,之后是牛,那上面還煙霧繚繞的,可見天天上香。
“這個?”別致啊。
朱興德笑:“咱家不是靠野豬掙了點兒錢嘛,蛇也幫過大忙,現在又有了牛,我尋思一氣兒都給供上。”
左撇子又細看用泥出的,發現只有肚子上有名字,還是家里甜水最稀罕的那只,那不是死了嘛。小外孫以為埋葬了,其實被他岳母給挖出來烤著吃了。
“小妹夫特意寫的。”
左撇子搖頭,這些孩子大個人了,還淘氣。
而朱興德在左撇子參觀屋子時,已經拽過椅子坐在爐子邊,看起了朱老爺子給他的書信。
看到最后,給朱興德都氣笑了。
他這才知道,他大姨帶著一家子,啥活不干,貴客做派,在老丈人家吃吃喝喝七日。
要沒有他爺捎來的這封信,想必岳父岳母和外婆本不會特意告訴他。
Advertisement
“爹,我大姨們這副樣子,您怎麼沒說呢。您和我細學學。”
左撇子摘下棉帽子,不以為然的模樣擺擺手道:“其實沒啥,不就是親戚去了,吃點兒喝點兒嘛,多幾雙筷子的事兒,咱家現在又不是招待不起。我也是過后聽說的,們所求的,你外婆全沒應,就得了唄。你也不用生氣,誰家沒有幾個這樣的親屬。咱家算的了。”
左撇子真是這樣認為的。
他還覺得真的“”了呢。
本以為年前,小婿的那位嫁到外地的伯母和堂哥們,也會找到家里。卻沒想到,峻熙了秀才公,人家照樣還是沒找上門。
親家母羅婆子白準備了。
為啥這麼說呢。
他有幸聽過彩排,羅婆子認為自己說話不夠給力,殺傷力不夠大,就和他岳母一人扮演一方。
他岳母演“羅婆子”,羅婆子扮演羅峻熙的伯娘和堂哥找上門來套關系,然后羅母將他岳母頂回來的那些氣人的話,全部記住了。準備就緒,只欠東風,結果沒來。
朱興德將信合上,嗤了一聲。
得了,他心想:他也不用再細問了,以免家里人來了城里團聚,好的氣氛被破壞。
無非就是那幾件事唄,要麼想借錢,用從他這里借來的去掙自個的錢。要麼就是想手酒買賣,跟著一起掙錢。
朱興德打算不被這份人束縛。本就想過倒出空來,到了夏天最熱的時候,小稻也生完娃了,酒買賣也一般了,去看看姥姥。姥姥需要什麼藥材治病,他就給拿些,再給姥姥四季的裳都添上兩套,厚棉棉花多塞些。以免給吃給喝,給錢,兩個舅舅舅母會扣下,用不到姥姥上。
他沒忘記前些年,姥姥走那麼遠的路,帶干糧來看他。
姥姥要是長壽,他更會年年都去看一看老人,照著老人能用到的給添置,也是為死去的母親盡一份孝心。
甚至,朱興德在大姨一家沒找上門前,就已經打算在去看姥姥的時候,一并償還爹娘借錢的人。
怎麼還呢,他認為大姨一家子要是那種好樣的,見面親的,他倒不著急了。
畢竟人這輩子三窮三富過到老。大姨一家人,要是有天出現急事,要用到他幫忙或是用到錢,哪怕是需要借用很多銀錢,且還說不出哪日能還上這份銀錢了,沒事,只要他有,他明知道夠嗆能還上,也定會拿出來。幫忙就更是了,他一定想辦法。
這的是意。
可要不是那種好樣的,得,他就打算比照著利息,多給大姨按照年頭翻幾倍行吧,爺信里說了,他爹當年向大姨家借了二十兩銀,用了一個月就給了過去。二十兩銀的利錢,照二十年翻,他撐死了給買個五兩八兩的禮送上門,然后完事兒,往后這門親戚就算斷了。
朱興德想到這里,最心疼的是他媳婦。
小稻著大肚子,就算外婆和丈母娘從沒為他大姨給過小稻臉,小稻也要抬臉瞅著吧。怕外婆和娘生氣。
還要去安和伺候那一家子事多的呢。一天兩頓飯張羅一桌子飯菜就夠嗆。
聽說甜水還挨了揍,和那家孩子總打仗。
另外,還有什麼表妹!
朱興德琢磨以上彎彎繞繞,不過在瞬息間就想的通。連明年夏天去看尹氏,將“人禮”送到哪里都琢磨完了。
他要當著兩位舅舅和姥姥的面兒,將人給過去。到時不用別人幫忙宣揚,舅母們就會幫忙去外面酸上幾句,說他這人夠意思,給了大姨尹氏不好東西。
朱興德將爐子里的火了,添了些煤,站起來對左撇子道:“爹,您隨我去趟后院,我這里有一家子人要給您介紹。”
“誰呀?”
左撇子看到老岳母二嫁的兒子:“……”
他都無語了。
——
當李老二見到繼母秀花時,都激地哆嗦了,眼淚唰的一下就掉了下來。
惹得他十一歲的兒和六歲的兒子很是疑。
要知道家里最難的時候,他爹出去干活摔一傷回來都沒有哭過。
秀花也半張著,手上還沾著白面呢,回吃驚地向門口的漢子。
也認出來了。
可是眼前二嫁那家的兒子,怎麼造的比左里正還老相呢。
今日鋪子特意關的早。
誰問一聲,朱興德都高興地回答:“我外婆、爹娘,還有俺閨來啦,頭一天來,早些回去,家里包餃子等著吶。”
所以,此時不僅朱興德和羅峻熙、楊滿山他們全在,連著二柱子那些送酒的小子也回來了。
院子里停著一輛輛空牛車。只有到了每日夜間,這個不起眼的院落才顯得很有錢,牲口車一排排的。
大家站在院子里,正見證著屋里的認親儀式。
李老二兩口子帶著一對兒,跪在秀花面前,連磕仨頭。
秀花坐在上方穩穩地點頭。邊一左一右站著左撇子和白玉蘭。
秀花又讓李老二一家子起,給雙方介紹。
猜你喜歡
-
完結741 章

末世之獨寵女配
她是妖嬈傾城的重生女配,他是異世風光無限的暴虐魔君。 是巧合,是意外,或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重生的她,風華絕代,卻甘願戴上麵具做個啞巴,隻求低調生活保住小命。 穿越的他,狼狽不堪且雙目失明,還沒有異能? 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場又一場的追逐碰撞。 當絕美女配遇上魔君大人,故事又該如何改寫? 一句話簡介,這就是一個美若天仙但內心缺愛的絕美女子找到一個腹黑悶騷暴虐魔君來獨寵一世的故事! 從此末世都是背景,女主男主都是浮雲。 本文背景是末世,女主不小白不聖母,男主強大且神秘,一對一不np,坑品保障。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199萬字8 20083 -
完結1323 章

重生之我的1993
張一鳴的人生,終結在了男人四十一枝花的年齡。再睜眼竟回到三十年前。那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張一鳴將重來的人生過成了詩和遠方,財富和夢想,親情和愛情,他都要。
252萬字8 49810 -
完結3357 章
重生福妻有空間
“李金鳳,你爸不要你,你媽上趕著給我們做後媽,你就是個拖油瓶!”一覺醒來,李金鳳成了困難年代缺衣少穿的小可憐!前有冷漠後爸,後有七個不喜歡自己的哥哥、姐姐!好在有隨身空間,物資通通都不缺!還能用饅頭換古董,窩頭換郵票。順便,和喜歡的男人,一起奮鬥出美好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小福妻!
296.8萬字8 351555 -
完結204 章

假少爺懷孕后不爭了
齊沅是萬人嫌假少爺,真少爺回來后他各種針對,還設計睡了真少爺他朋友,某真太子爺,后期更是不斷搞事作死,導致自己精神失常偏執嚴重,還和肚里孩子一尸兩命,重活一次,假少爺他不爭了.…
42.6萬字8.18 26794 -
完結7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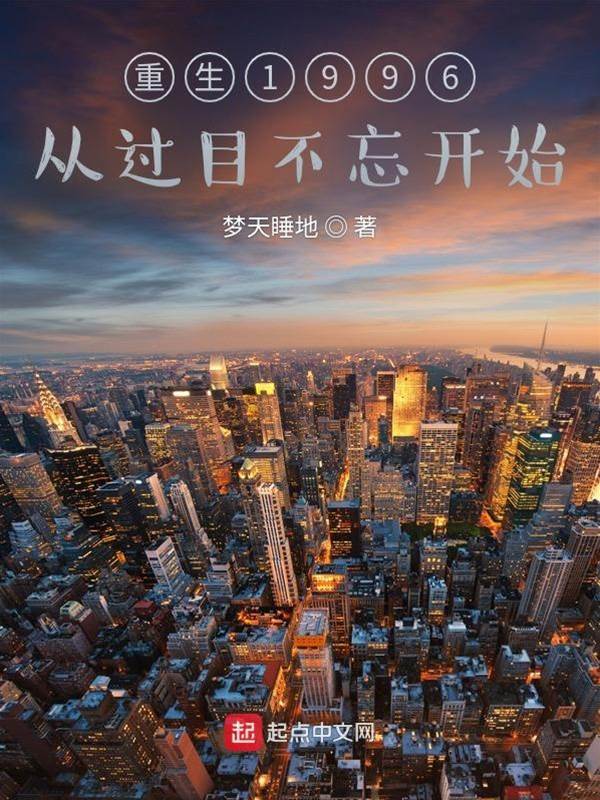
重生1996從過目不忘開始
一場車禍讓人到中年依舊一無所成的張瀟回到了1996年,回到了那個即將中考的日子。重活一生的張瀟不想再窩囊的活一輩子,開始努力奮斗,來彌補前世留下的無盡遺憾。
155.3萬字8 62069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3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