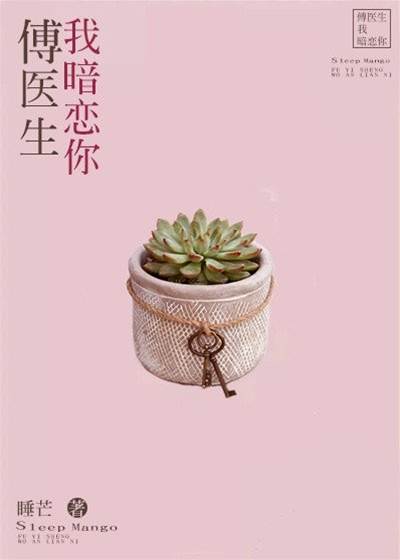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危險男秘》 第一百三十六章、虛構的平靜(下)
“肖鈺想要過來,向揚揚道歉。”
“你瘋了?”元鼓的話剛一出口,廖越安就立刻臉一沉,聲音都寒了三分,“你敢讓羅肖鈺出現在揚揚面前,信不信老子把你也趕回去!揚揚現在手都沒做,肖鈺把揚揚害這樣還不夠?還敢來添!”
“我……”元鼓剛想反駁,就被廖越安有些駭人的眼神兒瞪得不有些心虛,氣勢上立刻矮了三分。
兩年前驟然知道揚揚的份后,元鼓后悔得腸子都青了,恨自己為什麼就對他下了死手,更恨自己沒聽廖越安的話,可是廖越安卻什麼都沒說,更沒責怪元鼓一個字,一心陪著羅抿良只希能救回首揚。對此,元鼓更是愧得很,再不敢在廖越安面前多說一句過分的話。
一向難纏的元鼓有地噤了聲,衛一白和嚴界也不說話,客廳里依然抑得讓人心慌。
好一會兒,廖越安才下剛才的失控,“老元,我剛才的話你別放心上,只是肖鈺現在實在不適合過來。現在是個什麼況你還能不知道?連我們自己都日日心驚膽戰不敢出現在揚揚面前,生怕被他看到后刺激到他,更何況是肖鈺?當初揚揚見到那丫頭時候緒有多激烈你比我們幾個人都清楚,揚揚對肖鈺有多排斥你還能不知道?”
“我知道,可是、可不管怎麼說,老羅他在肖鈺的事兒上做得就是不厚道!”元鼓心里最藏不住事,廖越安的話一,他立刻憋不住說出心里話,“肖鈺是無辜的,雖然之前老羅爸爸,導致揚揚誤會,但那丫頭畢竟什麼都不知道!不知者不罪!何況那丫頭知道況后一心想向揚揚道歉,老羅卻連見都不見肖鈺一眼!這對肖鈺不公平!”
Advertisement
“哪有什麼不公平?這有點兒嚴重了,良子只不過是顧不過來。”
廖越安上象征地安著,語氣似乎很讓人信服。事實上,一向最了解羅抿良的廖越安明白得很,羅抿良這家伙,大事上一向大肚能容、顧全大局,可骨子里護短得厲害,心眼兒也小得很,甚至可以說睚眥必報,對于有點小虛榮小家子氣的干兒羅肖鈺,羅抿良私心里一直不喜,不過礙于特殊的生日和知分寸的小聰明,羅抿良一直屋及烏地容忍著。但現在居然膽敢傷害到自己兒子,羅抿良沒立刻和斷絕關系、將羅肖鈺趕出去都是看在元鼓的面!
不過這些卻不能讓滿心偏向于羅肖鈺的元鼓知道,廖越安了有些發疼的太,心想這段時間他一定要看了元鼓,不能讓他回國去接羅肖鈺過來——那丫頭小心機太多,來了的話指不定又會想什麼小手段,“這麼多年了你還不了解良子?良子不是不見肖鈺,而是揚揚這邊本走不開。”
“可肖鈺畢竟要結婚了。”元鼓甕聲甕氣,他日里最疼解語花一樣伶俐可人的羅肖鈺,心里很為抱不平。
“良子也為備好了嫁妝不是。”嚴界吐出一個大大的煙圈,似笑非笑。
“準備嫁妝算什麼!”元鼓瞪著眼睛鼓鼓的,不明白他們三個為什麼就這麼不待見羅肖鈺,“當初看人家小姑娘跟自己兒子是同一天出生,非要認領人小姑娘當自己干兒!現在找到親生兒子就立刻什麼都不管了?!”
嚴界嗤了他一聲,不屑理會他的話,掐滅手里的煙頭,掏出手機翻看著。
半天沒發話的衛一白終于沒有笑意地彎了彎角,“肖鈺,生了一顆七竅玲瓏心,但是——”
Advertisement
“但是什麼?”神經大條的元鼓有地覺到這不是什麼好話。
衛一白看了他一眼,沒理他,起走出去。
“哎哎!老白你別走!把話說清楚!但是什麼?!”
“但是,太聰明就不可了!”嚴界也站起,拿著手機出去打電話。
他們幾個不是線條的元鼓,全都知道羅肖鈺那丫頭對于羅抿良而言不過是個活的“兒子生日記錄儀”罷了,羅抿良對只有憐憫,只有自我催眠般的寄托與希冀。況且,他們幾個都是三合會的冷智囊,對一個整天在他們面前耍小聰明的丫頭片子,實在生不出什麼好來。
“什麼太聰明就不可了?”元鼓一臉不滿,顯然很反他們繞來繞去的彎彎腸兒。
“這樣吧,”廖越安看了他一眼,“等下以良子的名義再打到肖鈺賬號上五十萬當嫁妝,看看肖鈺怎麼說吧。”
——————————————————————————
溫哥華的番紅花正值花期,大片大片的彩明艷的花卉俏生生開放著,放眼去仿佛一片無邊的爛漫花海。
路邊高低起伏的坡地上,瘋長的野草被人工修剪一塊塊巨大的綠毯。
綠毯之上,花團錦簇,一條不太寬敞的山間道路蜿蜒著將這巨大的綠毯切割兩塊。
遠的山脈在清晨的天中籠罩著一霧氣,遠近山影重重,如同剪影。
“不、不行,我跑不了!”在外面的小路上繞著莊園慢跑了不足兩公里,首揚就難地停下,耍賴似的坐在地上怎麼都不愿意起來。
怕引起首揚的懷疑,羅抿良不得不適當允許莊園的醫護人員在莊園周邊范圍稍作走,當然,前提僅限于陪同首揚,外出時周邊更不了布的暗線。
Advertisement
見他的紫又深了些,陳昊忙掏出水杯,“先歇一會兒,等下再喝水。”
“不。”首揚著氣兒搖搖頭,捂了捂悶悶得有些難的口,往后野草旺盛的坡地上四仰八叉地一躺,大口大口著氣。
太剛剛升起來,隔著薄薄的霧氣,好像一枚明晃晃的潔鏡面。看得出,今天的天氣不是太晴朗,但一如既往得很舒服。
遠的山脈送來涼涼的山風,空氣中都帶著草葉和番紅花的清香氣。
首揚并不喜歡番紅花,番紅花在國經常被做藏紅花,地除了醫藥用,很有大面積種植這種花,所以首揚潛意識里總是認為,這漫山遍野的花本不是用來觀賞的,而是大片大片用來制藥的原材料!
“水還沒下去,草地上涼。”陳昊手去拉他。
首揚懶得,躺在自己并不怎麼喜歡的花間著懶,對眼前的手視而不見。
見他著實沒力氣起來,陳昊也跟著席地坐下,拍了拍肚子,“了。”
首揚沒說話,膛起伏著躺了好一會兒,呼吸才漸漸平穩下來,上詭異的紫稍微淡了一些。
兩公里的慢跑行程,上都微微有點熱,雙頰顯出點盈盈的溫度,使得臉不再那麼蒼白。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