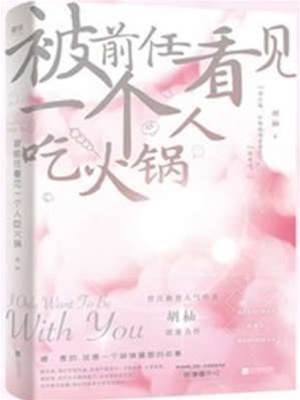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49章
聞硯桐:“嗯?”
池京禧道,“當時在門外敲門的是個經常習武之人,他走路輕盈無聲,能夠聽見我靠近門的腳步。但我并未聽見他離開的靜,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就在附近,我便故意說寺中有匪,引得他們自陣腳。”
聞硯桐恍然大悟,又問,“那你如何知道寺中的僧人也是一伙的?”
“掛在檐下的裳上,與那幾個念安寺位高的僧人上的熏香味道相同,但是在地下室的人不需要熏香,那些人極有可能是平日藏在僧人之中。”
他道,“這個念安寺中,約莫大半都是假僧人。”
聞硯桐道,“原來如此,沒想到竟有人敢在皇城邊上梁換柱,瞞天過海。”
池京禧沒應聲,看樣子是越來越虛弱。聞硯桐沒辦法,只好語氣一轉,兇的教訓道,“小侯爺,下次要是遇到危險,千萬莫要再獨自一人了!你子金貴,這次了傷定然是十分不得了,你的那些侍衛都要跟著罰的!”
本以為池京禧會冷言反駁,哪知道他只是懶懶的嗯了一聲,“我不會讓他們罰的。”
聞硯桐道,“那也不能讓自己傷啊!你看看你現在這模樣。”
池京禧掀起眼皮看一眼,“你不也下去了嗎?”
“我跟你能一樣嗎?”聞硯桐頂撞道,“我是平民,傷了就傷了,你可不一樣,你這一傷,可不得驚好多人啊!況且我當時是被刀架在脖子上下去,如果有選擇,我才不愿意一個人下去呢!”
池京禧道,“倒是委屈你了。”
聞硯桐又道,“再者說,我也沒傷啊……”
池京禧聽到這,也頓了下,問道,“你會功夫?”
聞硯桐搖頭,“當然不會,若是會功夫,定然會保護你,不你傷的。”
Advertisement
池京禧的雙眸攏上迷。他記得當時聞硯桐邊死了三四個人……
聞硯桐道,“說來也奇怪,當時的況真的很詭異,我自個也沒想明白。”
好幾次明明看著刀要砍下來了,但那些惡徒總在關鍵時刻出問題,然后把自己殺了,像是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庇護一樣。
這種莫名其妙的好運,先前也有覺。譬如武學測驗上突然的中靶,脆香樓突然中獎,前腳有了麻煩,后腳就有了解決的辦法。
皺眉,仔細回憶起來。
不一會兒熱水就送到了房間里,聞硯桐思緒回籠,說道,“快,快給小侯爺臉,洗洗手。”
侍衛將熱水置在床邊,便要手,聞硯桐攔住,“……小侯爺沒帶小廝來嗎?”
池京禧道,“掃雪不宜隨行。”
這樣一說,才注意到,牧楊和程昕好像也沒帶,邊只有侍衛。
但是怕侍衛手腳,牽池京禧上的傷口。牧楊似乎看出的顧慮,擼了袖子上前,自告勇,“我來給禧哥。”
“不,你更不行。”聞硯桐連忙上前,把他到一邊去,“還是讓我來吧。”
聞硯桐把手進盆里試了試,水極其燙,似乎沒兌涼水。忍著熱意把布巾擰得半干,然后跪坐在池京禧的邊,對池京禧道,“小侯爺,我先把你臉上的污去。”
池京禧重傷虛弱,一點攻擊都沒了,眸泛著懶意,默許了。
聞硯桐便把布巾折掌大小,從他的額頭開始起,逐一過俊秀的眉,漂亮的眼睛,高的鼻梁。得細致而輕,將他臉上濺的得一干二凈。
又把布巾浸,將上面的洗掉,再去脖子,過滾的結,白皙的側頸,連耳朵后面都沒落下。
Advertisement
侍衛將水換了一道,一洗,水中又泛著。
完了臉和脖子,又慢慢的把兩手干凈。
滾燙的意混著和的力道在皮上滾,池京禧從其中到了聞硯桐的小心翼翼。
他點了墨的眼睛好似淬了碎星般,芒微弱的閃,出了些許來。
聞硯桐把池京禧的手反復了好幾遍,才把污干凈,又怕熱氣跑了,就趕忙用棉被將他的手捂住。
仍然在等待之中,醫師也不知道過多久才會來,聞硯桐不敢放松警惕。牧楊一直在跟池京禧說話,但池京禧的回應越來越。
聞硯桐見狀便從懷里掏出一個油紙包,對池京禧道,“小侯爺,吃點東西壯壯力氣吧。”
池京禧沒有拒絕,但也沒有答應,只是看著手上的東西。聞硯桐就趕把油紙拆了,里面是兩塊夾餡薄餅,是怕坐馬車的時候揣懷里的。
餅的表面一層有些溫溫的,那是在聞硯桐懷中捂的溫度。
把其中一個遞到池京禧的邊。
池京禧起初沒彈,聞硯桐以為他不想吃,正要勸時,就見他張開咬了一口。
他緩慢的咀嚼之后,神染上一錯愕,“這是什麼餡的?”
聞硯桐疑他的反應,答道,“餡啊?小侯爺不吃嗎?”
話一出,屋中的幾人都愣住了。牧楊驚道,“你把餡的東西帶進寺里?”
聞硯桐后知后覺,“不可以帶嗎?”
“是要關大牢的呀!”牧楊道,“皇令再上,但凡在寺中吃葷食皆是對神明不敬,輕則罰板子,重則關押三到五年。”
“不是吧?吃個餅就要坐牢?”聞硯桐驚了,把油紙重新包上,又塞回懷里,“我沒吃啊,吃的是小侯爺。”
Advertisement
剛把東西咽下的池京禧:“……”
牧楊朝外張,“沒人看見……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正巧程昕帶著侍衛進來,“看見什麼?”
牧楊剛要說話,池京禧就先開口道,“無事,事可辦妥了?”
程昕點頭,“妥了。方才的靜鬧醒了書院的學生,我已派人驅散,寺中的僧人尚在睡覺,也沒有驚他們,只調了人先將念安寺周圍圍住了,明日一早再調來一批。”
池京禧頷首。
程昕擔憂的上前來,“止了嗎?”
聞硯桐看一眼他的肩膀,紗布早就被浸了,但卻沒有在往下流的跡象,“想來是止住了。”
程昕嘆一口氣,“沒想到大半夜竟出了這等事,小禧你再撐一會兒,醫師約莫快到了。”
池京禧沒再說話。
上的傷口讓他并不好,眉頭總是忍不住皺著,但神卻是平靜的。
忍耐中著年的堅毅。
聞硯桐忍不住嘆,年的池京禧就已有如此風骨,若是年了,那又該是何等模樣?
幾人在房中陪著池京禧說了半小時左右,醫師總算來了,被人拎著帶進了房中。眾人當下把位置讓開,讓醫師來醫治。
聞硯桐這才是真正放松了,子一險些站不住,跟在傅子獻后面往外走。
“聞硯桐。”突然有人。
驚愕的轉頭,就見池京禧墨眸平和,對道,“去把臉洗洗。”
聞硯桐雙眸一彎,一下子綻開了笑容,眉梢眼角都是繾綣的笑意,“小侯爺,這是你第一次我的名字,我記住了。以后可不能再我小瘸子。”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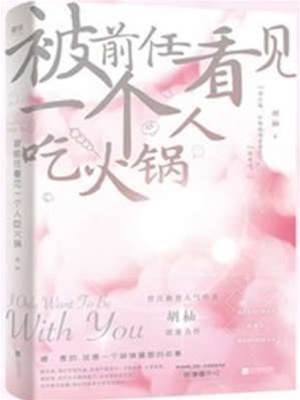
被前任看見一個人吃火鍋
【葉陽版】 葉陽想象過與前任偶遇的戲碼。 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書店。 在一切文藝的像電影情節的地方。 她優雅大方地恭維他又帥了, 然后在擦肩時慶幸, 這人怎麼如此油膩,幸好當年分了。 可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 他們真正遇到,是在嘈雜的火鍋店。 她油頭素面,獨自一人在吃火鍋。 而EX衣冠楚楚,紳士又得體,還帶著纖細裊娜的現任。 她想,慶幸的應該是前任。 【張虔版】 張虔當年屬于被分手,他記得前一天是他生日。 他開車送女友回學校,給她解安全帶時,女友過來親他,還在他耳邊說:“寶貝兒,生日快樂。” 那是她第一次那麼叫他。 在此之前,她只肯叫他張虔。 可第二天,她就跟他分手了。 莫名其妙到讓人生氣。 他是討厭誤會和狗血的。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讓她說清楚。 可她只說好沒意思。 他尊嚴掃地,甩門而去。 #那時候,他們年輕氣盛。把尊嚴看得比一切重要,比愛重要。那時候,他們以為散就散了,總有新的愛到來。# #閱讀指南:①生活流,慢熱,劇情淡。②微博:@胡柚HuYou ③更新時間:早八點
19.1萬字8 7230 -
完結179 章

攝政王妃嬌且媚
【腹黑白蓮花×口嫌體正直】【雙心機】上一世,楚遲隨墨初入了地獄。但是重來一次,他希望他能同墨初同留人間。他的小姑娘,其實又怕冷又怕黑。-————長安城中,名門閨秀數不勝數,在這其中,墨初若是自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不為其他,單單是因為那媚色無邊的容貌。娶妻娶賢,納妾納色。一語成讖。上一世,安分了十五年的墨初,甚至連一個妾都沒撈著,一朝落入秦樓楚館,不得善終。重來一世,墨初想去他的恭順賢良,本姑娘就要做那禍國殃民的第一人。可巧,殺人不眨眼的攝政王楚遲就喜歡這禍國殃民的調調。男主視角墨家那小丫頭長得好,恭順賢良又貌美,嬌嬌小小,柔柔弱弱,十分適合娶來做個當家“花瓶”,看起來也很養眼……哎,哎哎,怎麼和想象中的不一樣呢……——楚遲願以此生盡流言,惟願你順遂如意。#胭脂墨薄傾國色,初初意遲禍懷中。#
31.7萬字8 5892 -
完結183 章

風流債
沈初姒當年嫁給謝容珏的時候,還是先帝寵愛的九公主。縱然知曉謝容珏生來薄情,也以爲他們少年相遇,總有捂熱他的那日。 直到後來父皇病逝,兄長登基,沈初姒就成了沒人撐腰的落魄公主。 京中不少人私底下嘲笑她,跟在謝容珏身後跑了這麼久,也沒得到那位的半分垂憐。 沈初姒恍然想起當年初見。原來這麼多年,終究只是她一個人的癡心妄想。 謝容珏生來就是天之驕子,直到他和沈初姒的賜婚旨意突然落下。 這場婚事來得荒唐,所以等到沈初姒說起和離的時候,謝容珏也只是挑眉問道:“可想好了?” 沈初姒將和離書遞給他,只道:“願世子今後,得償所願。” 直到後來的一次春日宴中,兩人不期而遇。 沈初姒面色如常,言笑晏晏,正逢彼時的盛京有流言傳出,說沈初姒的二嫁大概是大理寺少卿林霽。 衆人豔羨,紛紛感慨這也是一樁不可多得的好姻緣。 卻無人可見,那位生來薄情的鎮國公世子,在假山後拉着沈初姒,“殿下準備另嫁林霽?” 沈初姒擡了擡頭,掙開被他拉着的手,瞳仁如點墨般不含情緒。 “……謝容珏。” 她頓了頓,看着他接着道: “你我早已和離,我另嫁何人,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29.6萬字8 10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