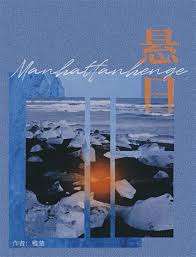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木有枝兮》 第37章 悅君 (修改版)
“其實不用再去找他,神藥谷也就不過如此,說不定用高瑜的方子,吃個幾年也就有效了。”
莫斐笑看并轡而騎的人一眼,單手控韁自如。
蘇錦言眉頭輕蹙,擔憂的看著他垂在旁混不著力的右臂。
原來說什麼三五年便能自愈是騙他安心,這次若非他堅持來神藥谷走一趟,又怎會知道當初云冕的原話竟是:紫眉丹易解難斷,若三五年我還找不到驅除余毒的法子,你這條右臂便當做是給尊夫人賠罪了吧。
“便是無效也無妨。”那男子又笑道,“這手果真廢了,便由你給我喂飯穿,且不更好?反正有你在,府里朝中的事也誤不了。”
聽如此說,一顆心更沉下去。
知道他原就做了最壞的打算,當初救自己時才會那般不管不顧。如今話說得如此賴皮,卻是從自己痊愈后,朝中府無論大小事務,又何曾肯讓自己為他代勞一分?總勸要多多休養,不許有半點勞思。
“好啦,別這麼愁眉苦臉。春如此明,我的夫人不能笑一下?”
莫斐見他總也不答,湊過臉來嬉笑逗趣。
蘇錦言無奈的看他一眼,微微彎了角,笑意溫如春。
“看到夜容過得平安喜樂,終于可以安心。”
Advertisement
莫斐嗔道:“原來你也不是為我求藥,而是去看。”
蘇錦言一笑,偏著頭看他:“侯爺留下的風流債,為妻自然要給你收拾好殘局才得清凈。”
難得一幅俏皮促狹模樣,倒惹得人心中一,只想把人拉進懷里,好好“欺負”。
前面傳來年的怒斥:“你做什麼!靠這麼近做什麼!別我的韁繩!我會騎!”
“好好好,”男子連連告饒,“你別,我不過來,你坐直,拉好韁繩,對對,就這樣……”
前面道路平坦,莫斐松開韁繩,拉住妻的手,信馬由韁。
“你說,我要不要故意把丹泉打一頓,讓你那小仆心疼心疼,才不至于天天這麼嫌棄?”
蘇錦言習慣了他的胡鬧,低頭笑道:“青楓其實對丹泉也很好。”
莫斐撇撇:“好?這也好?我看他跟他主子一樣不老實,心里明明喜歡得要命,上偏偏不饒人。”
蘇錦言溫一笑:“這麼比起來,丹泉可比他主子好得太多了。”
“哼!”莫斐發現這以克剛的,如今斗,自己還是要輸,真是夫掃地。
手指被人纏繞,蘇錦言靠過來,一雙笑眼瞅著莫斐。
“生氣了,夫君?”
Advertisement
只這兩個字便任何忿忿不平煙消云散。
莫斐展,長臂一舒,蘇錦言驚呼一聲,子臨空而起,被攬到他的馬背。
“發什麼瘋!”路人紛紛投來詫異的眼,他的耳一熱,一手捶在他口,“快放我下去!”
“不放!”他笑得囂張,“你是我夫人,共騁一騎,天經地義!”
蘇錦言滿面通紅,不敢去看路人臉。又怕他單手不好控制,抱住他的腰肢,把頭埋在他前。
“駕!”男人自詡騎一流,竟催馬狂奔。
“莫斐,你胡鬧!”
一雙眸薄怒含,瞪得又圓又大。
春下,那眼眸明亮,莫斐心神一。
曾幾何時,他午夜夢回,都是這雙眼睛。
那是在蘇府居家遷出京城之后。
本來日日相見,耳鬢廝磨,卻一下千里關山,一面難求。
他消沉了好久,日日錦書不斷。
那時,并不知道,這便是相思。
母親不知有意無意,談起娶妻生子,也默許他在花叢留,他便以為男人只能喜歡人。于是就浪著,卻一直覺得不夠,了些什麼似的無法言說。
直到到阿玉,第一此看見那雙眼眸,就瘋狂的上,覺得跟心中某一契合,有什麼被填滿似的滿足。
Advertisement
再后來,被北族子的快樂爽朗吸引,不復消沉惆惘。
于是,種種糾葛混,從此開始。
深種,不知在何時何地,卻差錯,顛沛流離。
——錦言,我喜歡你。在很小的時候,與你一樣。
心悅君兮不自知。
男子俯,溫的在妻子發頂落下一吻。
飛馬奔馳,道旁景快速被拋在腦后,如歲月匆匆,流逝不返。
那消逝的歲月不可追憶,他們相擁著奔向前方更長遠的春夏寒暑。
不知何起,也許很小很小的時候,也許直到離世前的最后一眼。
癡消得人憔悴,又難堪風霜雨雪欺。
相恨,相守。
相,相守。
不不恨,變陌路。
相知相守,一瞬,便是永恒。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團寵小鳳凰
上古鳳凰宿黎一朝渡劫失敗轉生,成為一個妖族家庭的孩子。萬年後的世界多姿多彩,層出不窮的新玩意讓宿黎大開眼界,為了能適應現代生活,他在大妖父母、學渣哥哥、熱心風妖、昔日下屬……等一眾人的關愛下重新修煉成長,直至本命劍離玄聽出現,他才漸漸發現萬年前渡劫失敗的秘密……該作品行文輕松平和,溫馨詼諧,以主角的成長線為主線徐徐推進講述故事,既寫出家庭生活的幽默有趣,又寫出宿黎在適應現代生活中啼笑皆非的舉動。故事以平穩的敘事方式講述親情友情,揭示宿黎萬年前的渡劫失敗的秘密,進而推出宿黎與離玄聽的情誼。文章敘事輕緩有序,溫馨觸人,值得一讀。
66.7萬字8 8942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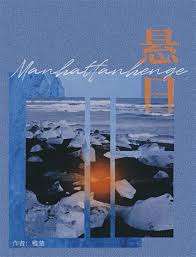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