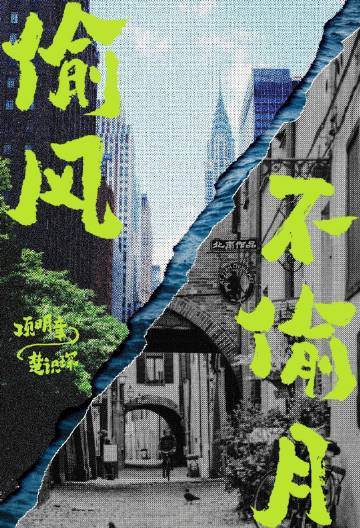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木有枝兮》 第11章
,痛苦而快樂的。
男子的息重到脈賁張。
子低低的聲音弱無力,如歌如泣。
“斐哥哥,記得我,記得阿玉,記得今晚。阿玉除了你,再不會有第二個男人。”
多年之后,在蘇錦言的夢魘中,安玉赫嵐耳鬢廝磨的哀求依舊清晰可聞。他也是個男人,可以想象得到,像
那樣的子,用那樣的語氣說出那樣的話,這個世上本沒有哪個男子能夠拒絕得了,更何況是深的
那個男人。
又一次驚醒,蘇錦言額間冷汗涔涔,心臟冷凝一片,把雙手麻痹,與那一晚毒發心脈時的形一般無異。
在那一個北原冰川上的夜晚,他孤一人在生死邊緣苦苦掙扎,鬼門關上幾番回。
而一簾之外,莫斐與他的阿玉春宵一度,共赴巫山,翻云覆雨。
有時,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自己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支撐過來的?
Advertisement
或許,他的人活了下來,心,卻死在了那里。
翌日,莫斐送安玉離開,大概惜別依依,難舍難分,送了一程又是一程。
回來時,帳中仍是一片安靜。
“還沒起?”他皺眉問,心想日上三竿,這也懶散得有些過了。
侍從低聲稟告:“大公子昨夜染了風寒,高太醫方才把了脈,說要臥床休息數日方能痊愈。”
“這麼貴。”莫斐嗤笑一聲,突然想起什麼,心大好,立刻吩咐人道,“既然是病了,不如過幾日再走
,去知會北王一聲,也給朝中回書。”
侍從張了張口,見小侯爺一臉興沖沖模樣,到的話生生咽了回去。
誰都看得出來,大公子并非真的染病,其中卻不可與外人言。也只有小侯爺漠不關心至此,完全無知無
覺,一心只在胡上,想要多留數日,只怕還是為了私會之故。
侍從雖是他的心腹,卻也覺得心寒。
Advertisement
三日后,太醫來回莫斐:“大公子病穩定,可以啟程了。”
莫斐遲疑一陣,卻是問道:“我聽帳仍有咳嗽,若還是虛弱,再多留幾日也無妨。”
太醫不知他心里的盤算,還以為太竟從西邊升起,小侯爺到底曉得關心下夫人了。心中著實為蘇錦言到
歡喜,趁機進言道:“要不然,侯爺去看一看大公子,問一問是否需要多做休養再啟程?”
所得的回復卻是淡淡一哼:“問他做什麼?你拿主意不就好了。”
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清清楚楚都聽在耳中。
蘇錦言昏昏沉沉之中心已痛到不知道痛,只曉得,自己不能死,無論如何不能死在這里。他答應了老侯爺,
要陪莫斐平安歸去。他也明白出使非同兒戲,和平即便只是假象,也不能因一己之失令戰事陡起,生靈涂炭
。
就是這樣又撐了兩日。
莫斐終于肯啟程上路。
Advertisement
他仍騎馬歸國,派了一輛大車載著“臥病在床”的夫人,一路且行且住,走得甚慢。不知的人還道小侯爺
恤夫人病,故意放緩了歸心似箭的行程。有心人卻看得明白,每逢夜宿驛館,總有頭戴紗巾的妙齡子
半夜自后門而,到天明方去。
直至回到朱雀侯府,蘇錦言的“病”仍未痊愈。
久咳不愈之癥,始于那個冬季。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