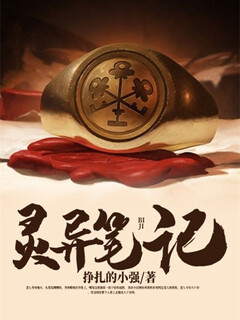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獨代神婆》 第176章 鏡中人
“坐下。”
高僧背對著獨蛋打開了一個破舊的櫃子,從裡面取出了一套泛黃的大,抖了抖,直接套在了上。
又不知道從哪裡摘了個拂塵,架在了左臂彎裡。
看這架勢,倒還真有點像做法的人了。
獨蛋坐在一面邊框磨損嚴重的銅鏡前面,欣賞著白非非的臉。
銅鏡不怎麼清晰,反倒讓鏡子裡的面孔稍顯扭曲,像是鏡子裡的人正在經某種痛苦而不得不皺著整張臉皮。
高僧端來一碗偏綠的水,輕輕安置在銅鏡旁邊。
獨蛋心一,這該不是給喝的吧?
這種水喝了確定不會死人?
高僧見了獨蛋驚恐的眼神,卻也不解釋,一心在後面準備著什麼。
獨蛋忐忑了許久,直至高僧的拂塵了這盛滿綠水的碗,獨蛋的心才終於落回肚子裡。
“忍著點,可能有點疼。”
高僧話音剛落,本就沒給獨蛋準備時間,就生生的將拂塵往頭上甩。
獨蛋驚得閉上了眼睛。
起初是沒有覺的,只能到拂塵輕微在頭上劃過的。
直到拂塵上的水緩緩過頭發流頭皮,一種天靈蓋被翻開的痛直襲獨蛋。
獨蛋痛得哇哇大起來。
“媽呀!我的腦袋!”
獨蛋出於本能雙手就要往腦袋上放,被高僧一一拍了下來。
“除非你想你的手跟你的腦袋一樣,穿個,那你盡管去腦袋。”
他的聲音極威懾力,讓獨蛋不得不哆嗦著手,將它們在了膝蓋之上。
“高僧……你想要我的命可以直說,但您總不能不厚道的在人腦袋上開個吧……”
獨蛋疼得眼淚都出來了。
“你的小命值幾條錢?我有必要這麼大費周章的要你命?別廢話了,安靜下來,等那東西出來。”
Advertisement
高僧的手沒有停過,一遍又一遍的將拂塵往獨蛋的頭上輕拂而過。
對於他來說可能是輕拂,對於獨蛋來說基本上就是一臺挖掘機在摧毀的所有神經。
獨蛋覺自己快要死了,頭腦被挖空的那種死。
“放心,你頭頂沒被打開,只不過是開了你魄上的口而已。”
高僧見到獨蛋生無可的神,最終還是開了口。
獨蛋從陣痛中回過神來,問他:“什麼魄?”
可沒等到高僧的回答。
“咦?”
一聲悠長的困讓獨蛋半睜開了眼睛。
過汪汪淚水,獨蛋居然在銅鏡裡面看到了自己的臉!
起初自己的臉是很模糊的,不仔細看的話是被覆蓋在白非非臉的下方。
可隨著疼痛的遞增,獨蛋的臉開始有節奏的忽忽現,直至最後完全覆蓋了白非非的臉。
除此之外,還看見自己頭發上伏著的一團像貓一樣的生。
高僧的手將那生直接取下了,丟在了蠟燭燃起的火苗之上。
隨之發出一陣窸窸窣窣像是有人在咒罵的語調,隨著火焰越來越小,其聲音也緩慢的消失殆盡。
“你——”
高僧這個字的語調拉了很長,像是橫沖直撞的火車頭,最終卻沒能接上火車車。
他只說了這一個字,宛若看破了一切,但他嚴嚴實實的閉上了。
獨蛋此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一時氣氛非常尷尬,尷尬到獨蛋忘記了腦袋上的疼痛。
等到獨蛋反應過來自己已經不再痛的時候,高僧已經收好了他所有的工,連他的大袍也下了。
獨蛋看了一眼銅鏡,裡面的臉又了白非非的。
了頭頂,是實的,的確沒有被開。這讓獨蛋大舒一口氣。
Advertisement
獨蛋心有餘悸的捂著自己的腦袋,看向神複雜卻沉默不語的高僧。
“高僧……為什麼突然就肯幫我了?”小聲的詢問道。
“不該你知道的,別問那麼多。”高僧惡狠狠的瞪了獨蛋一眼。
獨蛋脖子一,站了起來。
“好好走你自己的路,不要了別人的道。最好不要牽扯到我們這裡,否則遭罪的是你自己。”高僧剛剛似乎沒有瞪解氣,又加了一句。
“什麼意思?”獨蛋捂著腦袋不知所以。
“沒什麼意思。你走吧。”高僧揮揮手,要趕獨蛋離開。
獨蛋拒不出門。還在做最後的抵抗。
“高僧,我看你既然幫了我,應該也不算太壞,為什麼要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呢?”獨蛋鬥膽問道。
高僧的眼皮一抬,頗有威力,嚇得獨蛋往後靠了靠。
還好他並沒有拿工,只是拍了拍他略微發青的袖子。
“那些所謂施了法的錢,不過是為病人分散一些痛苦,讓那些接了錢的年輕人承擔一點點不屬於他們的痛苦而已。”
“一點點?”獨蛋咧了咧。
三番兩次差點見了閻王爺,如果這對於高僧來說,只是一點點痛苦的話,那他完全可以去過一過奈何橋了。
高僧無視獨蛋的質問,接著說道:“這種痛苦因人而異,有的人只是得一場小冒,或是摔一跤。最嚴重的也不過是流點無傷大雅的,本就不會危及命。”
獨蛋的眉頭擰得更深了。不得不按了按眉心。
“我們改變不了人的生死狀態,但這種行為能讓病人減輕很多痛苦。家裡有病人的話,這救命稻草會讓所有人都欣一場。不管是得病者還是照顧病人的家裡人,能活著的心態更重要。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這點。”
Advertisement
“那我呢?我算是怎麼回事?”獨蛋不敢相信這件事居然被他給描述得無傷大雅。
這兩天明明差點就死翹翹了。
就不信這人還能說出花來。
高僧凝神看著桌上的那盞蠟燭,火苗在他皺如枯葉的臉上瑟瑟發抖。
獨蛋也不抱住了雙臂。
“你曾經有過自殺的潛意識,還殘留在部,接了那承載病人痛苦的錢之後,殘念倍增長,在不主控制的況下會下意識的去尋求解方法。”
高僧仍舊對著火苗,似乎火苗才是他的說話對象。
“不過你放心,我已經將你上的殘念給取下了。以後不要再過來打擾我們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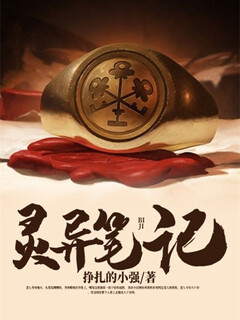
靈異筆記
為什麼自從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後的眼睛時常會變白?是患上了白內障還是看到了不幹淨的東西?心理諮詢中的離奇故事,多個恐怖詭異的夢,離奇古怪的日常瑣事…… 喂!你認為你現在所看到的、聽到的就是真的嗎?你發現沒有,你身後正有雙眼睛在看著你!
29.6萬字8 7634 -
完結1139 章

龍王妻
血月之夜,龍王娶親,洛安之本是高門貴女,卻因為命運的裹挾成為龍王妻,從此走上了一條不同於常人的道路……
163萬字8 6058 -
完結1231 章

我在驚悚世界當商人
有人做活人的買賣,也有人做死人的買賣。 我做的,就是死人生意,不是賣棺材紙錢,也不賣壽衣紙扎。 賣的,是你從未見過,更加詭異的東西......
214.3萬字8.33 160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