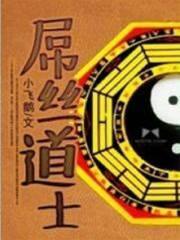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獨代神婆》 第105章 反轉
井涼這邊的況並不像井元易想象的那樣輕松。
他的力已經慢慢耗盡,一子下去已經無法敲死喪,有時甚至要三四才能放倒他們。
後面還有坡比和多德幫襯著。
雖然幫不上什麼大忙,但好歹可以讓他專心應付自己面前的幾個喪,不至於腹背敵。
“我說,這位小哥,力這麼強怎麼練出來的?”
坡比眼見這波喪已經只剩最後幾個,開始有心跟井涼聊天了。
“師父教的。”井涼冷冷回複道。
“師父?那你師父是誰?應該很厲害吧,居然能教出這樣的徒弟。”坡比竟然有些羨慕。
“跟你有關系嗎?”除非井涼自己提起,他很避諱人問他師父的名號。
他覺得這是對師父的不尊敬。
坡比被突如其來的一句反問給噎住,看了眼多德,乖乖閉了。
眼看井涼即將力支,拿著鐵的手也開始不聽話的抖了起來,多德也忍不住了。
“小哥,你先歇會兒,讓我們來。”
雖說他們兩個沒那麼大的本事一放倒一個。但一個轉移喪注意力,另一個叉喪是完全沒問題的。
井涼轉頭,看到的是一張秀白的面孔和一副瘦弱的,微微皺眉,握住鐵的手又了。
多德莫名的覺得他被這個男人辱了,臉不由得黑了起來。
“男人嘛,總有不如人的時候,這種時候就要學會放下。”坡比見狀拍了拍多德的口,有種落井下石的快。
多德角微起,沒有刻意去辯駁。只在接下來應對喪的時候,更加賣力。
等到井涼覺胳膊酸痛得再也抬不起來的時候,打算將這幾只沒啥危險的喪丟給後面的兩個人練手。
Advertisement
剛回退兩步,槍聲響起,震徹夜空。
面前的喪重重的倒下。
一槍倒一個,整整響了五槍。
“什麼人啊,早點出現,我們也不至於這麼艱難嘛……”
坡比無奈的看向槍聲的源頭。
一批穿戴整齊的雇傭兵一排站好,靜靜的守在黑暗中。
坡比瞳孔陡然小,下的線條繃了起來。
井涼著自己酸痛的,也沒有將鐵放下的意思,冷冷看著即將會發生的一切。
“該來的,始終會來。”
多德語氣帶著憾,像是歎冬天會帶走最後一片樹葉一樣的憾。
坡比整個人轉過去,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那排雇傭兵中走出來一個,對著他們說道:“歸隊。”
井涼側頭,冷眼看向坡比。
坡比沒有轉,也沒有說話,整個人宛如一座雕塑,屹立在黑暗之中。
“這兩個人,不能留。”
雇傭兵又說話了,隨即舉起了槍。
“不可以!”坡比一個回就要搶奪他的槍,卻抓了個空。
那人聲音狂,像是含了一口沙子,哈哈的笑了起來。
“你不會對這些人產生了吧?那個從小在訓練營長大的男孩居然會對他的獵產生,哈哈哈……”
坡比使勁咬著牙,脖子上的青筋暴起,眼裡也因憤怒逐漸泛起紅。
“我說,放了他們。”
“放?誰給你這個資格?要說份,我們的份可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你為間諜,明面上看起來比我們自由而已。”
雇傭兵玩弄著手上的槍,語氣略帶戲謔。
“我可以給你們想要的東西。放了他們,這是換條件。”
“條件?哈,你居然跟我們講條件。我們可是在訓練營一起長大的兄弟,你講條件……你他媽不就是為上面辦事的嗎?”
Advertisement
那人一腳踹在坡比的肚子上,踹飛半米遠。
多德看著地上捂著肚子的坡比,了拳頭。
“哦,真是對不起,一不小心就腳了,我們都是兄弟,這些小傷小痛你應該不會計較的,對吧?”
那人嬉笑著又去扶起坡比。
“不要以為在外面呆久了就是外面的人了,你可別忘了,你一輩子都有為人奴隸的印記。”
他了坡比的頭發,架著他往黑暗中走。
另一只手稍稍抬起,只待手落,子彈便會對準這多餘的兩個人去。
“坡比。”
獨蛋失的聲音在後響起,坡比沒有力氣也沒有膽量去回頭。
“咦,又多了三個?沒關系,三個一樣幹掉……”
話音未落,一輛車徐徐開來,軋在了剛被放倒的喪上,漿四濺。
雇傭兵立馬前去開門,上面下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孩。
笑得天真無邪,是尚夏。
從車上副駕駛下來的是另外一個人,同樣讓獨蛋眼。
是公司的人事部玲姐。獨蛋曾經就是的助理。
坡比微彎子,站在了尚夏的後面,眼神空。
獨蛋捂著自己發麻的腦袋,幾乎要撐不住了。
這是什麼況?
在的世界裡,這分明就是完全沒有半錢關系的三個人,今天,朦朧的晚上,站在了一起。
“獨蛋阿姨,你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呀?”尚夏那稚的嗓音笑著問道。
越是天使之音,越是地獄之門。
獨蛋子一歪,絆倒在地上。
多德趕沖過去要扶,被推開了。
“你知道多?你也知道是不是?”獨蛋的心此刻就像是一塊破布,這裡被人剪上一刀,那裡被人燒上一把,早已經皺皺,混不堪。
Advertisement
“我猜到幾分,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不要說了。我不想聽。”獨蛋將頭撇過去,留他一個冷漠的側臉。
多德和的眸子此刻變得暗淡無,他站起來,看向對面的坡比。
同為男人,他如何不懂坡比的痛?
他們都是被命運牢牢套住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得掉。越是掙紮便會越陷越深。
沒有人想騙。
沒有人想騙一個被爺爺保護得那樣好的一個純粹善良的人。
但他們上背負的,又豈是一個騙局能夠裝得下。
“獨蛋阿姨,反正今晚你會死,死之前還是讓你死個明白怎麼樣?”尚夏眨著的大眼睛,面帶無辜的笑道。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45 章

千年人鬼情
我的第一任老公是天庭神帝接班人。我的現任老公也不是人——是只鳥。我活了太多個13歲才成年,走了十遭鬼門關。如今,這槍林彈雨的現代社會怎麼鬥法術?妖精鬼魅全打門前過,咱打得服,但凡人做人最怕的,還是被情所累!神啊,求放過。
63.7萬字8 17766 -
完結7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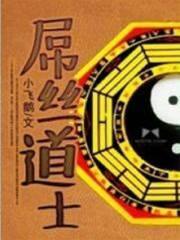
屌絲道士
一個尿尿差點被電死的男人,一個運氣差到極點的道士!他遇到鬼的時候會惹出怎樣爆笑的事端?各種精彩,盡在屌絲道士中。
182.8萬字8 7023 -
完結292 章

夜半陰婚
支教回校的路上,我接連做了兩場詭異的夢。村裏的神婆卻說,那不是夢,是鬼招魂。從此,我身邊多了個時時想把我撲倒的帥氣冥夫。我也踏上了不斷遭遇靈異鬼怪的漫漫長路……
134.7萬字8.33 96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