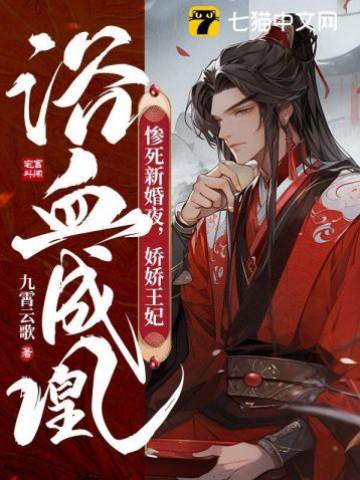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七十年代嬌媳婦》 第052章 (大修請重看)
葉青水并沒有很快睡,把腦袋靠在枕頭上,窗子下幾縷月,聽著耳邊微弱的呼吸聲,有了一種恍惚的錯覺。
仿佛手就能到似的。這種深夜的靜謐給人一種踏實溫暖的覺。
凌晨四點多,葉青水醒來的時候發現謝庭玉摟著的腳睡著了。
葉青水默默地回了自己的腳,躡手躡腳地穿上服,起床去柴房。
清晨,謝庭玉被一陣哐哐的敲敲打打的聲音吵醒。
他看見葉青水正埋著頭刨著木板,隨意扎的頭發上沾著幾縷卷曲的木屑,手里的作雖然笨拙、卻很有章法。
葉家正在蓋新房子,撿幾塊不要的木料方便得很。
謝庭玉看見眼前的這一幕,愣住了。他問:“水兒,你做什麼?”
葉青水頭也不抬地回道:“給你做張床。”
謝庭玉有那麼一瞬間的心塞。
他在葉青水邊蹲下來,湊近,看見沒穿棉,心領口里出的一截白玉似的脖頸,風一吹,額頭薄薄的微汗緩緩滴下。
謝庭玉說:“水兒你把木頭放一邊,我自己來做。”
葉青水聽了,放下了才鋸了一半的木頭,把它們統統給了謝庭玉。
……
初冬,一場雪下完后,杜家終于答應松口把杜小荷嫁到葉家。
原來是杜家老大思來想去,認為既然人已經確定要嫁到葉家,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多浪費一天的糧食,干脆早點把人嫁了省事。
然而葉家的新房子還沒有落,就這樣挑這種不尷不尬的節骨眼地把兒嫁來了葉家,著實不太面。
于是葉青水把自己的屋子讓了出去。
家里最大的兩間屋子一間是葉青水的父母住,另一間是葉小叔的,但葉小叔伍的時候跟侄換了房間。
Advertisement
葉媽倒是很想把自己住的房間讓出去。然而的丈夫英年早逝,把這個屋子讓出來當新房,名頭上不太好聽。
葉媽還擔心婿心里多有些意見,正想勸住兒,這件事還是算了。婿那樣講究的城里人,哪里能讓他住那麼寒磣的屋子?
誰料謝庭玉聽完水丫這個決定后,非但沒有意見,應和起來反倒很積極。
他聽到這個消息心一下雀躍了起來,小房間,這不就意味著他不用睡木床了嗎?
他言辭懇切地同葉小叔說:“原本這間屋子就是小叔讓給水兒的,咱們住了很久也夠了。現在是小叔娶媳婦要。”
那語氣,要多真誠就有多真誠,直把葉小叔這個大男人得不輕。
葉小叔現在已經徹底扭轉了對謝庭玉的印象,這個侄婿雖然廢柴是廢柴了些,家務活一竅不通,但是脾氣好、又通理,還是個知識分子,水丫沒看錯人。
謝庭玉說完之后,面含微笑地回屋子,他興致地把他那張新做的簡陋的小床拆了,扔到柴房里當柴火燒。
搬屋子的時候,謝庭玉承擔了搬屋子的重活,葉青水整理房間,夫妻倆配合起來,沒多久就把新房間捯飭得整整齊齊。
謝庭玉搬著東西的時候,里還哼著小調,從他邊路過的人都能到他的愉悅。
葉青水起初有些不解,還以為他真的很熱心。后來收拾東西的時候,琢磨過來了。
不會是想的那樣吧?
謝庭玉瑣碎的東西有些多,等把品全都擺到新屋子的時候,空間一下子變得仄了起來。
僅容兩人住的幾丈寬的屋子,再架一張木床意義不大。翻個,長的謝庭玉都能翻到葉青水的床上。
Advertisement
謝庭玉了把汗,臉上有著涌的笑意。
葉青水也想到了這個問題,心里騰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覺。
這種覺表現出來就是,的臉突然騰地就紅了。
葉青水讓出房間給小叔的時候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現在想起來了也不好再回去把房間要回來了。
晚上,窗外的寒風呼號,嗖嗖地刮這薄薄的窗紙。
葉青水打了一盆洗腳水,掉子把腳丫放進水里。
這個原本是非常尋常的作,只不過因為多了一道目的注視,變得別扭起來。
謝庭玉目灼灼地盯著浸泡在水里的腳丫,結滾了一下。
冬天溫度極低,水盆里薄薄的水霧繚繞,小姑娘白皙的腳丫沒在水下,氤氳著水汽,朦朧得跟一截白筍似的,細膩白。人的腳丫跟男人的差別也太大了。
這讓謝庭玉不地想起了一句詩:“六寸圓致致,白羅繡屧紅托里。”
這雙踩過水田的腳丫,出乎意料的小巧圓潤,靜靜的夜里,聽得到撥弄熱水的聲音。
葉青水以前不覺得屋子大有什麼區別,這屋子陡然減原來的三分之一大小,跟謝庭玉變得抬頭不見低頭見。抬起頭,看見他眼簾低垂,眼神灼灼地沖著的腳看。
葉青水臉蛋一紅,連洗腳的興致都沒了,匆匆地提起腳來干了水,很快提起洗腳水拿到門外倒掉了。
謝庭玉滿腦子里全是葉青水提起腳,白皙的腳丫子沾著水珠,被熱水燙得一片意,出乎意料地可。
他昨晚捂了一晚上的腳丫子,長這模樣。
謝庭玉覺渾突然燥熱,鼻尖有些意,他不低頭了把鼻子,旋即捂上。他臉微黑、匆匆地奪門而出,正好撞上了倒完洗腳水回來的葉青水。
Advertisement
謝庭玉隨意地跟葉青水說:
“我去洗個澡。”
葉青水差點被奪門而出的謝庭玉撞了個正著。
心里不罵了句謝庭玉。
謝庭玉很久之后才回來。
他打開門,屋外呼呼的一陣寒風灌了進來,他下了厚重的棉,出淺灰的棉質保暖。他用巾隨意地著剛洗的頭發,靠著火爐烤干了才上床。
時間尚且還早,兩個人的意識也都很清醒,跟昨晚那種迷迷糊糊之間的措手不及截然不同。謝庭玉的俊臉微紅。
他垂著頭,有一搭沒一搭地著頭發,那用力的程度,像是要把頭發揪下來似的。
葉青水本來沒有什麼特別的緒,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被謝庭玉染了。
忽然覺得很尷尬。
昏黃的燈下,那規律的呼吸聲,愈發清晰,甚至連哪一刻急了、慢了,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的男人和人之間,有一種莫名的愫在涌。
葉青水按照慣例,掉了棉和鉆進被窩里,連不自在的翻都減了很多。
的手心不自覺地起了汗,渾崩得的,半小時不到,的額頭就沁出了汗珠。
含糊地說:“你還要看書,看到幾點?”
“要不……要不我們把吹燈了?”
葉青水看見他在燈下的影子,洗過澡之后的他渾散發著一清新的澡豆氣味,夾雜著一點男人剛的氣息,淡淡的燈照在他的臉上,映得他的眉眼如星,分外璀璨。額間稍稍潤的發,短短的,清爽利落。
葉青水忽然心生煩躁。
心底仿佛有一的力量正在伺機反撲,它像一顆種子,長在暗的地方太久了,地,破土而出。
謝庭玉輕描淡寫地應了一聲,他說:“等頭發干了,我就吹燈。”
Advertisement
然后——
葉青水聽見了他隨意地解開服的聲音,忽然有些難,他進屋子的時候已經掉了多余的服,為什麼還要!
當他就勢掉子的時候,一直裝死的終于忍不住吱了一聲:
“那個、玉哥……”
“你、你睡覺不要子。”
謝庭玉聽見張的、糯的聲音,聽得心都了,他不期然地彎笑了一笑。
“誰睡覺不子的?”
被窩里的葉青水恨不得拿枕頭往他臉上砸。
他看見了得快能滴下的臉蛋,酡紅一片,可得一塌糊涂。
“謝庭玉,你不要耍流氓。”忍無可忍地說。
他終于不逗了。
“好,聽水兒的。”
他吹了燈,就勢躺了下來,他聽到耳邊的呼吸聲有些靦腆、張。
他躺了一個小時,心臟也砰砰地急促跳了一個小時。
這是一種青又甜的煎熬。
謝庭玉也不敢,指尖滲出了汗,“水兒,你怎麼連翻都不翻,有這麼張嗎?”
他輕輕地笑了一聲,“你覺不覺得咱們這樣怪別扭的——”
他漆黑的眼眸靜謐地注視著,兩個人之間暗暗涌的氣氛忽然變得干燥、曖昧起來。
黑暗之中,他呼吸漸漸地靠近、越來越近,鼻息間嗅到的甜甜的淡香,好得宛如夢似的。
葉青水臉轉向另一邊,把眼睛閉得更了。
的腳趾不自覺地了,有點張。雖然是冬天,但也能到邊那個溫暖的熱源,以及他帶來的力。直到覺得渾繃得發酸了,一顆心七上八下提心吊膽。
當謝庭玉以為他可以一親芳澤的時候——
邊的人突然翻起了床,“嚓”地劃破火柴,點亮了燈。
習慣了黑暗的眼睛被這明亮昏黃的線灼得眼皮發跳,謝庭玉額間的汗水流了下來,碎碎的短發在額間,有一種說不出的。
看見了謝庭玉眼睛像夜空,星目劍眉,眼瞳里糾結著一團黑,濃稠得像墨。
謝庭玉定定地看了許久,只見長臂一撈,出乎意料地從床底揀出幾只空碗。認真地把糾纏在一起的兩張被子分開來,把一只只空碗擺在中間。
謝庭玉聽到了令人心碎的聲音。
小姑娘強打著鎮定、聲音沙啞卻依舊甜潤地說:
“這是一條楚河漢界,你不能越過它,要是被我發現它不見了——”
“明天你就繼續打地鋪。”
謝庭玉只覺興頭上,強行被潑了一盆冷水,他抿住了,沉默地盯著看了許久。
越看越覺得不可思議。
半年之前那個會沖上來主他子的水丫,已經不見了,變這個興頭上還能一本正經地用碗擺界限的狠心人。
葉青水雙臂握在一起,漆黑的眼眸出一抹不屈的芒。
半晌……
聽見了謝庭玉著聲說:“好好好,你別怕我。”
“睡吧。我保證乖乖的、不越界。”
“你好好睡。”
謝庭玉俯下來,給松了松被子,用手帕了額頭上的汗。作輕,仿佛對待珍寶似的。
他俯下來,漆黑的眼睛在靜謐的眼里,暗流涌,分外灼熱。四目相接的那一剎那,葉青水不住地扭過了頭。
謝庭玉地笑了一聲,強忍住親一口的沖。
他給完汗后,規規矩矩地睡下了。
第二天,葉青水醒來,發現自己的另一邊的被子平平整整,連道痕都沒有,擺在正中央的碗也一只沒倒。睡在外頭的謝庭玉,姿勢標準,睡得平靜安穩。
涼涼的月落下,落在他白皙的面龐,清雋的五褪去了白天的沉穩,安靜放松的模樣增添了一分年的味道。眉目清秀俊朗得跟畫上去的似的。
他遵守了許下的承諾。
葉青水躡手躡腳地穿好服,爬下了床。
……
隆冬臘月,到了年底任務的時候,葉青水把自己養的豬趕去稱了斤。
一直按照劉一良給的養豬訣,科學地養豬。
于是葉青水養的每一頭豬都超過了兩百斤,變了大隊里炙手可熱的養豬能手,還賽了第二名足足有三十斤。每頭豬超過兩百斤的部分,都額外地獎勵給養豬戶。
三頭加起來差不多就有二十多斤,加上每家每戶能均分的十斤豬,足足三十斤豬。
這可把葉阿婆高興得快瘋了,三十斤的豬,哪怕勻個十斤出來也夠做一場面的酒席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5 章

七零小軍嫂
1972年的夏天蘇若正收拾著行李,過幾天她就要去青大讀書,那里還有一個未婚夫正等著她。 可是一覺醒來,她卻成了一個偏僻鄉村的知青, 床前站著一個陌生的軍裝男人, 床頭有一個娃正叫著她“阿媽”。 她轉頭,就看到破舊的床頭柜上,有一個日歷,上面印著,1977。 蘇若:#$$#?我還是個寶寶呢! 可是這個男人,好帥! 她的臉紅了。// 蘇佳重生歸來,舉報繼妹,逼她下鄉,搶她男人,以為這樣繼妹前世的氣運就都會落到她身上,結果沒想到繼妹竟然嫁了個更有權有勢的回來了…… 蘇佳:男人還你,咱還能做好姐妹嗎? 蘇若:麻煩臉拿來給我踹一下先~
44.2萬字8 69404 -
完結480 章

重生之別來無恙
傅昭覺得自己修道修成了眼瞎心盲,一心敬重維護的師兄為了個小白臉對他奪寶殺人,平日里無所交集的仙門楷模卻在危難關頭為他挺身。雖然最後依舊身隕,但虧他聰明機智用一盤蛤蜊賄賂了除了死魂外啥也沒見識過的窮酸黃泉境擺渡人,調轉船頭回了八年前的開春…… 十六歲的霍晗璋(冰山臉):“師兄,我要傅昭。” 師兄無奈搖頭:“晗璋,人活在世上就要遵守規則,除非你是製定規則的人。” 霍晗璋(握劍):“我明白了。” 師兄:……不是,你明白什麼了? 關鍵字:強強,溫馨,雙潔,1v1
118萬字8 7202 -
完結309 章

夜場小王子
一場陰謀,讓我獲得了命運筆記,里面有格斗術,隱身術,讀心術等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技能,為了完成任務獲得那些小技能,我毅然踏上了夜場偷心的香艷之路…… 陰險歹毒的財閥千金、暴力傾向的女班主任、非主流大姐大校花、嫵媚動人的黑道女老大、可愛呆萌的女警花……不管你是女神還是女神經,在我夜場臺柱子的套路下,都將淪陷…… 美女需要服務嗎?我什麼都會,最拿手的是偷心!
57萬字8 9080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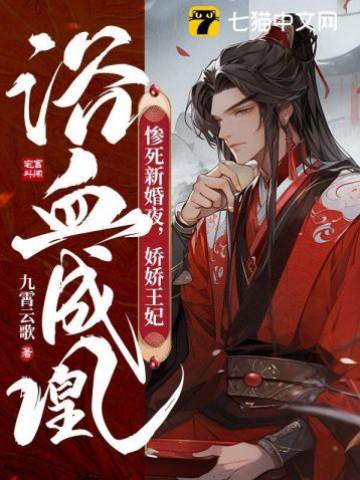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