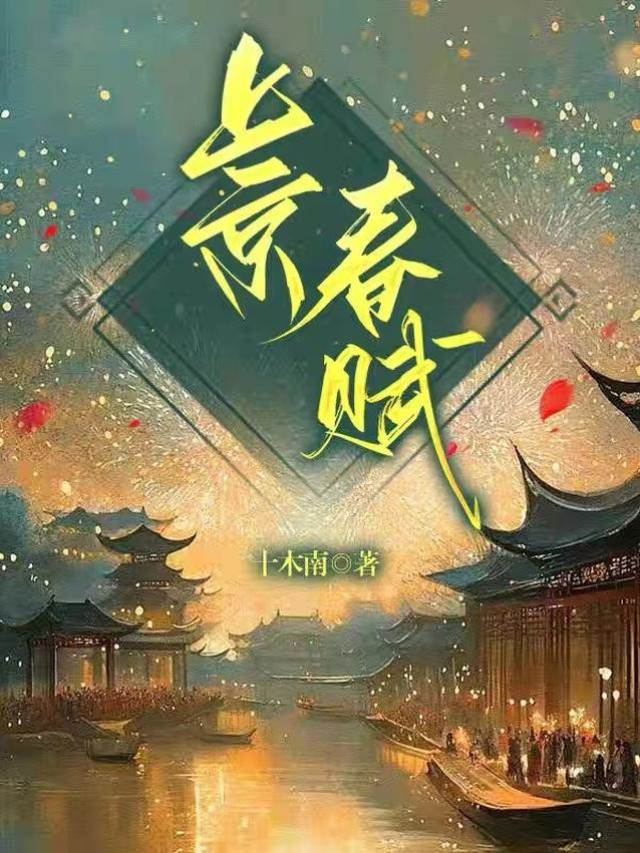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囚金枝》 第103章 平行世界
風停了, 花園里極靜,靜的一切聲響都清晰可聞。
兩人躲在大樹后,嘉的心跳起.伏的厲害, 口鼻被蕭凜蒙住了,又有些不過氣來。
那草叢里的男人四下了察看了一番, 并未發現人影,又急吼吼地回去了,沖著那人安道:“沒人,剛才是樹影。”
“可我明明看到了一個子……”那人圍著服,肩頭還在外面,警惕地看了看,“要不今晚我先回去吧?”
“咱們見一次不容易, 這次若是錯過了, 下次還不知得什麼時候。”那男人仍是湊了過去,“這里這麼偏僻, 不會有人來的,他們都在前殿參宴,咱們快些結束就是。”
“可是……”
那子仍是有些猶豫,那男人卻直接撲了上去, 急不可耐, 口中“心肝”“餞”地胡喊著, 各種污言穢語伴隨著不堪.耳的聲響一起傳來, 躲在樹后的嘉雙頰登時紅,眼神不知該往哪里看。
蕭凜捂住嘉的, 呼吸的熱氣落到掌心, 帶著些微的意, 引得他間也微微發, 手指無意識地蜷了蜷。
捂了片刻,直到手底下的人平靜了下來,雙頰憋得發紅,蕭凜這才低聲開口道:“那孤放開,你別喊。”
嘉已經窘迫到無以復加了,再不放松一點,恐怕能直接暈厥過去,連忙點了點頭。
那手一放開,立即大了幾口氣,才好些。
然而一平復下來,樹后的靜卻原來越大。
嘉從前從未接過這種事,聽著那子似是痛苦又似是愉悅的聲音連忙低下了頭,裝作沒聽見。
可心底卻止不住地好奇,不明白這子為何這般……
蕭凜比年長一些,這種事已經見怪不怪了,但外面的聲音越來越放肆,他皺了皺眉,手從后面捂住了嘉紅的快滴的雙耳:“孤幫你擋住?”
Advertisement
嘉點了點頭,任由他將雙手搭上去。
雖然這雙手實際上遮不住什麼,但掩耳盜鈴也好,起碼能讓他們不那麼尷尬。
捂住了的耳,將人擋在了自己后,蕭凜這才向不遠的張德勝咳了一聲。
他低低一咳,正在提著燈籠的張德勝立即發現了草叢里的異樣,朝著那邊大吼道:“你們在做什麼?”
那對男一見有人來,慌忙分了開,拾起服穿上。
可經過張德勝這麼喊,四周巡邏的侍衛立即都聚了過來,將兩人團團圍了起來。
刺眼的燈籠一打,眾人才認出來,原來這鬼混的兩個竟然是一個不寵的宮妃和侍衛。
到底是個宮妃,眾人面面相覷,一時不知該如何手。
張德勝為難,只好去樹后請示了太子。
穢宮闈乃是大罪,當場杖斃也不為過。
但蕭凜懷中還有個膽小的人,沉了片刻,怕嚇到,他只是吩咐了一句:“先把人關起來,送到慎刑司去。”
“奴才遵命。”張德勝領命,吩咐著將人捆了起來。
外面又哭又,鬧騰了好半晌才平靜下來。
可不知為何,嘉卻覺得邊的人呼吸也在發沉,在的后頸上有意無意地拂過,引得微微栗。
嘉瑟了一下,指了指他捂住雙耳的手,蕭凜這才松了開。
手一放開,蕭凜拈了拈指尖,手上仿佛還殘留著那臉頰的.膩。
撞破了一樁宮闈事,嘉心里慌,連忙跟他賠罪:“殿下,臣不是故意的,請殿下見諒。”
“與你無關。”蕭凜將手垂到了腰側,又問,“你不是隨父母回去了嗎?”
嘉方才的確是走了,又不好直說找墜子的事,只是含混地開口:“回稟殿下,臣有點事耽擱了,這才折回了一趟。”
Advertisement
“丟東西了?”蕭凜問。
他為何會知道?
嘉一臉困。
蕭凜卻直接從袖中將那墜子拿了出來,遞到了跟前:“是不是這個?”
那墜子上還刻著字,嘉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連忙低下了頭:“是臣的,多謝殿下。”
說著便要去拿,可是當剛到那墜子時,蕭凜卻忽然收回了手,將那墜子握在了掌中,微微挑眉:“這墜子,不是送給孤的嗎?”
他果然看到那墜子上的字了。
嘉面緋紅,囁嚅著開口:“這個做的不好,殿下還給我吧。”
“既是生辰禮,豈有收回去的道理?”蕭凜著那墜子細細地挲,約還能聞到一清淡的香氣,“孤覺得很好。”
明明是在說玉,可他的眼神落在的臉上,嘉心中微微發,直覺他是在說一樣。
那宮妃和侍衛已經被人拉走了,可蕭凜還著站著,呼吸落在的側臉上,嘉臉上又又麻,連絨都豎了起來,覺得有些不妥。
但蕭凜神正常,看著只像是忘記了挪開一般。
夜風飄著悠長的弦歌聲,縷縷,悠長婉轉,方才令人耳熱的聲音還驅之不去,氣氛一時間變得有些怪異,嘉著狂跳的心,小聲地開口:“殿下,我先……”
可一抬頭,卻正對上了一張迫人的臉,蕭凜不知何時又進了一步,幾乎快將整個人圈住。
嘉呼吸一滯,后半句話堵在了里,呆呆地站在那里屏著呼吸,任憑他越來越近。
當那高的鼻尖到的鼻尖,清冽的氣息將包圍的時候,嘉眼神的不知該往哪里看,手心地抓著角。
兩片溫潤的即將到一起的時候,嘉心跳已經跳到了嗓子眼,下意識地閉上了眼。
Advertisement
可預想中的溫熱卻并沒有到來。
蕭凜薄已經過了的鼻尖,即將落下的時候,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年紀似乎還不大。
理智一拉回來,蕭凜深吸了口氣,在了的耳側沉沉地.息:“你是不是尚未及笄?”
嘉耳被他口中的熱氣燙的微麻,懵懵地點頭:“下個月。”
還有一個月。
他等得起。
蕭凜看著薄薄的幾乎可以看到那青經絡的臉頰滾了滾,手將那落到那頭發上的葉子摘了下來,又恢復了一派正經:“不早了,孤派人送你回去。”
“謝殿下。”嘉腦海中了一團漿糊,讓張德勝護著走了回去。
直到轉的時候,嘉才想起來自己是來拿墜子的,又回頭看他:“那墜子……”
“墜子不錯,孤很喜歡。”蕭凜將那墜子收到了手心,“你下個月及笄,孤也會送你一份禮。”
他要送什麼禮?
還是在及笄宴這種談婚論嫁,對子來說極為特殊的時候。
嘉心跳砰砰,正問他,但是一看見他那劍眉星眸和清冷疏離的樣子,又怕是自己自作多,胡地點了點頭,隨著張德勝碎步離開。
不長的一段路,上了馬車的時候,嘉卻已經微微出了汗。
“怎麼耽擱這般久?”秦父擔憂地問著兒,“東西找到了嗎?”
嘉心思恍惚,半晌才回過神來,連忙回答:“找到了。”
秦父看著空空如也的雙手,和江氏對視了一眼,默契地沒再開口。
回去之后,天已經不早了,拜別了父母,洗漱完之后,嘉一個人躺在床上,真正靜下來的時候白天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回放,忽然覺察出些許不對。
Advertisement
那墜子怎會到了太子殿下手里?
張德勝一個東宮的小太監,沒有主子的應允,怎敢隨意帶著去花園尋找?
為何又那般巧,太子殿下又恰好出現在花園,巧救了?
嘉越想越不對勁,腦海中生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念頭——這位太子,該不會是故意拿了的墜子,引到花園一見吧……
這想法一生出來,嘉又立馬否定,不可能。
他堂堂一個太子,怎會對一個五品小的兒費這麼多心思。
可若是不是……這一切又該如何解釋?
嘉翻了個,閉著眼的又睜了開,看著黑沉沉的夜有些困。
還有那會兒,殿下低下了頭,是準備吻嗎?
他準備送的及笄之禮又是什麼呢……
嘉一仔細回想,眼前卻忽然出現了他那張英氣人的臉,低沉的嗓音仿佛也環繞在耳畔,心跳不控制地砰砰直跳。
輾轉反側了許久,嘉臉頰一忽兒滾.熱,一會兒發白,冷熱替了許久,起來擰了帕子了臉才平靜了下來,著自己閉上了眼。
折騰了一通,直到天微微見了白的時候,嘉才終于睡了過去。
昏昏沉沉中,不知為何,白日花園的那一幕忽然進了的夢。
草叢搖晃,人影浮,耳邊飄著細碎的聲響。
只是那面目模糊不清,黑團團的混沌了模糊的影。
嘉想走開,可雙腳卻仿佛被勾住了一般,怎麼也挪不步。
恰好一陣風刮過,那子揚起的脖頸忽然高出了草叢,出了臉。
嘉一定睛,忽然發覺那雙目迷蒙的人竟和長得一模一樣——
僵了片刻,視線再往下,卻見那只錮在腰上的手骨節分明,手指修長。
而這只手的主人,正是那位風霽月的太子殿下。
花園的人為何會變他們……
一對上那雙幽深的雙眼,嘉心跳砰砰地響擂鼓,猛然睜開了眼坐了起來,大口大口地著氣。
秋日的早上還有些冷,不多會兒,嘉平復了片刻,后背上的熱汗轉冷,冰涼地在脊背上,才慢慢清醒了過來。
醒是醒了,可夢中的一切卻分毫未淡忘。
嘉捂著臉,臉頰一點點地發燙,不明白為何會做這樣的夢,可那夢太過清晰,連.沉的呼吸都清晰可聞,仿佛又不止是夢似的。而且,夢里的那位太子殿下,和現在似乎也很不一樣……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59 章

九歲嫡女要翻天
西涼威遠王府。 虎頭虎腦、年僅5歲的小王爺蕭沫希見自家娘親又扔下他跑到田野去了,包子臉皺得都鼓了起來。 小王爺哀怨的看了一眼身邊的爹爹,老氣橫秋道:「父王,你當初怎麼就看上了我那沒事就喜歡往外跑的娘親呢?」 蕭燁陽斜了一眼自家人小鬼大的兒子,隨即做出思考狀。 是呀,他怎麼就喜歡上了那個女人呢? 沉默半晌...... 「誰知道呢,腦子被門夾了吧」 同命相憐的父子兩對視了一眼,同時發出了一聲無奈嘆息。 攤上一個不著家的女人,怎麼辦? 自己的王妃(娘親),只能寵著唄! …… 身懷空間穿越古代的稻花,只想安安穩穩的在田野間過完這輩子,誰知竟有個當縣令的父親,於是被迫從鄉下進了城! 城裡的事多呀,為了在家有話語權,稻花買莊子、種花卉、種藥材,培育產量高、質量好的糧種,愣是輔助當了九年縣令的老爹一步步高升,讓寒門出身的顏家擠進了京城圈子! 這是一個寒門嫡女輔助家族興旺繁盛的奮鬥故事,也是一個相互成就、相伴成長的甜蜜愛情故事! 男主:在外人面前是桀驁的小王爺、霸道的威遠王,在女主面前,是慫慫的柔情郎。 女主:事事人間清醒,暖心又自強!
241萬字8.33 267043 -
完結98 章

給前夫的植物人爹爹沖喜
宋朝夕一觉醒来,穿成书里的同名女配,女配嫁给了世子爷容恒,风光无俩,直到容恒亲手取了她的心头血给双胞胎妹妹宋朝颜治病。她才知自己不过是个可怜又可笑的替身。奇怪的是,女配死后,女主抢走她的镯子,病弱之躯竟越变越美。女主代替姐姐成为世子夫人,既有美貌又有尊贵,快活肆意! 宋朝夕看着书里的剧情,怒了!凭什么过得这么憋屈?世子算什么?要嫁就嫁那个更大更强的!国公因为打仗变成了植物人?不怕的,她有精湛医术,还有粗大金手指。后来国公爷容璟一睁眼,竟然娶了个让人头疼的小娇妻!! 小娇妻身娇貌美,惯会撒娇歪缠,磨人得很,受世人敬仰的国公爷晚节不保…… PS:【女主穿书,嫁给前夫的是原著女主,不存在道德争议】 年龄差较大,前面女宠男,后面男宠女,互宠
50.2萬字8 21788 -
完結155 章
重生后成了皇叔的掌心寵
燕寧一直以為沈言卿愛慕自己才把自己娶進門,直到沈言卿一碗燕窩讓她送了命,她才恍然大悟,自己不是他的白月光,撐死了只是一顆米飯粒。沈言卿的白月光另有其人,清艷明媚,即將入主東宮。重頭來過,燕寧哭著撲進了楚王鳳懷南的懷里。鳳懷南做了三十年皇叔,神鬼皆俱無人敢親近他。僵硬地抱著嬌滴滴依戀過來的小丫頭,他黑著臉把沈家婚書拍在沈言卿的臉上。“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本王媳婦兒!”上一世,她死在他的馬前。這一世,他給她一世嬌寵。
79.5萬字8.18 65138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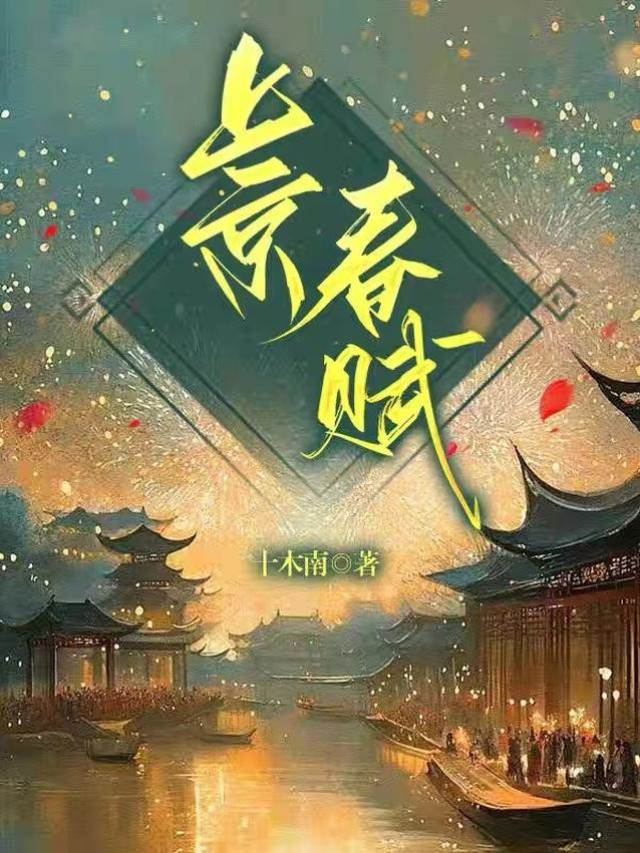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