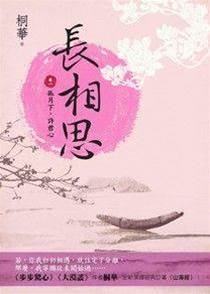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白日提燈》 第96章 奪燈
雖然段胥答應了要與晏柯合作,但晏柯對段胥仍然不放心。他把段胥從鬼牢中提了出來,但是在外面行走時依然要他戴上手銬腳鏈,在他上施加法咒令他不能呼喚賀思慕,不過免了拷打刑罰。
晏柯一面對于段胥不屑,因為這只是個生命短暫的凡人,沒有一點兒法力,在惡鬼的面前不堪一擊,賀思慕對他的關照和護也只是須臾一瞬。段胥很快就會被賀思慕忘,而他,就算是被賀思慕憎恨,也會在心中停留更長的時間。
另外一面,他又對段胥抱著約的嫉妒,畢竟段胥曾經得到過賀思慕的,無論短暫或長久,那畢竟是貨真價實的。
賀思慕告訴他鬼王燈的蹊蹺所在時,晏柯覺得憤怒至極,但是他又覺得果然這才是能讓他喜歡三百年的子,能讓他暫時下對權力的,做的臣子的人。
世上沒有哪個人能比得上賀思慕,他一定要得到。
段胥則表現得十分乖巧,每每提到賀思慕總是出痛恨神,他時常被蒙著眼睛帶到這里或那里,十幾天之后他終于聽見了震耳聾的戰火聲。
他眼上的布被拿下來,適應了一陣線,環顧四周發現自己于一座營帳之,戰火聲仿佛是從腳下傳來的。
段胥想他們應該是在一座山的山崖上,山崖之下便是戰場。
晏柯開營簾走進來,冷冷道:“便是現在,時機到了,和賀思慕換五。”
段胥出手來道:“把破妄劍還給我,我要借破妄劍的靈力催符咒。”
晏柯瞥了段胥一眼,還是鬼仆拿上來了破妄劍。
段胥接過破妄劍,拿出禾枷風夷留給他的符咒。破妄劍微微閃爍起芒,段胥卻皺起眉頭,睜眼道:“賀思慕離這里太遠了,符咒難以起效。”
Advertisement
晏柯目一凝:“你想耍什麼花招?”
段胥思索了一會兒,指著晏柯腰間的鬼王燈,說:“鬼王燈里有的魂魄,或許我可以借它的氣息來換五。”
晏柯一手便掐住了段胥的脖子,眼里滿是懷疑。段胥抬起手握住他的手腕,艱難地說道:“你也知道……我沒有半點法力……也不是惡鬼……就算鬼王燈在我手上我也用不了。這里……里里外外都是你的部下……我還戴著手銬腳鏈……我怎麼逃……”
段胥的臉漲紅了,眼里一派真誠清澈。
晏柯慢慢地松開手,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他。
雖然他有所懷疑,但是段胥確實是沒有一點法基的凡胎,拿著鬼王燈也無用,不可能逃。
晏柯沉默了片刻將鬼王燈放在段胥手中,目地盯著他。段胥一手拿著鬼王燈,一手拿著符咒,他將鬼王燈舉至前,突然粲然一笑。
在這粲然一笑的瞬間,晏柯意識到什麼不對,還來不及做任何反應段胥已經將那鬼王燈玉墜一口吞下,頭一咽進了肚子里。
霎時間從他的里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如同回山倒海般擴散開來,一瞬間得晏柯后退三步才勉強站住。段胥的服和頭發被疾風得飄飛起來,他整個被籠罩在鬼王燈浩的鬼氣中,如同一只真正的惡鬼。
“抱歉,我真的能用鬼王燈。”
段胥偏過頭,仿佛在五年前的幽州見城一般,微微一笑。
當年他和思慕第一次換嗅覺時曾經吞過鬼王燈,那時賀思慕便以破妄劍的靈力為,讓鬼王燈聽命于他,當時說,鬼王燈與他意外地契合,他竟然能掌控大部分力量。想來這些年里,思慕并沒有撤回這道許可。
Advertisement
鬼王燈原本是的命門,卻在認識他僅僅半年多時將鬼王燈托付給了他。在喜歡他之前,已經付了信任。
段胥仿佛摘鐲子一樣把手上的手銬摘下來,再抬腳將腳上的腳鏈踢開,微微一笑道:“還有,這些東西關不住我,抱歉。”
烏泱泱的惡鬼涌進來,晏柯起便要沖向段胥,段胥目一凝周便燃灼起藍的熊熊鬼火,瞬間將晏柯沖開。
段胥并不拔出劍,只是拿劍指向鬼眾之前不能靠近他的晏柯,一派明朗地笑道:“晏大人,思慕的名字從你里說出來,我都覺得惡心。要奪走的法力,要俘虜,待我死后你要對做什麼呢?你生前就這麼惡心的嗎?”
晏柯兇狠地盯著他,簡直恨不得要把他碎尸萬段。
段胥的笑容更燦爛,轉著手中的劍徑直撇開晏柯朝營外走去,藍的火焰順著他的步子一路燃燒,惡鬼紛紛避讓,他邊走邊說:“我可做不到像你這樣惡心地活著。”
鬼界事鬼界了,滅晏柯的事,他便不越俎代庖了。
鬼火燃灼了營簾,段胥走出營外一眼便看見了對面山崖之上的賀思慕,那紅白曲裾烏發飄飛的姑娘,如同烏枝紅梅覆白雪。隔得太遠他看不見的表,只覺得好像往前走了一步。
段胥低下頭看去,果然在山崖之下便是兩邊廝殺的惡鬼軍隊,戰場上塵煙滾滾,無數惡鬼在利齒和刀刃之下化為灰燼漫天飄飛,如同一場灰白的細雪。再這樣鋪天蓋地的灰燼之下,線變得昏暗,世界仿佛停滯在晨昏界的時刻。
“真是壯觀啊。”段胥低聲說,他拿起破妄劍平舉于眼前,兩手各執一邊緩緩開,銀白的劍上折出耀眼的芒,映在他圓潤的眼睛之中。
Advertisement
“走吧,破妄。”
他說完便徑直從山崖上一躍而下,明藍的火焰隨他一路燒著,快落地時他以破妄劍在山壁上幾番借力,趁著鬼王燈的火氣落在戰場之中。
他面前站著的是晏柯的兵,那些鬼兵回頭看見從天而降一只燃灼鬼火的惡鬼,不驚慌失措地起來。段胥雙手一揮破妄劍,挽了個漂亮的劍花,便毫不廢話地沖進了惡鬼群里。
賀思慕站在山崖上,瞳孔一陣。
惡鬼的視力是極好的,便看見的小將軍一黑殺進了敵軍后方,兩柄寒閃閃的劍仿佛疾風般卷起所有接近的惡鬼,絞殘肢化為灰燼。他眼帶笑意,像是不知疲倦般于殺戮中盛放,仿佛永不止息的夸父,追逐太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樣大開殺戒。
賀思慕的世界靜止了片刻,然后便從山崖之上一躍而下,顧不得后姜艾的驚呼。以強悍的鬼力讓萬軍戰栗,如烏云頂一般落在戰場中,一路奔向段胥,最終在戰場中央拉住了他的臂膀,喚道:“段胥!”
段胥舉劍的手停了下來,在這個瞬間賀思慕拉住他一閃便回到了原先所在的山崖上。
段胥滿眼赤紅,如同了力一般跪倒在地,向前傾倒時被賀思慕抱在懷里。
“哈哈哈哈哈……暢快……真暢快……”段胥在賀思慕肩頭大聲笑著,斷斷續續地說道。
賀思慕扶著他的肩膀,目著,著他的眼睛喚著他的名字:“段胥!”
段胥的眸閃了閃,眼中的紅慢慢退。他安靜地看了一會兒賀思慕,繼而笑道:“思慕,新年好呀,歲歲平安。我來給你送新春賀禮。”
他指指自己的肚子,說道:“鬼王燈我幫你拿回來了,就在我肚子里。”
Advertisement
賀思慕著他半晌,那雙漆黑的眼眸抖著慢慢沉淀于黑白分明,紛紛揚揚的細灰之中,他們仿佛剛剛穿過天地燃灼的浩劫。慢慢地將他抱,覺不到他的,所以要用盡自己的力氣,把他抱得一點,再一點。
“段胥,段舜息……”咬牙切齒地喊著他的名字,聲音抖著,仿佛每一個字都花掉了很大的力氣,一字一頓地說:“我恨死你了。”
段胥也抱住賀思慕的后背,把頭埋在的肩膀里,后知后覺地開始,仿佛上的傷在這一刻都疼了起來一般,的肩膀慢慢地被他的淚水浸。
時隔一年看到的剎那,他想他要一路殺到面前,然后對說——我不想跟你結束。
我們還要糾纏一輩子,我們不可以就這麼結束。
但是現在他說不出來這句話,他只是喃喃說道:“疼,思慕,你抱得太。”
賀思慕在他耳邊低聲說:“不會有我疼。”
“你現在又不會疼。”
“我會的。”
是你教會了我疼。
賀思慕覺得渾的痛楚無著落,只能道:“你要疼死我了。”
段胥拍著的后背,拍著拍著,突然渾繃,掙扎著要推開。賀思慕猝不及防地松開他,便看見段胥吐出深的水澤,濺在的臉上和襟上。
怔了怔,看著段胥捂著,那源源不斷地從他的指中流下來,仿佛永不停止似的,他眼里有些驚惶,卻含糊地說:“你不要怕……這個……”
“是。”賀思慕拉開他掩著的手,只覺得快要不了這種疼痛,慢慢地說道:“你以為我看不見,便不知道這是什麼嗎?”
段胥不能再捂住,便從他的里大量涌出,他的目漸漸變得迷離,搖晃著向前傾倒,倒在賀思慕的肩膀上。他低聲說:“思慕……我……我生病了。”
在說這幾個字的空檔,他還勉強握住了賀思慕的手,與十指相扣。
然后松了力氣,暈倒在肩頭。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3581 -
完結369 章

權臣心上撒個嬌
蕭懷瑾心狠手辣、城府極深,天下不過是他的掌中玩物。 這般矜貴驕傲之人,偏偏向阮家孤女服了軟,心甘情願做她的小尾巴。 「願以良田千畝,紅妝十里,聘姑娘為妻」 ——阮雲棠知道,蕭懷瑾日後會權傾朝野,名留千古,也會一杯毒酒,送她歸西。 意外穿書的她只想茍且偷生,他卻把她逼到牆角,紅了眼,亂了分寸。 她不得已,說出結局:「蕭懷瑾,我們在一起會不得善終」 「不得善終?太遲了! 你亂了我的心,碧落黃泉,別想分離」
65.4萬字8.18 673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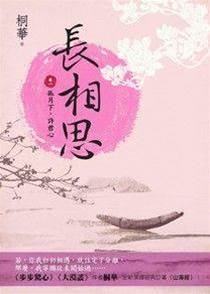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790 章

重生后我被繼兄逼著生崽崽
上輩子的謝苒拼了命都要嫁的榮國候世子,成親不過兩年便與她的堂姐謝芊睡到一起,逼著她同意娶了謝芊為平妻,病入膏肓臨死前,謝芊那得意的面龐讓她恨之入骨。一朝重生回到嫁人前,正是榮國侯府來謝家退婚的時候,想到前世臨死前的慘狀,這一世謝苒決定反其道而行。不是要退婚?那便退,榮國侯府誰愛嫁誰嫁去!她的首要任務是將自己孀居多年的母親徐氏先嫁出去,后爹如今雖只是個舉人,可在前世他最終卻成了侯爺。遠離謝家這個虎狼窩后,謝苒本想安穩度日,誰知那繼兄的眼神看她越來越不對勁? ...
106.2萬字8.18 21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