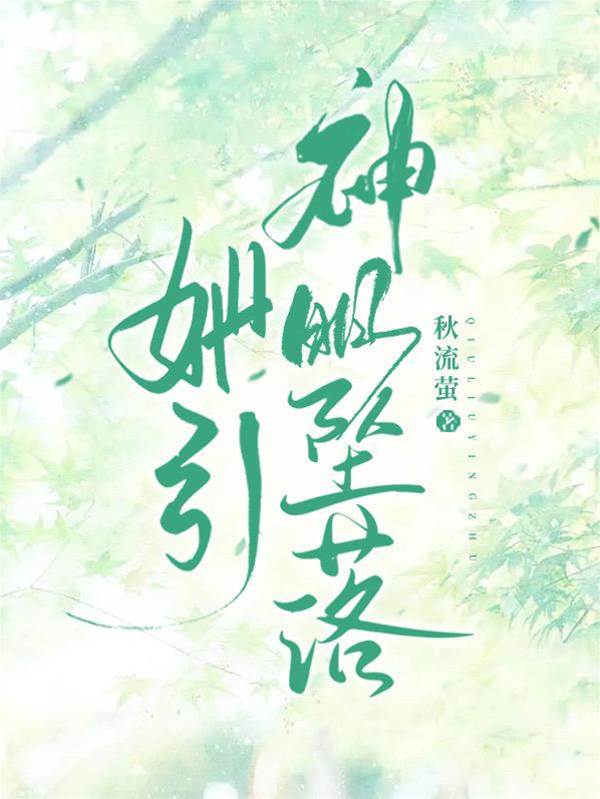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縱我情深》 第38章 能看出來我很期待了麼。……
下午五點
哪怕外界已經一團,頂層總統套房,厚厚的窗簾拉著,不讓一瀉進來,不任何打擾,安靜抑得像是另一個世界。
房間暗無天日,只有書桌上一盞臺燈靜悄悄地亮著。
借著燈,還能依稀看見昂貴的地毯上散落著幾個空了的酒瓶。
不僅如此,房間里都彌漫著濃重的酒氣,沙發上的男人在影中,看不出是睡著還是醒著,手機就放在手邊,屏幕亮著,散發出微弱的芒。
霍思揚看見眼前這副場景時,一度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認識傅北臣這麼多年,他還真的從來沒見過他什麼時候像現在這樣頹唐過。
哪怕是之前有一次項目出事,傅北臣險些就要輸掉那場對賭協議,差點就一無所有的時候,他也沒見過他頹廢如此,了無生氣的樣子。
更何況,現在的況遠遠比不上之前如履薄冰的時候,據他所知,傅北臣早早就已經準備好了應對策略,可以將損失降到最低。
可等消息真的出來之后,他卻沒有第一時間阻止事態發酵,而是任由那些新聞高高掛在首頁上。
外面已經了一鍋粥,沒人知道他究竟要做什麼。
可霍思揚卻能覺到,他像是在順水推舟,借這次機會,將他的這個,告訴某個人。
一片死寂中,沙發上的人忽然低聲開口:“查到了嗎?”
霍思揚驟然回神,才發現他本沒睡著,并且聲音聽著也異常清醒,只是比平常啞了些。
他走過去,將沙發的落地燈打開,沒了平時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查到了,消息是韓子遇那個垃圾出來的,還有個項目被停了,商琰不知道怎麼橫了一腳,現在價還在跌。”
Advertisement
霍思揚在他旁邊坐下,面嚴肅:“還有老爺子那邊,看來是要徹底跟你站在對立面了,不東借著這次事想你把位置讓出來,老爺子沒放出風聲,相當于是默許了。”
傅北臣倚在沙發上,襯衫領口凌地散著,領帶松松垮垮,眉眼一片暗。
他的聲音依舊沒什麼緒:“知道了。”
聽出他還是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霍思揚徹底急了,口不擇言地了口:“所以你他媽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等到你這幾年玩命拿回來的傅氏再被你親手毀了?這他媽是鬧著玩的嗎?”
“有多人看見新聞了?”傅北臣忽然淡聲問。
霍思揚被他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一愣,好氣又好笑地反問:“首頁掛了一天了,你說呢?”
傅北臣沒說話,只垂眸看了一眼旁放著的手機。
依然安安靜靜。
霍思揚看見他的作,一個難以置信的念頭忽然冒出來。
“你他媽等到現在,不會是為了等姜知漓看見那些新聞吧?”
話音落下,無人應答。
霍思揚實在難以理解他這麼做到底是為了什麼,氣極反笑道:“傅北臣,你他媽是不是瘋了?”
沙發上的男人闔著眼,神晦暗莫辨。
房間里靜得幾乎連針落下都能聽到。
不知過了多久,低沉喑啞的聲音忽然響起。
“我很怕。”
頓了下,傅北臣勾了勾,語氣嘲弄:“怕知道這些之后,又會像八年前那樣,離開我邊。”
因為怕,所以才不敢告訴有關傅家的一切。
聞言,霍思揚猛地一怔,不敢相信這句話居然會從他的里說出來的。
傅北臣在他眼中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將驕傲兩個字刻進了骨子里。除卻私生子的世,他就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站在神壇上,是可不可及的存在。
Advertisement
當初簽訂對賭協議之后,連霍思揚這個外人,看著那個不可能完的數字,每天都在心驚膽戰。
甚至,他還問過傅北臣,如果最后輸了,該怎麼辦。
那時候的傅北臣,站在落地窗旁,俯瞰這整座城市,著與年齡不相符的從容沉穩,不開口便能讓人信服,是天生就該站在頂端俯瞰的人。
他神極淡,只說了一句話。
我不會輸。
于是他們就真的贏了那場不可能的戰役。
霍思揚從來沒見過他像現在這樣。
那個對什麼事都同樣冷淡,像是天生就冷心冷的傅北臣,也會因為一個人而患得患失。
會因為一個人,把他與生俱來的理和都拋在腦后。
明明是睚眥必報的格,卻只給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就這樣什麼都不做,守著手機,等著。
霍思揚離開后,房間再度陷一片死寂。
唯有墻上的時鐘的指針轉發出的微弱聲響。
時間一點點流逝,窗簾隙里進來的也逐漸徹底消失,他的心好像也跟著一點點沉下去,墜進一片深不見底的深淵之中,空得聽不見任何回響。
手機依然安安靜靜,昏暗的線里,傅北臣拿著手機,將聊天記錄從頭看到尾,一遍又一遍。
不知道究竟看了多遍之后,他終于放下手機,沉默地起走到浴室,洗漱換。
早晨七點,傅氏集團總部大樓,會議室里燈火通明。
急會議忽然召開,打得所有人措不及防。
長達三小時的會議結束后,整座大樓陷張而凝重的氛圍,每一位員工幾乎都開始忙碌起來。
公關部,項目部,甚至是法務部,全部開始有條不紊地行起來。
在業其他大型企業還在籌謀如何低價收購傅氏集團的份時,才驚覺傅氏的價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穩住。
Advertisement
一場接著一場的急會議后,會議室上方的LED燈終于熄滅。
高層們聽完實時匯報,終于如釋重負地松了口氣。
原本他們還以為,這次危機有在國的傅董事長從中推波助瀾,再加上已經錯過了□□的最佳時機,損失慘重必然是不可避免了。
可沒想到的是,下跌趨勢竟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被控制住,顯然是提前就制定好了全部應對計劃,并且算無策,手段雷厲風行。
臨時跟傅氏集團解約,翻臉不認人的幾家企業,全部在同一時間出了各種丑聞,且要支付巨額違約金。
會議室里的人一個個都面喜,唯獨坐在主位的男人依舊面平靜,看不出喜怒,只是漆黑如墨的眸比往日更暗了幾分,渾散發著生人勿近的氣息。
所有人連大氣也不敢出,只能打起十二分的神仔細做事。
會議結束,傅北臣率先走出會議室,幾個高層隨其后,跟著他朝辦公室的方向走去,打算繼續商定后續策略。
安就在辦公室門口,看見傅北臣的后還尾隨者一行人,素來沉穩的面容染上一慌。
他急切開口:“傅總.....”
可安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完時,辦公室大門已經被傅北臣推開。
突然,一道纖細的影從里面出來,像是飛起來的花蝴蝶似的,直直沖進傅北臣的懷里。
實在太過措不及防,傅北臣的也僵了一瞬,眼底的寒潭剎那間裂開一條隙。
在場所有人都愣住了,呆呆地看著傅北臣下意識抱住了那個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總裁辦公室里的人。
什麼況???他們老板不是不近嗎??
察覺到四周投來的無數道好奇的目,姜知漓把頭深深埋在了他的前,恨不得找個地方鉆進去。
Advertisement
太丟人了太丟人了。
本來悄悄坐飛機過來沒告訴他是想準備一個驚喜,誰知道傅北臣的辦公室里還會進來這麼多人,安這個不靠譜的!!
空氣短暫地凝固一秒后,傅北臣最先反應過來,面容冷淡而鎮定,沒有過于明顯的緒顯。
覺到懷里的人恥得不行,他的掌心輕輕過微的后腦勺,帶著些安的意味。
他語氣平靜道:“抱歉,我太太有些調皮。”
“今天的會議暫時延后。”
聽到太太兩個字,眾高層瞬間如石化了一般。
說完,傅北臣便拉著的手腕進了辦公室,沒再理會后眾人是什麼表。
門合上,隔絕掉外面一切視線,也聽不見聲音。
這下姜知漓才終于好意思抬頭了,長舒一口氣,抬眼就對上他深邃的視線。
搞什麼啊!!他怎麼這麼淡定?!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啊......
從昨天下午掛掉倪靈的電話之后,姜知漓就第一時間聯系了安,然后想也沒想地就要買機票飛北城。
可昨天沒了直飛的航班,只能不停地轉機,折騰了快一天才到。
一直沒告訴他,就是為了給他一個驚喜,可這人怎麼回事!!
傅北臣垂眸盯著,沒有說話,幽暗的眸中似有暗涌,被深深抑著。
“怎麼突然來了?”他忽然開口,嗓音有些發啞。
姜知漓有些不滿他的反應,卻還是忍不住角上揚的弧度。
看著他,眼睛亮亮的,一板一眼地說著反話:“我覺得你可能想我了,所以我就來了呀。”
其實是想他了才對。
見他的神晦暗莫辨,姜知漓歪了歪頭,故意說:“不過看你好像一點都不期待我來的樣子,那我還是走吧。”
說完,裝模作樣地就要轉離開,并沒有看見男人雙眸中濃稠晦的緒,像是即將掙牢籠的野。
轉的一剎那,的手腕忽然被人拉住,還沒等姜知漓反應過來,整個人就被抵在了辦公室的門上。
力道是從未有過的強勢和霸道,甚至不給一一毫反應的機會,與上次那個淺嘗輒止的輕吻不同,他的指尖扣著的下,不給半退的余地。
他的瓣溫熱,舌尖急切地探進的牙關攻城掠地,滾燙的氣息瞬間將侵占。
姜知漓本招架不住,渾的力氣瞬間瀉下來,如果他的手沒有扣在的腰間,恐怕下一刻就會癱坐在地上。
辦公室外都是人,姜知漓心驚膽戰,好不容易回過神,剛抖著抬起手想推他一下,就被他察覺到意圖,手腕被牢牢摁在了門上。
這下徹底沒法掙扎,只能被地承他熱烈又蠻橫的吻。
姜知漓也想不明白,傅北臣到底被什麼刺激到了,能讓一個向來冷靜自持的男人在肅穆的辦公室里,幾乎快要將吻昏過去。
耳邊都是他重而灼熱的呼吸,讓的大腦一片空白,無意識地發出一輕。
像是被的回應刺激到,傅北臣終于停下作,輕地含了含的瓣,剛剛的霸道和強勢忽然消失了。
他修長的手指微微抬起的下,幽暗的眸里盛滿的倒影,嗓音低沉得發啞。
“那現在呢?”
姜知漓還沒回過神,雙眼迷蒙地看著他,沒聽懂他的話。
傅北臣眼底的/尚未褪去,復又低下頭,又在的瓣上輕咬了下,帶著懲罰似的意味。
他啞聲問:“能看出來我很期待了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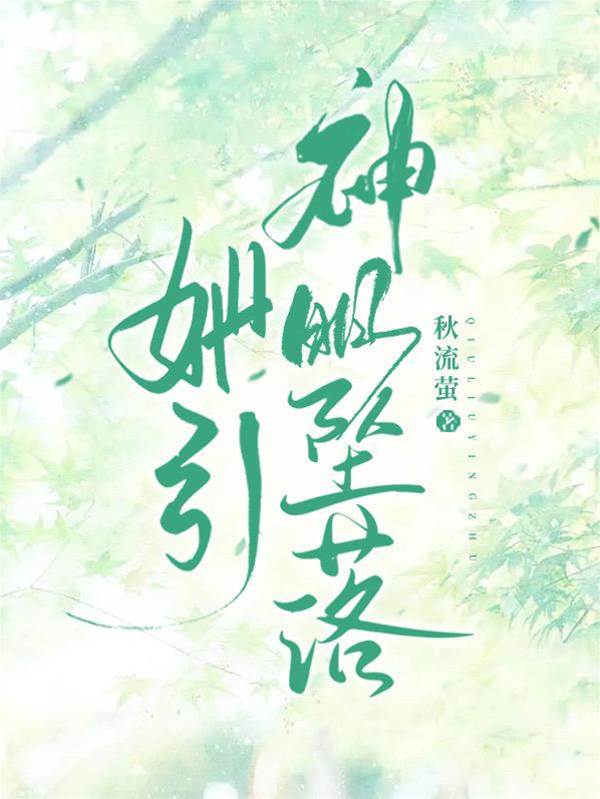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