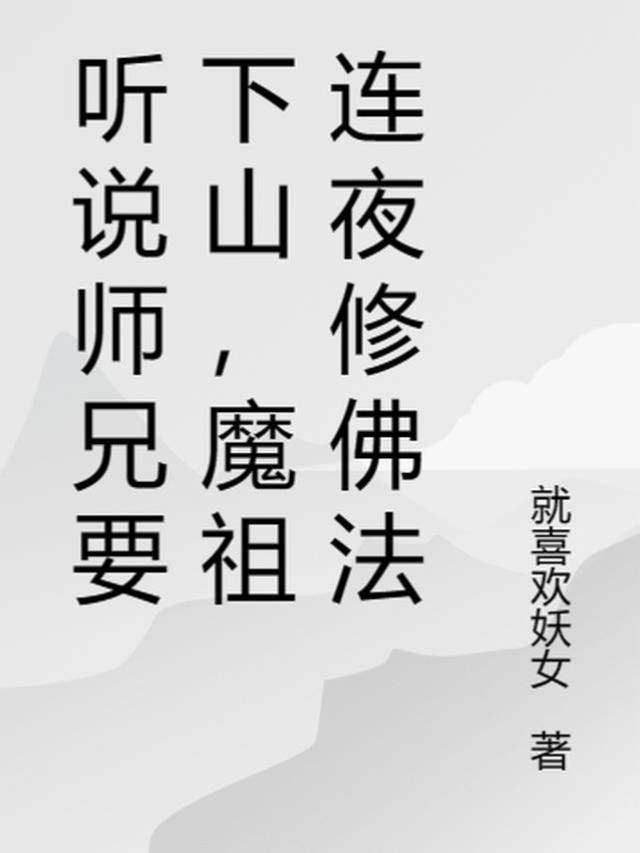《豪門前夫痛哭流涕求我復婚》 第一節課時,秦遇當時給她發的那條消息。
阮甜上了學校網查了自己的期末績,明晃晃的六十一,代表了秦遇最后的良心。
阮甜剛放假沒多久,就生病了。
一向不錯,從小到大都很冒發燒,這回因為初雪來臨,興的在雪地里撒了一晚上的歡,把自己給凍冒。
吃了藥不見好,反倒是燒的越發厲害。
腦袋暈暈,昏昏沉沉。
手機上的消息都沒看沒回。
秦遇給打的電話自然也就沒有接到。
阮甜窩在被子里睡了兩天,燒的迷迷糊糊,還不知道家的門被人用碼鎖給解開了。
秦遇一進臥室,見大床中間拱起來的這團,心中松了一口氣,沒事就好。
他用指尖掀開被子一角,阮甜的臉睡的通紅。
秦遇用手探了探的額頭,眉眼神冷了下去,隨即就要將阮甜從被子里拽出來。
意識不清時還記得要抓著被角,不肯離開的床。
秦遇忍著不耐,說:“你發燒了。”
話音落地,秦遇自嘲的笑笑,“你現在也聽不懂我說話。”
他的指骨用了點勁道,用被子把阮甜裹了起來,從床上打橫抱起,用腳踢開房門,抱著下了樓。
司機是個有眼力見,趕忙上來問:“是要送到醫院去嗎?”
Advertisement
秦遇沉,“直接開回老宅,讓家庭醫生過來。”
司機應了聲是。
一路無聲。
司機通過后視鏡往后看了兩眼。
大爺板著張冷冰冰的臉,擰著眉,出聲催促,“開快點。”
司機不敢分神,忙道了聲好。
不到半個小時,便開到了秦家的老宅。
家庭醫生比他們到的更快,已經在二樓的臥室里等著了。
秦母見兒子抱著阮甜急匆匆的上樓,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忍不住問:“甜甜沒事吧?”
秦遇答了聲:“發燒了。”
秦母也跟著上了樓,“這孩子一個人住,也沒個人照顧,你怎麼也不多看著點?”
秦遇沒吱聲。
家庭醫生看過之后覺得沒什麼大問題,開了退燒藥,又給阮甜打了個吊水,“按時吃藥就沒問題了。”
阮甜額頭上的溫度似乎退了點,睡著睡著又把自己悶在被子里。
秦遇把不過氣,強的將從里面提了出來,將前的被子折了起來,免得還想個袋鼠似的往里鉆。
阮甜好像做了一個很漫長的夢。
夢見了自己剛回來的那一天,明面上淡定,心里其實非常的不安。
周母牽著的手,從車里下來,走進一棟奢華的別墅樓里,指了指左邊這棟說:“這里從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Advertisement
然后又指了指另一邊說:“那是你秦遇哥哥的家,不知道他今天有沒有去上學。”
僵,跟著周母進了客廳,又到了的臥室。
行李放下之后不久,周母便帶去隔壁同鄰居打招呼。
周母和其他人在寒暄,覺得無聊,也不喜歡那些人打量的眼神,那天又有些頭痛,很不舒服,便尋了個由頭溜了。
在那棟屋子里瞎轉了兩圈,找不到回去的路。
好像聽見某間臥室里傳出來的劇烈聲響,大著膽子靠近,著耳朵想聽的仔細一些,門被人暴的從里面打開,腳下一個趔趄便摔到了地上。
年坐在椅上,冷冰冰的眼神注視著的臉。
摔了一跤也沒有生氣,反而是看見他坐在椅上覺得他很可憐。
年卻當著的面站了起來,把手到了的面前,“起來。”
記得那雙手沒什麼溫度,起來涼涼的。
抓著年的掌心慢慢從地上爬了起來,低聲說了句:“謝謝。”
轉要走時,被他住了。
年從他的屜里翻出了一盒藥,作一點都不溫,丟給了,“記得吃藥別病死了,后門在花園口。”
Advertisement
愣了一下,沒拿地上那盒藥,順著他指的路就跑了。
阮甜夢見了十七歲的秦遇,后面又夢見了十七歲的沈赦。
醒來時,腦子又又沉很不舒服。
阮甜睜開眼就看見坐在床邊的秦遇,他的臉和十七歲好像沒什麼分別,只是變得更鋒利,更加冷酷。
秦遇手里端著杯熱水,另一只手掰著的下,輕聲吐字:“吃藥。”
阮甜恍惚了好久,就覺自己好像還在做夢。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16 章

絕世農家女
一聲驚雷讓陳佳這個曾經的女學霸,現在的女白領,穿越到一個架空時代的農女小包子身上,重男輕女的奶奶,重病的爺爺,貧窮和不平等充斥著整個農家。她要改變,山中奇遇讓她擁有絕世武功精神財富和巨大的秘密,江、史、孫、楊,四大家族,四大美男,讓她一步一步開啟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75.8萬字7.92 133988 -
完結397 章

快穿之寵愛
作為一個合格的女配,就該惡毒邪惡千方百計各種作死勇敢犧牲給真愛們送上神助攻? 白曦笑了。 虐渣甜寵快穿,人人愛上我係列 甜甜寵寵
40.2萬字7.58 5944 -
完結524 章
穿越女法醫,王爺驗個身
一朝穿越,居然成了戴罪的丫鬟,沒關係,琳瑯帶著法醫知識引領仵作潮流,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賺不完的銀子。 一不小心竟讓自己成了王爺的債主。 「本王府中銀錢都交於了你,不如剩下的銀錢用本王來抵,如何?」
93.2萬字8 30068 -
連載4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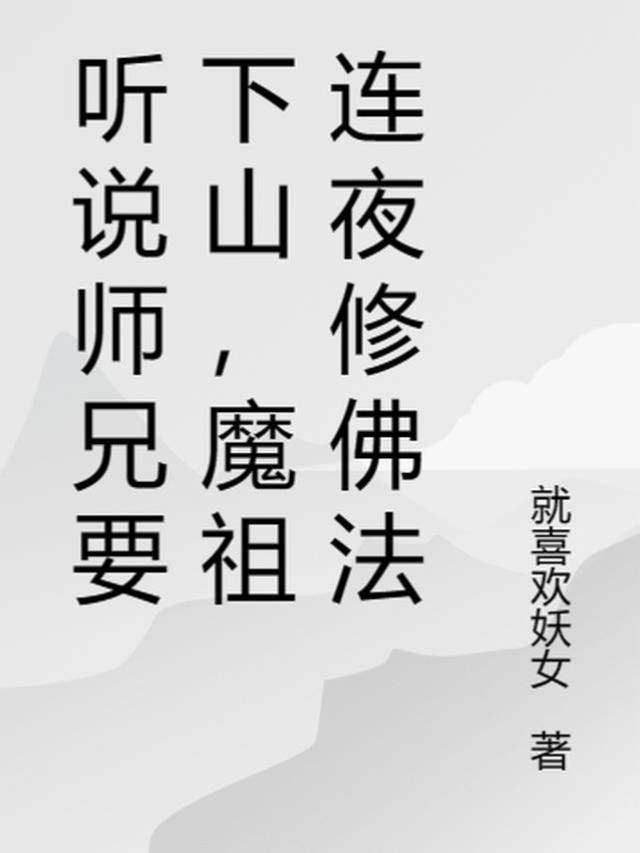
聽說師兄要下山,魔祖連夜修佛法
王慧天,自卑的無靈根患者,劍術通神。自他下山起,世間無安寧!魔祖:“啥?他要下山?快取我袈裟來。”妖族:“該死,我兒肉嫩,快將他躲起來。”禁地:“今日大掃除,明日全體保持靜默,膽敢違令者,扔到山上去”向天地討封,向鬼神要錢。燒一塊錢的香,求百萬元造化。今日不保佑我,明日馬踏仙界……
87.8萬字8.18 148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