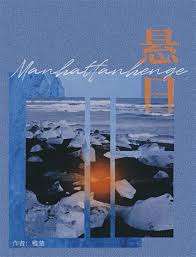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願以山河聘》 第13章 斷袖
半個時辰前,姬越還堅定不移地想,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半個時辰後,姬越凝眉著沉睡中的青年背影,思考自己為什麼會那麼衝地把人回來。
如此放肆,簡直不把孤放在眼裡。
就該凍死他。
姬越扯過被子,不忿地想。
睡著了看你還怎麼跟孤搶。
衛斂確實沒再和姬越搶。
他闔著眼,一副倦容,呼吸均勻綿長。
青年對裡側臥著,一手枕著腦袋,夢中蹙著眉頭,微微蜷。
被子被姬越卷走,他大半子都在外頭,襯著一團的姿勢,更顯單薄。
姬越清楚,這是人在不安狀態下會有的表現。
公子斂初來異國,頭上隨時懸著一把刀,又得與他這個兇名在外的暴君周旋,怎麼可能真正放松。
你也有怕的時候。
姬越一邊嗤笑,一邊將被子重重扔回衛斂上,將人蓋得嚴嚴實實。
他掀開簾子,衝床頭燃著的蠟燭吹了一口。
室頓時一片昏暗。
姬越這才躺下來,抓過被子另一端,閉上眼睛。
他其實並不排斥衛斂。
如果有一個人,他是世上唯一靠近你不帶殺意,擁抱你無所畏懼,把你當作尋常,與你嬉鬧玩耍。
你怎麼舍得推開他。
在靜謐與黑暗裡,本該睡的衛斂爭開雙眸,眼中一片清明。
他攥了攥蓋在自己上的錦被,抓出幾道褶皺。
良久才再次闔目。
一夜酣眠。
天黛青泛起微亮,一連落了幾日的雪終於歇了一口氣,雲層後出幾縷日。
養心殿院子裡,幾名宮正在掃雪。其中一個乾完活,拄著掃帚,對另外兩人招了招手。
“珠瑯珠,過來過來,跟你們說件事兒。”珠玉一臉神。
Advertisement
珠瑯和珠相視一眼,圍上前來。珠好奇道:“什麼事呀?”
宮裡的日子無聊。若有什麼八卦,們都是很樂意聽的。
珠玉四下張了眼,將手掌抵在邊小聲道:“這事兒我憋了一夜,必須得跟你們講。青竹閣過來那位呀,可是得寵了!”
珠噗嗤一笑:“珠玉,這消息宮中人人都知道。陛下不寵那位還能把人接到這兒?你這不是廢話麼!”出些興意闌珊的表來。
珠玉急道:“哎呀不是!我昨夜在書房伺候,大臣們送來一摞人畫卷,陛下讓衛侍君挑,衛侍君說他挑不出,那些人都沒他好看。你們猜陛下怎麼著?”
珠驚訝:“這麼大膽?陛下罰他了?”
“哪裡呀!陛下不僅沒生氣,還說只要他一個,還,還——”珠玉說到這兒頗為人,“還將衛侍君就放在那堆放奏折的桌上幸了!”
這話就牽扯到床笫之事,幾個未經人事的宮一呆,又是臊,又是好奇。
珠年紀輕些,膽子也大,追著問:“這如何得知?當著你們的面?”
“煞人也!我等自是被陛下屏退了,可我是走後頭那關門的,門裡看過去……真的,我親眼瞧見的!”珠玉低聲音,“後來湯泉宮裡陛下在池子裡又……哎呀,死人了。”
珠瑯聽著,言又止。
珠半信半疑:“真的假的?不過說真的,衛侍君生的那模樣,我見了也喜歡。”
“噓!”珠玉趕捂的,“那可是陛下的人。”
珠笑著躲開:“怕什麼?這院子裡沒別人。”
“應該是真的。”珠瑯溫婉,還未語臉就先紅了大半,“實話說罷,昨晚我守夜,撞見彤史匆匆忙忙從裡頭出來,瞧那樣子,應是撞見陛下和衛侍君正行好事呢……而且……”突然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Advertisement
珠玉珠都催道:“而且什麼呀?你別賣關子!”
珠瑯索一口氣說下去:“而且今早我聽珠月姐姐說,進去伺候陛下更時衛侍君還在床上睡著,陛下專程吩咐不要吵醒他。許是,許是昨夜累著了。”
三名宮一時都有些靜默。
珠小聲道:“一日承三回皇恩,衛侍君他也不知不得住……”
這般不分場合、不分晝夜的寵幸,陛下可真是……厲害了。
衛侍君也厲害的。
“你們不乾活在這兒聊什麼呢?”珠翠一進院子就見三名宮圍在一起,面紅耳赤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三人忙一字排開:“珠翠姐姐。”
珠翠是養心殿中的大宮,比們要高一等,們自然不敢在面前嚼舌。
珠翠覷們一眼:“都散了。”
“……諾。”
三名宮又各自分開,清理院子裡的雪。珠翠回著金碧輝煌的宮殿,搖頭輕歎。
公子確實是承了寵。可只要一想到那風霽月的人要此折辱,便覺得惋惜。
宮中沒有,秦王寵衛斂寵得高調,不過半日便傳揚開來。
瞧這趨勢,遲早能傳到宮外。
衛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姬越下朝回來的時候,就見青年已穿好裳,慵懶斜倚在榻上。一手支著腦袋,一手捧著書卷,垂目凝神,眉眼認真。
姬越問:“看的什麼書?”
衛斂眼皮也不抬,信手翻過一頁:“聖賢書。”
他這回連禮也不行了。
膽子愈發大了。
姬越也不多問,上前直接走衛斂手裡的書。
衛斂手中一空,略略抬了眼。
姬越低頭一看,目便是兩道白花花的人影疊在一起,四肢糾纏,行著魚水之歡。
Advertisement
姬越手一抖,把那書卷立時扔在地上,頓覺汙了眼。
他難以置信道:“……你管這東西聖賢書?!”
衛斂悠然道:“彤史今兒特意送了這男子之間的春宮戲圖給臣,讓臣好好學著點,才好服侍陛下更盡心些。”
他突然嚴肅:“臣認真抱著求知心態在學,怎麼就不是聖賢書了?”
衛斂眉眼一彎:“陛下,你耳朵怎麼紅了?”
姬越下意識去自己的耳朵,溫度正常的很,不紅也不燙。
他慣會掩飾緒,怎麼會輕易外。
姬越咬牙:“你耍孤?”
衛斂靠在榻上,笑得清朗開懷:“哈哈哈哈哈,陛下如此作態,莫不是從未嘗過這滋味兒?”
尋常貴族家,男子十三四歲就有負責教導人事的婢,更何況王室。
“怎麼,難道你嘗過?”姬越反問,心中卻不抱期。
……他也不知道他在期什麼,又或是不希什麼。
衛斂應當是有過的。
他是楚國公子,十三四歲時已經被妃收養,會有宮教他人事。
只要一想到青年曾和另一個子翻雲覆雨過,姬越就有點……不是有點,是很不愉快。
他思來想去,覺得衛斂現在名義上好歹是他的人。他的東西絕不許別人染指,就算是在屬於他以前。
秦王便是如此霸道。
誰知衛斂止了笑,說:“不曾。”
這回答姬越一怔。
“為何不曾?”
他是因為對太后送來的人不放心,衛斂呢?
衛斂坦然道:“因為臣是個斷袖啊。”
衛斂沒有喜歡過人,可他天生就喜歡男子,這點他自己最清楚。
姬越不聲地退後一步。
“你最好別喜歡孤。”
合作夥伴什麼的,扯上就最麻煩了。
Advertisement
被牽扯的人,總是會失去理智。而姬越從來都理智至上。
衛斂挑眉:“這話該是臣對陛下說。陛下可千萬別喜歡上臣才是。”
姬越立刻否決:“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喜歡上別人。
“是嗎?”衛斂勾,“那陛下為何從方才臣說自己不曾破且是個斷袖之時,角的笑就沒下來過?”
姬越一頓,才發現自己竟然是一直笑著的。
不是以往那種毫無意義的笑。
……是不自覺的開心。
姬越立刻將角平,試圖轉移話題:“你未免太過放肆,見了孤至今也不行禮。”
衛斂很順從道:“參見陛下。”
他就只是上說了句,沒彈過。
衛斂從來都不喜歡跪來跪去。第一日他和秦王完全陌生,不得已才跪了許久。如今只要一點點和秦王把關系混,秦王不會追究他偶爾的失禮。
姬越打量他:“衛斂,你初時還一副君子之相,這才三日,便顯出狐貍尾了?”
“臣天如此,不敢欺瞞。”衛斂有禮道,“初時不曾見您,有所拘謹,而今與您相,有所了解,自是無畏。”
姬越凝眸:“李福全在孤旁十二載,都不敢說了解孤。你怎麼敢。”
“衛斂,孤真不知你的底氣何來。可別再說把孤當夫君這種蠢話,孤不想聽到第二次。”姬越淡聲,包含危險的警告。
衛斂一頓,道:“那臣說實話。”
他倏然起下榻,目視窗外,語氣疏狂:“這天下多的是窮兇極惡之徒,忘恩負義之輩,利熏心之人,卑鄙齷齪之流。”
容極盛的人轉,含笑凝年輕的君王。院是大片的積雪,裹著冬日的寒冷席卷而來,被盡數擋在窗外。
窗是冰玉骨、風華無雙的公子,立在窗前,眉目清冷,般般畫。
他字字珠璣。
“人心至惡,你一樣不佔,我何懼之有?”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700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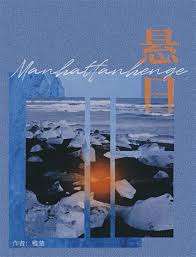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