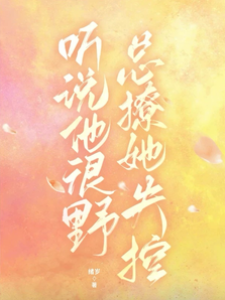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狙擊蝴蝶》 第69章 第六十九次振翅(“岑矜”)
下班回家前,岑矜特意去了趟附近的復古雜貨店,挑了對杯,準備帶回去當作給家里男大學生學上一小步的嘉獎。
結果一開門,還沒來得及拿給他看,自己先被當獎勵拆了。
不只是撕去紙皮,簡直快被拆筋剝骨,只能纏他腰,用一些不調的哦一聲聲贊頌他蓬發的生命力。
結束后,岑矜爽累加地癱在床上,心想著連卸妝的步驟都免了,反正臉上早被了個一干二凈。
而李霧已經去廚房給煮晚飯,香味無孔不地飄進房間時,岑矜側了個,把臉埋枕頭里笑起來。
太喜歡這種攻擊與發力了。
可能因為前夫的個相對斯文,慎重,不溫不火,在這些事上亦如此,所以李霧這種突然襲擊反讓更加新鮮盡興。
尤其是在沒有開燈的臥室把進床褥的時候,暗的環境讓周圍看起來莽莽榛榛,危機四伏,而年是一頭強勢矯健的雄豹,將撲咬,拖拽,直至徹底侵占。他毫不克制的激進與息,都讓意迷,甘當一只弱無力的獵,呼救又沉溺。
啊。
岑矜忍不住想要與友分,已經奪走了還不滿二十歲的小男友的子之。
春暢興得像個大母猴一樣嗷嗷:什麼覺?
岑矜思考許久,用四個字準概括:黃破裂。
春暢:靠?真的假的?
岑矜:當然夸張手法。
春暢除了羨慕得要死之外無話可說。
……
簡單沖了個澡,岑矜換了舒適的家居服,將頭發扎起,去廚房找李霧。
他在煎豬排,回頭瞥一眼,就笑了。
岑矜上前環住他勁瘦的腰,靜靜到他背后。一會,手不老實,探進前擺,與他的腹進行增溫流。
Advertisement
李霧結了下,低咳一聲:“姐姐……”
岑矜收回手,也松開了他,將茶幾上的杯拿過來,拆開,排放到桌上,想了想,又將李霧那只推至對面。
李霧擺完盤,端著兩份外形不輸日料店的豬排飯回來時,就看到了這只杯子。
全白款式,上面是因斯坦吐舌頭的黑白線條畫,圖案凸起,帶著些顆粒,背后則是公式。
他端詳一圈,不釋手,笑著俯視人:“給我的?”
岑矜支起下,輕輕頷首:“對啊,小理學家,給你帶學校用。天涼了,記得多喝熱水,健康萬事如意。”
李霧笑意不減:“好,”又看向手里:“你杯子上是誰。”
岑矜舉高自己的:“阿基米德。這套只有理學家圖案,為了跟男朋友湊對我將就著用吧。”
李霧開心極了,立馬將兩杯子洗燙干凈,倒了些甜滋滋的氣泡水回來。
兩人面對面坐著,邊閑聊邊吃飯,不經意間,岑矜的碗就見了底。
大約是李霧廚藝非凡,外里的口一吃就停不下來,又或者,是真的了累了,需要高熱量的食來補充力。
李霧問還需不需要,鍋里還有些飯與海鮮豆腐湯。
岑矜搖了搖頭。
李霧便將米飯與湯全部刨來,拌在一塊,低頭專心解決。
岑矜搭腮看著他吃,笑眼彎如兩道月牙。可真是三年如一日地喜歡看他的真人吃播。
見目一直鎖著自己,李霧有些不自在了,再度發問:“姐姐,你確定不吃了?”
“不吃,我很飽了,”岑矜雙手搭腹:“李霧,以后別我姐姐了。”
他小刷子樣的睫往上一,眼睛熠熠看向:“什麼?”
Advertisement
岑矜放下手,疊到桌面:“名字,全名。”
“哦……”他低應著,斂眼接著吃。
“啊。”岑矜催促。
李霧抬了下眉:“現在?”
“不然呢。”
他握著筷子,雙耳漫上一層赧,又了幾下脖子,還是沒喊出來。
岑矜歪頭困:“有這麼難嗎,昨天不是還很理直氣壯。”
李霧放下筷子:“那時候緒激,一下子就喊出來了。”
“這會就喊不出來了?”
李霧噤聲,醞釀一下緒,語速極快道:“岑矜。”
岑矜嚴聲:“我都沒聽清,看著我,好好說。”
年臉也紅了,了下,又抿,似下定決心,直視過來:“岑矜。”
他嗓音清冽,字正腔圓,平平常常的人名似乎都裹滿了意。
四目匯,岑矜心臟有一瞬斷拍,而后揚“嗯”了聲,約定:“說好了啊,以后都這樣我。”
李霧還是靦腆地笑:“嗯。”
岑矜腳出拖鞋,直了,在桌下攻擊他膝蓋:“你到底害什麼啊!”
“等會告訴你。”李霧繼續埋頭吃飯。
幾分鐘后,岑矜全失重離椅面他的時候,才明白過來。
趴在他肩頭嘰嘰咕咕:“不就換個稱呼嗎,有必要反應這麼大嗎?”
……
―
李霧適應得很快,臨睡前,他已經能面不改地親親人額頭,再跟說“岑矜,晚安”了。
岑矜也頗為用,好像出了一把鑰匙,讓他為這間屋子里能與自己平起平坐的男主人。
姐姐這個稱呼,除了是作弊一樣的存在之外,還容易讓平添優越。需要更為直觀的稱謂來警示自己,用以維系這段關系的公正度與平衡。
背在李霧懷里玩了會手機,岑矜聽見了他均勻的呼吸音。
Advertisement
的男孩睡著了。
岑矜往上拱了拱子,近距離平視李霧的睡容。他睫真是好長啊,還是直直垂下的那種,像黑夜的葦,覆蓋著一汪清澈的泉。
怕弄醒他,岑矜忍耐著,沒,又去欣賞他的雙,它們在清醒狀態下總會繃著,抿著,帶著多種緒下的克制,似一扇戒備的門扉,但此刻廓微揚,張開了松懶的,有可乘之機的罅隙。
岑矜一不看著,忽而又迷了。
無疑是他的,可這份到現在都像一杯分不明但澤人的尾酒,摻混著憐惜,需索,耽溺,始終不那麼合乎邏輯,只能且看且行。
極輕地了一下李霧角。
年眉心微蹙,畔的弧度更了,含糊地夢囈:“姐姐……”
岑矜以同樣分貝的嗓音認真糾正:“岑矜。”
李霧再無靜。
岑矜彎了下角,翻回去,打開微信。
眼皮一揚,發現自己給那位kol的好友申請已被通過,但他也沒有給自己發來任何消息。
岑矜擰眉心,主客氣地打招呼,并自報來路:周先生,您好。我是奧星的客戶經理岑矜,這麼晚還打擾您是為了昨天的視頻侵權事宜,先為此事向您深致歉意,然后想聽聽您的意見與訴求,看看我們怎麼以你最能接的方式理解決這件事,您看可以嗎?
發出去后,岑矜打算略掃眼他的朋友圈,鎖定對方趣向所在,好對癥下藥。可惜的是,周教授只開了三天可見,并一片空白。他的頭像與背景都是風景,頗中老年風,岑矜已在考慮明早要不要買點保健品。
周綏安并沒有冷著,但回應的態度也跟冷理沒多區別,甚至有點譏諷:你們不用在意。我轉我的博,你們發你們的視頻。
Advertisement
岑矜:“……”
想了下,直抒來意:可侵權況是真實存在和發生的,我們不想忽略它,這件事的確是我們的失誤,更是我們的錯誤。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跟您買下這個片段的版權,盡量小給您帶來的傷害與損失。
周綏安回:是要我現在報價?
岑矜呼了口氣:如果您方便的話,當然越快越好,因為您的微博影響力很不一般,但如果您現在不方便或者需要再考慮周詳,我們也會耐心等候。
周綏安說:那你們等等。
岑矜無言。
難搞。
岑矜腦袋飛閃過這兩個字,了會拳,最后還是客氣有加地回以笑臉:好的,期待您的回復。
放下手機,岑矜心那些溫存一掃而空,翻過去,李霧重新給自己充能。
李霧了,把攬住,按得離自己更近,無隙。
他軀高大,幾乎能圈住整個。
岑矜在里面,油然而生出一種被保護被容納的脆弱依賴,人不由恍惚起來,輕輕了聲:“老公……”
“嗯。”
年輕的鼻音迷迷糊糊,囈語般回應著。
岑矜一瞬夢醒,摑了下他結實的后背。
李霧也秒醒,大眼睛急急找到面龐:“什麼事?”
“你干嘛了?”
“我沒干嘛。”
岑矜裝一無所知,撓貓般撓他下:“你剛才嗯什麼,嗯?”
李霧笑意微妙:“我好像夢到你我……”
“什麼?”小心刺探著,怕他裝睡,這樣絕對面盡失。
年人不言不語,笑里浮著得逞,好像剛從全宇宙最妙的夢中。
他不敢明說,看來是真的當做夢了,岑矜寬下心來,抱住他輕聲道:“晚安。”
―
翌日早上,岑矜跟在李霧后頭起了個大早,打算跟他一起去F大,當面會會那位周教授。
傻等是最不可取的行業行為,眼睜睜看著產品口碑逐日貶值與掃地,只會讓客戶對他們的應急理能力從此懷疑。
到F大后,兩人在車里吻別,李霧預祝一句進展順利,就捎上背包一步三回頭地去教學樓上課。
晨氣疏朗,岑矜在校園里漫無目的地逛游,聯系上那位留校任教的老同學后,說明意圖,問怎麼才可以見到這位周教授。
幸而同學巧認識他本人,便從中牽線,約了頓三人上午茶。
面談地點在一間岑矜并不陌生的咖啡館。
暑假跟李霧確認關系第二天來學校找他時,就是在這邊辦公邊等了他一下午。
岑矜頭一個到場,挑了個線最好的卡座,耐下子等候。
半小時后,那位柴思明的老同學回了電話,說他們就到了。
剛掛斷,側窗頁已被人重叩一下。
岑矜了過去,明凈的玻璃后已站了兩個男人。
盡管柴思明離最近,并且第一眼就被認出,但視線還是不由自主飄去旁邊那人上。
岑矜有些意外。
因為這位周教授的外形超乎預料,并非想象中人如其名的儒雅學派男士。
他比柴思明要高,一駝大,五稱不上英俊,但整氛圍很是抓眼。
岑矜一下子無法揣出他的年紀,因為他的與姿態都偏年輕化,背不算直,看起來瘦削,散漫,隨意,氣質像極學生時代那種坐教室最后一排的差生。但他鏡片后的眼神從容不迫,這種從容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鑄就,需要經年累月的沉甸積累。
他頭發微蜷,被風吹,蒼白的手指夾了煙在吸,看眼岑矜后,便放下了,朝勾了勾,笑意似有若無。
岑矜回過神來,忙在掛上自打轉職來就練得爐火純青的最佳笑容模板,以此迎接他們。
煙已被男人在進門前撳滅或丟棄,總之,三人會合座時,周綏安手里已沒任何東西。
本還想近距離確認下香煙品牌的岑矜,此刻只得作罷。
岑矜再次自我介紹,也據境改換稱謂:“周教授,你好,我是昨晚聯系你的奧星客戶經理……”
周綏安看向:“岑矜。”
岑矜一怔,莞爾道:“對。”
“這麼急著要報價?”等服務員來點完餐,周綏安比還開門見山。
不知是天生如此還是后天吸煙所致,男人的嗓音略微嘶啞,好像聲帶里硌了砂。
岑矜也不打馬虎眼,直言目的:“主要還是急著讓你刪微博。”
“好啊,”周綏安隨口應下,而后從兜里取出手機,角微掀:“岑小姐,中午單獨請我吃頓飯吧。”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5 章

難以招架,裴總每天都想強取豪奪
【1V1 雙潔 強取豪奪 強製愛 男主白切黑 天生壞種 追妻火葬場】裴晏之是裴家的繼承人,容貌優越,家世極好,外表溫潤如玉,光風霽月,實則偽善涼薄,是個不折不扣的壞種。他從小就感受不到所謂的感情,不會哭不會笑,就連這條命都是拽斷了一母同胞哥哥的臍帶才留下來。裴家人都說他是沒有感情的瘋子,因此把人送到道觀養了十多年。直到他18歲那年斬獲大獎無數,才被裴家人歡天喜地接回來。都以為他會改邪歸正,殊不知,惡魔最會偽裝。*江予棠自幼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放在人群裏一眼看不到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了裴晏之的私人醫生。都說裴晏之性格溫柔,教養極好。江予棠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兩人交往過程中,他步步緊逼,讓人退無可退。江予棠含淚提了分手。可招惹了惡魔,哪有全身而退的道理。往日裏溫潤如玉的男人像是被惡魔附體,對她緊追不舍,把人壓在牆上,語氣又壞又惡劣,“你要和我分手?換個男朋友……”後來的後來,男人抓著她的手,小心翼翼貼在臉上,嗓音裏滿是祈求,“棠棠今天能不能親一下?”從此以後,上位者為愛強取豪奪,搖尾乞憐。【沉默寡言醫學天才女主X表麵溫潤如玉實則陰暗瘋批偽善涼薄男主】
22.6萬字8.18 17507 -
完結72 章

遲來童話
城南池家獨女池南霜從小千嬌百寵,衆星捧月,是洛城圈內出了名的矜縱任性。 偏偏在二十四歲生日這天,被池老爺子安排了一樁上世紀定下的娃娃親,未婚夫是洛城地位顯赫的謝氏掌權人謝千硯,據說明朗俊逸,只是鮮少露面。 衆人皆道這門婚事佳偶天成,老爺子更是態度堅決。 氣得她當場把生日皇冠扔在地上,放言: “我要是嫁給謝千硯我就不姓池!” 抗婚的下場是被趕出家門,千金大小姐一朝淪落爲街頭商販,自力更生。 在屢屢受挫之際,是隔壁的窮小子宋宴禮多次出手相助。 對方溫柔紳士,品貌非凡,且人夫感十足,除了窮挑不出別的毛病。 相處中逐漸淪陷,池南霜毅然決然將人領回家。 老爺子聽說後,氣得抄起柺杖就要打斷這“軟飯硬吃”小子的腿。 然而柺杖卻沒能落下來—— 窮小子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熟悉的臉。 “爺爺,”他溫柔地笑,“不是您說,只要我把南霜追到手,這門親事就還算數嗎?” 池南霜:???
24.8萬字8 160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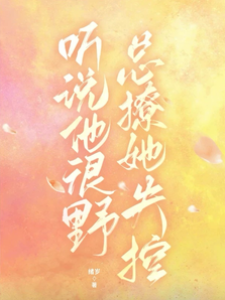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