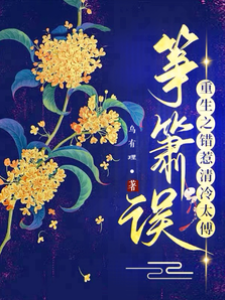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小狼狗飼養守則》 第85章
衙門口一對夫妻趕在天黑下去之前趕到, 正是林貴和徐三娘。
梁鴻義挎著刀從里頭慢慢踱步出來, 沒拿正眼看他們。才走兩步被壯著膽子上前的林貴攔住了, 一臉笑的問,“請問這位爺,不知衙門現在還理不理事?”
梁鴻義一邊想著家里媳婦做的飯菜, 一邊勉強耐下子答了一句,“早歇了,明天記得上午過來。”
而后便走, 再不理會。
林貴與徐三娘沒有法子,只得暗自咬咬牙在城里找了一家客棧準備住一晚上。
隔天一早。
全睿一路進了自己母親的院子里,面上帶著幸災樂禍的笑意,先請了安, 而后也不等他母親問起緣由就一鼓作氣的將心中所想說了出來,“母親您猜怎麼著?二房的那個昨天竟讓人去和林小娘子說了。”
全家大媳婦兒原本漫不經心的喝著茶,聽見這一句也停下了手中的作, 帶著些好笑的道,“還有這麼一回事,昨天一起說話的時候卻沒有提起呢,你怎麼知道的?”
全睿還是笑,“見著靖郎了,你都不知道他那臉黑的和什麼似的, 若不是咱們家的人,說不準還要吃他一頓排頭。”
“二郎他若說起來倒也不是和羨娘不相配,只不過這相配也就相配在這一時, 家里若是分家,二郎他攏共也拿不著多東西,自己又是個溫溫吞吞沒有野心的,往后眼見著吃老本,羨娘卻是轉眼就要飛出清溪鎮的人,兩個怎麼能一樣……”全家大媳婦道,“就是你我當年也沒敢上門提呢,別說他了。”
全睿聞言嚇得連忙擺手,“母親,這樣的話你可千萬別說了,我媳婦兒聽見了要同我生氣不說,若是給靖郎知道了恐怕真要沒得好過了。”
Advertisement
這邊說話的聲音漸漸歇了下去,衙門那里卻是正熱鬧起來。
林貴與徐三娘兩人戰戰兢兢的站在衙門堂中,仰面同老爺說明,“我們林家就那麼一份祖屋,因為我堂祖父那邊就一個孫,故而長輩們做主將這祖屋轉到了我的名下,只是那個時候手續匆忙了些,沒有弄仔細,比如房契地契一類的還沒有轉我的名字,所以今天特意帶著字據過來講這事托著老爺理一理次序,免得以后有什麼誤會。”
“那祖屋是你堂祖父建的?”座上的人勉強抬著眼皮,“這都快出了五服的親戚了,就算那邊只一個孫也……罷了,誰知你們家里是什麼事,你將字據拿來給我瞧瞧。”
林貴連忙將手上的字據遞上去。
縣仔細看了,點頭道,“這字據也,不過你堂祖父家里的后人到底還在,雖說子要外嫁,可現在還沒嫁,這樣吧,你去將人找來,兩方的人都在場,我再主持將字據變了。”
林貴面難,徐三娘連忙接著道,“大人,這恐怕有些困難。”
縣反問,“這怎麼說?”
“這是長輩的意見,那時候他那堂妹還未曾出生,如今他堂妹也都十六歲了,我們估著人家恐怕不愿意將祖屋讓出來……雖說如此,可是我們考慮這到底是長輩當初的想法,且堂妹不日就要嫁人,林家就這麼一個祖屋,我們就怕到時候讓外姓人占了便宜。”
“千般理也要讓人過來給我問問話,怎麼好不明不白的就將事辦了?”縣睜大了眼睛,終于出一點不耐煩的模樣,“你們說這堂妹住在清溪鎮上,那請人也容易,就給我報上名字來,我這兒自然有差去請人。”
Advertisement
林貴沒有法子,只能報上了林羨的名字。
聽到這里,原本懶懶散散站在一邊的梁鴻義才打起神,皺著眉頭看向林貴。而后他站出來請命道,“大人,不妨讓我去。”
個人罷了,誰去皆是一樣,縣擺擺手隨了他。
梁鴻義還沒先去林家小院,而是去運館那邊找了林靖。他將前后的事和林靖說了清楚,再讓他回去陪林羨一塊兒出門。
林靖遠沒想到林貴那邊還有這樣的膽子胡攪蠻纏,將白的說黑的,他又不想讓林羨為這樣的腌臜事煩心,是以先隨梁鴻義去了縣衙,沒和林羨招呼。
林貴和徐三娘在縣衙里面等的心慌,須臾聽見外面傳來人聲,連忙轉頭去看。只見梁鴻義與一個英武小郎君前后進堂中,卻不見什麼小娘子。
“梁鴻義,這不是你的徒弟林小郎君?”縣見過林靖幾次,因為林靖剿匪有功還讓他了上面的嘉獎,是以對林靖頗有些好,“林郎,你來這里做什麼?”
林靖簡單行禮,道,“回稟大人,林羨正是家姐。”
他上氣勢不凡,帶著銳利的煞氣,林貴低著頭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心里更是后悔加害怕,覺得自己這趟來錯了。不想后頭縣的一句話卻峰回路轉。
“原來如此,”縣道,“不過你前些日子要出林家戶籍自立門戶,昨天晚上我已經將文書擬好,你不是林家人了。”
林靖一怔,全沒想到這件事會在這里砸了自己的腳。
于是這下沒有法子,便又只能讓人去找了林羨過來。
前后兩趟有人進衙門,林羨又是在馥郁鋪子里面找著的,不百姓聞著看熱鬧的味兒就過來了,探頭探腦的圍攏在縣衙口觀。
Advertisement
林羨的印象中沒有面前這對堂哥堂嫂的半點影子,對他們的說辭也覺得莫名和稽,“我的父親直到去世之前也未曾同我說過祖上有過這樣的約定,后頭我從沒回去過也是因為家里早已經將祖宗牌位都請到了清溪鎮上,祖屋我以為是一直空著的,不想原來堂哥堂嫂已經安穩住了這麼些年。”
“那時候你還小,未曾聽說過也是尋常,”林貴道,“只是大人之間的字據也都已經立好了,你現在可不能抵賴,否則毀了長輩的名聲。”
他盡量把話說的重一些,好讓林羨心里能犯怵。
卻不想林羨全不怕,反還要問,“堂哥說有字據,字據在何,可有我父親的親筆?家里還存著不父親當年的書畫字帖,若是你的字據上能夠有所對照,確實是我父親的筆記,那麼地契與房契自然都給你了,否則也不好辦。”
字據上除了族長的筆跡,哪里還有其他人半點痕跡。
林貴自知理虧,話鋒一轉說起另外一套,“這祖屋空空這麼些年,你未曾回來過一趟,都是一脈相承,怎麼就容不下我們了?連空著都不舍得給我們住不,你在清溪鎮家大業大,轉頭就忘了家里的曾經疼你護你的親戚,卻不想如今還要將人到這樣的份上。”
此般指責一出,人群之間竊竊私語頓時大盛,多有說的是林羨如今并不缺這點房子,手上又不錢,該容人一些。
林羨聽在耳朵里覺得可笑,面上冷淡的道,“我的確未曾回去一趟,可祖宗牌位我也一天沒有忘了打理,我如何容不下堂哥你們,我是容不下你們不聲不響在里頭住了這麼多年,還是容不下你不僅要安穩住我家祖屋還要反告我到府妄圖將之占為己有?
Advertisement
我在清溪鎮‘家大業大’,我挨凍的時候可曾見過一個親戚的影子?就連我父親母親離世讓人特意傳了口信回鄉,也沒一個人過來瞧過一眼,如此種種怎麼反了我的過錯?”
頓了頓繼續道,“若是用胡攪蠻纏就能占理,若是當下誰過的好些就是罪過,這世間還有什麼公平話好說?”
這般梳理下來,原本碎碎說話的人群也一下安靜了不。
林貴被林羨說的啞口無言,一時支支吾吾無從反駁,縣也拍了驚堂木,下了定論,“林貴若拿不出其他證據來,房契地契便維持現狀不變。”
他說完要退堂,林羨道,“大人請等一等,我還有一事要說,我從前并不知道祖屋被人強占,如今知道了便不能夠坐視不管,還請您做主,將無理侵占我家祖屋的人趕出去,還我一個清凈。”
林貴聽到這句眼前差點兒一黑,徐三娘已經在他懷里哭得昏天暗地。
縣一愣,略微思索一番,“也在理,那就改如果林貴不能拿出其他證據證明祖屋已經移轉,那就不能繼續住在里頭,退堂。”
驚堂木拍下,一切落了定論,林貴不蝕把米,好一陣子了清溪鎮上眾人津津樂道的談資。
作者有話要說: 林貴徹底走了。
還有一更會有時間跳躍。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30 章

傾世妖妃:纏上精分九千歲
他,是權傾朝野的東廠九千歲,忍辱負重,只為報滅國之仇。 她,是離府煞星轉世,身懷奇絕黃金瞳。 他滅她滿門,她害死他心上人, 他強娶她為妻,她誓要讓他失去一切! 他恨不得她死,她恨不得他生不如死! 這兩人恨透彼此,卻又一起聯手屢破奇案。 她的黃金瞳可以看透世間萬物,獨獨看不透一個他。 他對天下皆可心狠手辣,唯獨一次次欺騙自己不忍殺她!
92.7萬字8 15298 -
完結135 章
無上帝寵
【暫定每天中午十二點更新,如有變化作話、文案另行告知~】《無上帝寵》簡介:京城第一美人烏雪昭,膚如雪,眉如畫。她性子雖嫻靜,不動聲色間卻能勾魂奪魄,媚態天成。只可惜意外被男人破了身子。養妹烏婉瑩聽到流言十分心疼,從夫家趕過來安慰:“姐姐,你別擔心,我挑剩下的男人里,興許還有肯娶你的。”外頭人也一樣,都等著看烏雪昭的笑話。甚至還有人說:“美麗卻不貞,一根白綾吊
41.6萬字8 9699 -
完結487 章

退婚后,修仙女配靠彈幕翻盤了
宋錦抒胎穿到了古代,卻沒想到有一日未婚夫上門退婚,看見他頭頂上竟然有滾動彈幕! 【氣死我了,這一段就是逼婚的場景了吧!】 【惡心的女人,長得都像個狐貍精!就知道天天貼著男人跑!】 宋錦抒:!?? 她怎麼就是狐貍精,啥時候倒貼了,還有這些彈幕憑什麼罵她!? 宋錦抒這才知道原以為的普通穿越,結果竟是穿進一本修仙文里,成了里面的惡毒女炮灰! 不僅全家死光。 哥哥還成了大反派! 宋錦抒氣的吐血,因為一個破男人,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真當她傻? 退婚,果斷退婚! 【叮!恭喜宿主激活彈幕系統】 【扭轉較大劇情節點,難度:一般,獎勵極品健體丹×1,黃級雁翎匕(首次獎勵),屬性點:力量+1,防御+1】 擁有了彈幕系統,只要她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原定命運,系統就會給出獎勵,憑借這個金手指強大自己,追求大道長生它不香嗎? 宋錦抒立志決定,認真修煉成仙,什麼男人都全部靠邊! 然而她卻沒想到,自家性子冷漠的哥哥宋錦穆,卻對她退婚的事耿耿于懷,竟然成天想收刮美男塞給她。 宋錦抒:“……” 球球了,現在她一心向道,真的無心戀愛啊! ps:女主低調,但不怕事,非圣母,慎入
98萬字8.18 18155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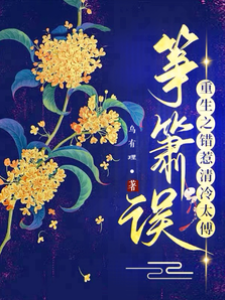
箏簫誤:重生之錯惹清冷太傅
【重生】【1v1雙潔、HE】原名:《箏簫誤》【深情克制“高嶺花”權臣✖️堅韌勇敢“不死鳥”千金】 *** *** 死光了男丁的祝府,窮的只剩花不完的錢。 樹大招風,孤立無援,前世被太子滿門抄斬。 一朝重生,祝箏為了保全全家,順了祖母招婿的美人計,生米煮熟飯,討個平庸的夫婿聊作靠山。 春酒助興下,紅羅帳燈昏,一夜良宵暖…… 但是……等等!哪里出錯了? 誰能告訴她……晨起枕邊人,為何不是祖母的安排? 而是當朝權臣,太傅容衍? —— 深山雪夜,月下梅前。 容衍給祝箏講了一個故事。 癡情的妖君與山神做了交易,換回他的公主死而復生。 祝箏凝眉:“他交易了什麼?” 容衍:“不重要。” 祝箏:“怎麼會不重要?” “公主不知道,所以不重要。”他目光沉靜,淡淡道,“妖君不在乎,所以也不重要。” “那什麼重要?” 容衍抬眼,眸光若皎皎冷月,籠罩著眼前人。 良久,道出兩個字。 “重逢。” - 情難自解,愛是執迷不悟,覆水難收 #非傳統重生文,立意“純愛萬歲,自由萬萬歲” #男追女,究極暗戀、蓄謀已久、甜寵微虐、復仇、沒有火葬場的漫漫追妻路、無雌競、非嬌妻、非女強、非強取豪奪、女主輕微回避型依戀(請自行排雷)
37.5萬字8 1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