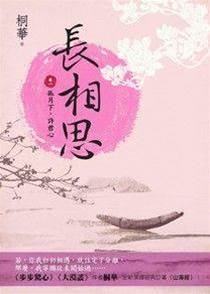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皇後劉黑胖》 第15節
是蔡諸葛原來不要的那一個?”
“難怪呢,換了我,也要豆腐西施啊。”
“啊呀呀,這人好潑辣,被男人甩了,居然還跑到婚宴上來砸東西!”
永福怔然看著地上的茶壺碎片,了,卻沒有說出話來。
“永福,你年紀也不小了,怎麽還這麽看不開呢?”
永福了幹的:“你……不是你請我來的麽?”
蔡諸葛驚愕地睜大眼睛:“我請你來,是看在我們街坊一場的份上,請你喝一杯水酒,並沒有請你來砸東西啊!”
“我……我隻是不小心倒了……”
蔡諸葛對永福的解釋恍若未聞:“唉,其實我送你張請柬隻是一片好意,你就算是不來,我也是可以諒解的。可是你現在搞這樣,豈不是讓我臉上無?唉,永福,若是換了旁人,隻怕現在已經將你打出門去了。看在你也有可憐之,我就不跟你計較了,你還是走吧。”
眾人點了點頭,互相道:“是啊,也隻有蔡諸葛這樣的好人,現在還能跟好聲好氣地說話。”
永福扁了扁:“我不就是打了一個茶壺麽?”
蔡諸葛語重心長地歎了口氣,還要說什麽,他旁蓋著紅蓋頭的新娘子卻一把將蓋頭掀了起來:“一個茶壺?這可不是普通的茶壺!你要走,先賠了我這茶壺錢!”
眾人嘩然:你這茶壺能值幾個錢?
豆腐西施擰著小腰,翹著尾指,從地上拈起一塊碎片:“大家瞧一瞧,這是我從娘家陪嫁過來的茶壺,哥窯出來的的,一個要二兩銀子呢!”
那水汪汪的桃花眼往永福上一繞:“打斷婚宴的事,我和我家相公就不追究你了。快賠銀子來吧。”
永福瞪著那碎片看了很久,並沒有看出它究竟是哥咬出來的還是弟咬出來的。可是豆腐西施言之鑿鑿,永福也隻有認命地往袖中去。
Advertisement
了許久,隻出一錢銀子。
“老蔡啊,我今天是來喝喜酒的,上怎麽會帶錢呢?”永福可憐兮兮地著蔡諸葛。
蔡諸葛有些心,將那一錢銀子收在手裏,道:“娘子,一錢銀子就一錢銀子吧,剩下了,讓改天再補。”
“不行!”豆腐西施柳眉倒豎,“誰知道改天還認不認賬?除非,讓當場立據畫押!”
“對,立個字據!”
“寫個借條!”
人群裏同一條街上的小年輕門們嘻笑著起哄起來。
永福就像一隻衰老的貓,被到了角落裏。
“我……”
“那個……各位百姓……”一個錦玉服的年公子吭哧吭哧地從人群外頭進來,手中握著扇子作了個揖,正待說什麽,一聲驚雷並地而起。
“寫你個兒!”
年公子的臉立刻像被霜打的茄子,白裏紫。他轉,著那聲音的出,目中出不可思議的芒:“皇嫂……”
那一聲皇嫂淹沒在眾人的驚呼中。一個神抖擻的小黑胖撥開人群,來到了繡娘永福的麵前。
“娘!”
永福怔怔地著眼前無論是廓還是細節都和自己別無二致的小黑胖,良久,眼中淌下淚來。
“黑胖……”
“娘!”金眼睛裏也溼潤了,手抱住自己家黑黑胖胖的娘,過了許久才緩緩鬆開。
“我的乖兒,你總算回來了!”永福破涕而笑。
“娘啊……”金懇切地著永福的眼睛,歎了一口氣,“耗子拜堂有什麽好看的?幹嘛跑到這裏來惹一?”
豆腐西施的桃花眼立刻變了三角眼:“你罵誰?”
金的眼睛在豆腐西施上上下一繞,半晌,漫不經心地笑起來:“你說我罵誰?”
豆腐西施的臉青了:“你們娘兒倆今天是來砸場子的?”
Advertisement
“當然不是。”金搖頭。
豆腐西施臉稍平,以為金會說些服的話。
然而金卻施施然道:“我娘是來喝喜酒的,我才是來砸場子的。”
起剛才豆腐西施拿著的茶壺碎片,看了兩眼:“二兩銀子一個?”
“雲重,你上有多銀子?”
段雲重苦著臉,捧出自己的腰包,
金也不客氣,從裏麵出兩錠金元寶,往桌上一扔:“這裏所有的茶壺,我包了。”
“雲重,砸。”淡淡的吩咐聲送進段雲重耳朵裏,段雲重還未反應過來,一個茶壺碎在他腳邊。
“皇……”段雲重被嚇住了。他見過風萬種的人,沒有見過瘋起來這麽有種的人。
“你不砸,是要我一個人把它們砸麽?”金了手腕,而後抓起鄰桌上的兩個茶壺,啪地摔在地上。
“……”眾人呆若木。
豆腐西施和蔡諸葛都張大了,不知道是被金的架勢鎮住了,還是被那兩錠金元寶鎮住了。
段雲重盯著他家勢如破竹的黑胖皇嫂,驀地臆中升起豪無限。
“好,我們一起砸!”
眾人繼續呆若木。
婚宴,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這兩個穿著講究的男,怎麽是兩個瘋子呢?
當段雲嶂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剝繭順藤瓜找到這個名黃家巷子的神奇所在時,局麵已經超出了每一個人的控製。
他看到他隨和可的弟弟滿場竄,抓到瓷就往地上扔,口中還大著:
“二兩銀子一個!”
太池水心涼
皇帝陛下很生氣。
賠了錢,收拾了犯罪現場,另外將嶽母大人平安送回小院,皇帝陛下將犯婦——老婆一名,犯人——小弟一名拎回大皇宮。
這才是真正的叔可忍,嫂不可忍。
Advertisement
反了天了。
皇帝陛下在軒羅殿裏來來回回踱了好幾圈,都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自己心的憤怒。而他做了這麽多年皇帝,最大的的心得之一就是:找不到話說的時候,最好是保持沉默。
於是皇帝陛下繼續踱步。
段雲重在底下跪得久了,終於忍不住抬頭小聲道:“皇兄,臣弟可以回去了麽?”
段雲嶂一個利眼掃過去,段雲重立刻乖順地低頭。
倒是跪在他邊的金輕輕說了一句:“雲重,你就先回去吧。”
皇帝陛下然大怒:“朕什麽時候允許他回去了?”
金無畏地仰頭看他:“皇上,閭王若是留宿宮裏,您就不怕太後問起原因?”
“你……”段雲嶂恨得牙直,他怕太後問起原因?要不是這小黑胖拐了段雲重擅自出宮,他怎麽會怕太後問起原因?
為什麽這死黑胖還像沒事人一樣?
段雲嶂握拳頭往案上捶了又捶,終於道:“你,先回去!”
段雲重如蒙大赦地告退,一路狂奔出宮,估計三個月是不會在宮裏出現了。
段雲嶂又在殿中踱了幾圈,而金卻好好地跪在下麵,沒有再出聲了。
終於,段雲嶂停了下來。他看向下方跪著的小黑胖,覺得自己心中勉強恢複了祥和。
“皇後,隨朕到太池邊走走吧。”
金恭敬垂首:“是,皇上。”
。
這一夜,皇帝陛下和皇後娘娘在太池邊,促膝談心。
至於他們究竟談了什麽……
啊,我們不妨先說說,太池這個東西,是個什麽東西。*思*兔*網*
太池是段雲嶂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在深宮裏挖的一個大池子,池子裏漂了三個小島,一個蓬萊,一個方丈,一個瀛洲。池子裏的水引自渭水,不錯,就是薑子牙釣周公姬旦他爹的那個水。
Advertisement
總而言之,太池是一個仙氣杳杳的地方,起碼,段雲嶂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希它是個仙氣杳杳的地方。
於是,池子裏必然要種上蓮花,池底必然要有許多的淤泥。
太池,就是這麽一個東西。
池上雖然未必仙氣杳杳,卻也的確是水氣濛濛,皇帝陛下和皇後娘娘就在瀛洲小島上,在濛濛水氣中,麵對麵蹲下來。
“皇後,你是否對朕有什麽不滿?”
“臣妾不敢。”
“那麽私自出宮,破壞婚宴,還教唆閭王同犯,這些都是怎麽回事?”段雲嶂定了金,“皇後,你要給朕一個解釋。”
“臣妾沒有解釋,單憑皇上責罰。”
“……”段雲嶂滿腔的怒氣都化作了頹然,他忽然覺得,他這個皇帝,在小黑胖眼裏興許連個屁都不是。
就這麽自然地恢複了溫良恭儉讓的姿態,仿佛之前那個在無辜百姓家中打砸搶,還罵話的小黑胖不是。
從一開始他就知道,這死黑胖的順從都是假象,可是明明被看出來是假象,還維持得這麽自然,這人真是魔鬼。
“朕知道,朕喜歡白玉,你是不開心的。”一個不留神,真心話便直直地從段雲嶂口中溜了出來。
然而也隻有真話,能夠敲中這黑胖的肋。
果然,金訝異地看了他一眼。
段雲嶂頓了一頓:“皇後,其實你心裏的苦朕都明白。”
“皇上,你是不是……誤會了什麽?”
段雲嶂深款款地握住了的肩膀:“皇後,朕想清楚了,你畢竟是朕的結發妻子,就算你又黑,又胖,又險,又膽小,朕也不應該嫌棄你。”
霾,終於在金的雙眼裏匯聚起來。
“皇上,您是想激怒臣妾麽?”
段雲嶂義正辭嚴地搖頭:“皇後,朕隻是要你看清你的境。無論是從才來看,還是從容貌來看,你和白玉,那都是天壤之別,天壤之別啊……”他一時興起,手將的下抬起,隻覺得下上圓圓的一坨,♪十分,於是,又忍不住了一下。
金渾一僵,已先於大腦做出了反應,雙手狠狠往前一推。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
皇帝陛下就這樣一跤栽進了太池裏。
啊,您已經知道了太池是個什麽東西,那麽您想必也猜得到,皇帝陛下栽下去以後,會變個什麽東西了。
阿彌陀佛。
太池水心涼,段雲嶂在池水裏翻了幾個筋鬥,終於把腦袋出了水麵。他吐了一口泥水:
“劉、黑、胖!”
劉黑胖已經芳蹤杳然。
。
金做下了這天理不容的事之後,立即鼠竄回了香羅殿。
逃離現場之前,沒有忘記回頭確認,皇帝陛下的確是一瘸一拐地踩著汙泥,裹著汙泥,上岸了。
這是一雙多麽偉大的手啊,居然活活地將皇帝陛下推下了太池。金十分崇敬地欣賞著自己十小棒槌一樣的手指。
想,最遲明天一早,或者就是今晚,太後娘娘就會左手白骨爪,右手執金釵,飄進香羅殿,捅進的心髒。屆時,的腦袋也好,手指也要,都要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