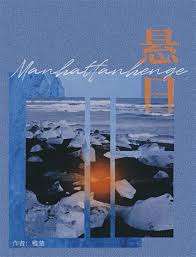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為什麼這種A也能有O》 第81章 “想干什麼?”
阿姨比他們早到,已經將家里打掃了一遍,正在做飯。
兩人搬了張躺椅放在門前,讓江阮嘉抱著貓咪坐在上邊。
白糖說:“貓狗雙全!”
“嗯。”
蔣云書倒騰回鐵門,看著比自己還高的快遞包裹,一時有些不知何從下手,“這是什麼?”
白糖正用手臂不協調地搬著小件:“唔……吊椅?還是秋千?也有可能是黑糖的玩。”
蔣云書來來回回搬了七八趟,并且由衷謝自己是個alpha,他單手提起一袋米一樣的東西拿到眼前看,一字一頓地讀道:“威納克水泥。”
白糖站在遠小心翼翼地拿著刀拆開小包裹,聞言轉頭朝alpha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睛瞇起來,抿著笑。
蔣云書用刀劃開四邊的膠帶,再牟足力氣一扯,滋拉一聲,箱子就開了,然后他從大大小小的包裹里拿出來鐵架、秋千、吊椅、大鋤頭、一大袋鵝暖石還有黑糖的大型蹺蹺板玩。
白糖小小一只蹲在alpha旁邊,時不時湊過臉去要親。
蔣云書就側過頭來親一下再繼續弄。
偶爾黑糖會哼哧哼哧地跑過來要加他們。
在得到alpha的第8次親親后,白糖心滿意足地站起來,眼前卻霎時有些黑,暈乎乎地站不住就要往前倒。
蔣云書心都快跳出來了,戴著臟兮兮的棉線手套,連忙張開手臂扶住他。
蹲久了突然站起出現頭暈眼黑是人的一種正常反應,但白糖本來就差再加上流了那麼多,足足趴在alpha上趴了快五分鐘,眼前的世界才逐漸清晰。
白糖悶悶不樂道:“啊蹲太久了”
蔣云書皺著眉,心疼道:“幾秒是正常的,你是太了。”好不容易養好了點,現在又他只怕白糖落下了病,年紀稍微大點就多病痛。
Advertisement
白糖直起來,自知理虧,他親了口alpha的側臉,不愿道:“我會好好喝中藥的”
蔣云書說:“我們再去看看老醫生,給你把把脈再重新撿藥。”
白糖胡地點著頭,用左手拿起放在小型除草機,右手手臂抵著機,說:“那我去除草啦?”
“別,你的手現在沒法拿穩,”蔣云書制止他,除草機底下是鋒利的合金鋸片,快速轉起來足以把人的手直接割斷,“我來弄。”
白糖的左手手腕還沒痊愈,傷口很深,無法用力,右手整個手掌被包住,手指無法彎曲,蔣云書實在放心不下。
蔣云書把黑糖拴在門上,又去把水閘擰開,將水管遞給白糖,商量道:“你澆水,好不好。”
下,alpha戴著一頂鴨舌帽,因干活掉了累贅的大,只穿著單薄的衛,衛底下的手臂發有力。
白糖曾過的,一下就能把他抱起來。
他聽話地拿住水管,只見alpha蹲下子,一點一點地幫他把腳挽到腳踝。
“謝謝蔣醫生!”白糖仰起頭朝蔣云書笑。
蔣云書心很好,他第一次親手做這些事,而很幸運的,第一次做就有喜歡的人陪著,白糖看起來也很開心,角的笑意從進門到現在都沒消失過。
蔣云書忽然發現,omega的瞳孔其實更偏向于淺棕,在下非常明顯。他垂眼看了幾秒白糖的笑,接著猝不及防地扯掉了右手的手套,上白糖的側臉,微微彎下腰,歪頭親了下來。
為了防止帽沿到白糖,他的頭側得很偏,下頜線分明。
白糖被嚇了一跳,他不停地推拒,空喊道:“唔!阿姨!阿姨嗯還在這!”
Advertisement
蔣云書看了眼在旁邊坐著的江阮嘉,低著頭沒把眼神分過來,只有皺的手著貓咪。
于是alpha明正大地把omega推到門上親了。
十分鐘過去,漲紅了臉的白糖憤懣地指控:“你變了!蔣醫生你變了!”
“沒變,”蔣云書輕輕笑了下,“我只是把我想做的付諸實踐了。”
放肆一點。很爽。秦終南說得沒錯。
青草和潤的泥土味漸漸在空氣中彌漫開來,除草機的聲音很大,嗡嗡著,白糖跟在alpha后,將水澆在被修剪好的草地上。
忽然家政阿姨打開了門,手里拿著部手機,大聲喊道:“誰的電話響了?”
白糖看過去,“是我的!”
他將水管拋到還沒澆到的地方,然后兩三步跑過去。
是一個陌生的電話:“喂你好?”
“白糖,是我。”
白糖微微瞪大了眼,是時穆清!棲的校長!
“我看到你把簡歷發到我們郵箱了。”
“是、是的”白糖磕磕起來,他之前也說過,將來想當一名老師,去棲任教。
時穆清說:“你能考上帝都,真的很厲害,而且只復習了一年。在簡歷上,我有看到你的專業績都名列前茅,基本的證書你也拿到手了,我相信剩下的那些你也能通過。所以我想問,要不要先來棲當助手?悉一下。”
白糖久久說不出話來,直到蔣云書走過來問怎麼了。
“我、我可以!謝謝時校長!”白糖的喜悅掛上了臉,手抓著alpha的手臂,激得甚至跳了幾下,“但是我最近可能不太方便可以半個月之后再去嗎?”
“可以,到時候聯系吧。”時穆清說。
電話掛了。
Advertisement
“哇啊啊啊!”白糖著攀上蔣云書的脖子,后者輕而易舉地托起omega的屁抱了起來,一串作下來行云流水,默契又自然,仿佛做了上千萬遍。
白糖雙圈著alpha的腰,雙手捧著alpha的臉。他看到蔣云書的鼻尖上蹭到了灰,手揩掉,他眼睛里全是笑意和,迎著,漂亮又生,“時校長!你還記得嗎!我上周不是將簡歷發到棲的郵箱上了嗎!時校長聯系我說我可以先去當助理!”
蔣云書聞言也打心底地替自己的omega到開心,“好消息。”
白糖激地連親了alpha側臉好幾下,ua ua的,很響亮。
連帶著江阮嘉都有了些反應,遲鈍地抬起頭,看到了兩人著的剪影。
草地還沒完全修剪完,阿姨就吆喝著說吃晚飯了。
白糖注意到,從吃完晚飯開始,蔣云書就有些焦慮了。
他拿了張a4紙過來,畫了下花園的平鋪圖,基本上是一個長方形的形狀。
“蔣醫生,這里,”白糖在長方形的下面寫下了鐵門兩個字,又圈起右下角一大塊,“這里我們要不要弄一個池子,養一些金魚?”
蔣云書說:“可以,但你不是討厭腥味?這不是活水,許久不換水的話會很臭。”
白糖遲疑地咬了下筆帽,他想著到時候蔣醫生可能會很忙,自己也會很忙,要不算
“我們可以加錢讓阿姨換,”蔣云書湊到omega耳旁說,“想養就養,沒關系的。”
白糖便畫了個四分之一圓,說:“那我們就在這弄一個池子!里面養胖嘟嘟的金魚,尾很大肚子很大那種!”
蔣云書答應下來,“好。”
鐵門在花園的正中間,有一條小路供大家從鐵門走到房門,白糖畫了條彎曲的線連接池子和小路,“這里,我們就弄一條鵝卵石小路好不好?我買了一袋的鵝卵石!”
Advertisement
蔣云書:“可以。”
白糖下筆畫著,“這里,還有這里,這邊放秋千,旁邊種一棵小樹苗,我也買了!這邊放”
蔣云書跟著想象了下,然后發現,白糖的審好像很不錯。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著,據不同的意見來回調整,最終拍案。
期間白糖去洗澡,他出來看到alpha正坐在書桌前,用信紙寫著給父母的那封信。
白糖沒有打擾他,輕手輕腳地下了樓,很自覺地把中藥一口氣喝完了,皺著臉吃了三顆alpha買回來的水果糖。
一個小時過去,白糖坐在客廳上看著一本課外書。可短短半小時之,他看蔣云書上下走了三趟,分別拿上去了些不重要的小東西。
“寫完了嗎蔣醫生?”白糖問。
蔣云書穿著珊瑚絨家居服,站在樓梯間,“嗯,組織的部分工作也做完了。”
于是兩人約定好看一部電影,但白糖注意到,alpha總無意識地蹙著眉,指尖反復點著大,有些煩躁焦慮的模樣。
白糖摁下了暫停。
蔣云書這才驚醒,意識到在看電影時不專心是一件讓人很不舒服的事,他握住白糖的手,問:“抱歉,是不是我影響到你了?”
“不是,沒關系,”白糖搖搖頭,本來就是為了轉移蔣云書注意力看的電影,他說,“蔣醫生,你現在在想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蔣云書沉默片刻,坦白:“有點煩,我今天什麼工作都沒做就寫了一封信,覺得自己很,沒用。”
他說完也沒看白糖,把自己的缺點和病暴在喜歡的人面前,讓他更焦慮了,連帶著有些忐忑。
白糖卻說:“但是我覺得你今天做了很多事啊!”
蔣云書頓了下,看過去。
“你看,”白糖一件一件地給他數著,“早上去見了心理咨詢師,下午我們去接了阿姨和貓貓,接著回來休息了下,我們就開始除草了呀,你忘了嗎?現在花園外邊干凈了很多很多!看起來就跟新的一樣!然后晚上我們商量了很久要怎麼改造我們的花園,你不僅寫了一封信,還做完了今天的組織工作,現在又一起看了快一半的電影。而且!我很開心。”
組織現在也不發任務給他了,只有一些用腳趾頭都能做的驀地,聽到最后一句的蔣云書神有些怔愣,間發出一聲:“嗯?”
“你一直在陪著我,所以我覺得很開心。”白糖陷在沙發里,在周圍暗淡的燈下,的米白領子襯得他越發乖順,“雖然之前我也很開心,但是今天特別特別開心。”
蔣云書看著他,焦躁的心莫名地被安了。
他今天讓白糖很開心。
白糖開心比什麼事都要重要,他忙死忙活,不就是為了讓白糖過得開心嗎?
蔣云書的結了下,“好。”
可這只是暫時的,臨睡前,他的心又變得躁了。
白糖一遍又一遍安著自己的alpha,但效果甚微。
蔣云書吃了顆安眠藥,他現在有些睡眠障礙,是醫院給開的。
距離關燈已經過了半小時,白糖躺在alpha的懷抱里有些困,他的還沒恢復好,今天做的事已經讓他很疲憊了。
他甩了甩腦袋,問:“蔣醫生睡不著嗎?”
在黑暗中,蔣云書的眼睛很亮,里面毫無睡意,他“嗯”了一聲,“你快睡吧,待會安眠藥就發揮藥效了。”
白糖坐起來,擰開燈,他說:“要不,我哄你睡覺吧?”
蔣云書看著他:“怎麼哄?”
白糖穿上套和拖鞋跑了出去,沒一會拿著一本書進來了,他立起枕頭靠著床頭,說:“來,我給你念念思想政治的概念。”
蔣云書又好笑又無奈,他笑了下,“別,你快睡吧,你這還熬夜。”
“不行,”白糖斬釘截鐵地拒絕,他坐在躺在的alpha旁邊,手掖了掖alpha上的被子,說,“我開始念了。”
蔣云書著被人放在心尖上關心的覺,心里仿佛被打翻了罐子,他表面上無奈,可角都是上揚著的:“就半小時,我還沒睡著你就先睡。”
白糖不理他,自顧自念道:“哲學基本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思維和存在誰是第一的問題,這是劃分唯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派別的依據”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ABO]離婚后他拒絕當渣攻
強大狠厲Alpha攻&斯文謙和Omega受(強強聯合)破鏡重圓小甜品,吃糖了! ****** 一:秦聞跟遲寒的三年婚約到期,他看著對方毫不猶豫遞出離婚協議。 整整三年,竟是一點兒眷戀都沒有。 遲寒冷漠地看著秦聞:“緣分到此,日後珍重。” 秦聞說不出話,他想折盡尊嚴地問一句:“可不可以不離婚?” 但是遲寒轉身太快。 每當秦聞想起這段灰暗絕望的時光,就忍不住給身邊的人一腳,然後得得瑟瑟地問:“你當年不是很狂嗎?” 遲寒將人抱住,溫聲:“輕點兒。” 二:離婚後沒多久秦聞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就那一次失控。 秦聞輕嘆:“寶寶,以後就咱們父子兩個相依為命了。” 可遲寒卻不答應了。有人刁難秦聞,遲寒想盡辦法也要扯下對方一層皮;有人愛慕秦聞,遲寒差點兒將人扔進醫院。 同性戀合法,雷生子勿入,雙潔!
57.7萬字8.18 2316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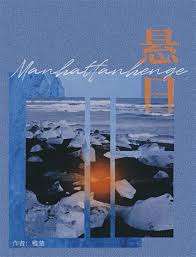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