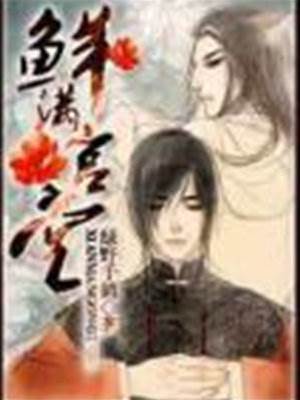《為什麼這種A也能有O》 第37章 “真的要來了。”
“如云…… 如云你答應我。” 白糖滿面紅地在廁所隔間里,死死抓住門把手。
鄭如云在門外一臉狂躁,他 “嘖” 了一聲,“你先告訴我你用了多支抑制劑!”
“唔……” 白糖的腦袋無力地枕著自己的膝蓋,囁嚅道,“四、四支。”
“三天用四支,” 鄭如云氣得破口大罵,“你他媽想死是不是?!”
昨晚的白糖并沒有正式步發期,早上他起床的時候,alpha 還睡得昏沉。但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當他的發期真的來了,躲在洗手間難地打抑制劑時,被鄭如云撞見了。
“我抑制不住……” 白糖意識模糊,他盯著垃圾桶那針抑制劑,視線卻沒對焦,“它是壞的……”
鄭如云什麼都聽不清楚,他用力地拍了拍門,“白糖,你先開門!”
聲響喚回了白糖些許神智,他覺自己仿佛在烈火之中,什麼都思考不了,只有眼前不停閃過鮮艷的紅,他虛弱道:“嗚你答應我……!不要喊,不喊蔣云蘇來…… 會很痛。”
“我不,我答應你,咱不喊他來,” 甜味越來越濃,鄭如云快速地給自己也來了一針,防止被影響導致兩人雙雙發,“你先開門,我看看你況!”
白糖的手臂發,已經有些抬不起來了,指尖一點一點地索著門上的鎖,汗珠一顆顆地往下掉,總算是撥拉開了。
距離上課鈴響早已過去十多分鐘,方老師尋著味道,找到了洗手間,“怎麼回事?”
鄭如云暴躁道:“媽的,白糖發期來了。”
“我讓王老師送他去醫院,” 王老師是個 beta,方老師當機立斷道,“不然發期會影響學校里的 omega。”
Advertisement
白糖現在沒有安全極了,幾乎是小小一只地嵌在角落里,服下擺掀了起來,領口大開,他半瞇著眼睛著熱氣,不停地用地去冰涼的墻壁,“熱、熱…… 難嗚……”
“抑制劑為什麼發揮不了作用!” 鄭如云都要心疼死了,他捉住白糖滾燙的手臂,“沒事,咱們去醫院,很快就到了。”
眼前一片熱氣蒸騰的模糊,他恍惚中看清了鄭如云的臉,斷斷續續地、帶著哭腔哀求:“綁起來,嗚…… 快、快把我綁起來……”
王老師用隔離袋把白糖整個罩住抬到車子里,“如云,上車。”
“郭醫生!” 一個護士跑到空無一人的腺科,“有位omega發了,您去看看腺況!”
林醫生無所事事地坐在隔壁,聞言站起來,“我也去瞧瞧。”
“林醫生您別鬧了!” 護士說,“你是 alpha!”
“啊啊……”林白晝了個懶腰,發出 “喀啦喀啦” 的聲響,“我又不進去,一天到晚坐在這要發霉了,走走不行啊。”
醫院人來人往,5 樓腺科和別的樓層簡直是兩個世界,鄭如云焦急地站在隔離室外,郭醫生檢查完走出來下口罩,對王老師說,“他這種況沒法再打強效抑制劑了,最好最安全的解決方法是讓他的alpha來標記他。”
“不行的,” 鄭如云咬著牙說,“那個畜生會這麼好心?白糖也說了千萬不能讓他來!”
林白晝頓住了腳步:“白糖?”
郭醫生拿著結果報告,說道:“里的確有過量的抑制劑,這樣吧,先隔離觀察 15 分鐘,你們現在趕讓他的alpha來等著。”
Advertisement
一般的omega在發前期,只需兩支抑制劑就能把狂躁的信息素制下來,可白糖的腺原本就發育不正常,信息素失調紊和環境不穩定導致發期遲遲未來,而這次發期程度就等于積累了四個月的信息素一下子發轟炸過來。
林白晝湊過來,確認了白糖的名字。
“林醫生,你?” 郭醫生疑。
林白晝眉頭皺起,“我不建議再繼續等下去了,哪怕最后抑制劑功制住了發期,他的腺發育也只會愈發不正常。”
郭醫生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但那個omega的腺上全是傷,如果喊他的alpha來,況可能只會更不妙。”
15 分鐘后,郭醫生面凝重,語氣嚴肅:“他的alpha呢?!你們誰是他的家屬或者朋友,趕聯系他的 alpha!這不是開玩笑的!”
鄭如云握了拳頭,臉發白,“是真的一定要喊alpha嗎?”
“你是聽不懂人話嗎?” 跟著一直等待的林白晝忽然開口,盯鄭如云,“如果沒有 alpha,再過十幾分鐘,患者就要休克了,嚴重一點會死,這下聽懂了嗎?”
沒有 alpha。
這幾個字狠狠地中了鄭如云,他瞳孔驟,憤怒得連臉都扭曲了,“你他媽…… 你是個alpha吧?你懂什麼?!omega 在發期幾乎沒有神智!這時候alpha想怎麼傷害他都可以!那個畜生會弄死白糖的!白糖會死在里面!”
林白晝也著角,面無表地往前一步,幾乎懟到了鄭如云的面前,迫極強,“我管你那麼多彎彎繞繞的,我們醫生要做的就是讓他活著,底線就是患者的生命,他的alpha現在不來,就只有死路一條!”
Advertisement
鄭如云氣上了頭,他同樣向前一步,不甘示弱地瞪著,眼睛里燒出了火,兩人的臉幾乎要上了,“你……”
“如云,” 王老師的手用力地搭上鄭如云的肩膀,“冷靜點,醫生說得是對的,我現在打電話讓教務找白糖alpha的聯系方式。”
林白晝退后一步,冷笑一聲,“等你們這垃圾效率,患者都要死了。”
“…… 你說什麼?” 鄭如云一把揪上了他的領子。
蔣云書的眼皮掙扎似地抖了抖,好一會才掀開一條,亮刺進來,腦袋昏沉地想不起任何事,他重新閉上眼睛,躺了 15 分鐘后,意識才逐漸歸位。
他撐起,發現自己昨晚是怎麼倒下的,現在就怎麼起來,看了眼掛在墻上的鐘表,11:47,足足睡了 13 個小時。
白糖那小崽子……
昨晚蔣云書毫無防備地喝完了那幾口藥水后,兩人又進行了一番方的流,見白糖矢口否認,他也無可奈何,只能放人去洗澡。
可漸漸的,困意涌上來,書本上的字有了重影,到這時,他還以為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畢竟今天很疲憊,公司出了點問題讓他去理,反復來回奔波。
又撐了十幾分鐘,直到他發現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睡意時,已經為時已晚,他兩眼一閉,一頭栽倒在沙發上。
蔣云書掀開被子坐起來,沉默兩秒,被氣笑了,他是要謝白糖還給自己蓋了張被子還是怎麼地。
至于白糖為什麼昨晚要給他下藥,為什麼冒著險也要讓他睡過去,蔣云書猜測一定是出現了什麼特殊狀況,再結合回來的路上一直若若現的甜味。
他幾乎是肯定,白糖發期來了。
可家里并沒有信息素的味道,找遍了也沒發現白糖的影,蔣云書的表逐漸沉了下來,剛找到學校的電話號碼時,林白晝的電話來了。
他擰著眉快速點開,只聽到對面的背景音一陣嘈雜,林白晝的聲音飽含火氣:“喂?!蔣云書!帝都醫院 6 層,白糖發期快休克了,現在!立刻!馬上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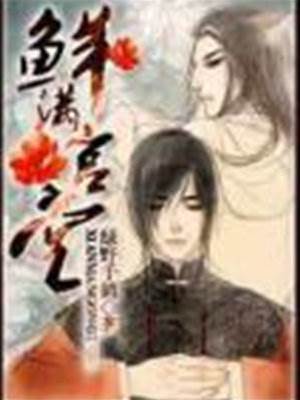
鮮滿宮堂
海鮮大廚莫名其妙穿到了古代, 說是出身貴族家大業大,家里最值錢的也就一頭灰毛驢…… 蘇譽無奈望天,為了養家糊口,只能重操舊業出去賣魚, 可皇家選妃不分男女,作為一個貴族破落戶還必須得參加…… 論題:論表演殺魚技能會不會被選中進宮 皇帝陛下甩甩尾巴:“喵嗚!”
35.5萬字8 7357 -
完結224 章

離婚后渣攻痛哭流涕
“挖!把他的骨灰挖出來!”蘇平愛顧銘,是他這輩子的劫數,十年掏心掏肺,換來的卻是凄慘無比的下場。“顧銘哥,放了我……”“你害舒安出了車禍,我這輩子都不會放過你。”當真相浮出水面,渣攻痛不欲生……人物表:顧銘蘇平肖杞葉洋沈宴男葉舒安葉嘉文齊佑齊佐季正霖駱楓…… 【本文純屬虛構,架空背景】 分類:虐文 HE BE 現代 架空 生子
50.1萬字8 82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