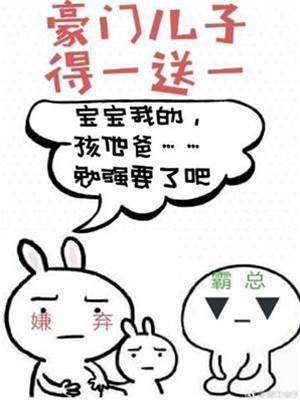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等風熱吻你》 第40章 四十吻
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 烏云挪了一個角, 出點點月。和枯葉被冷風吹著墜落, 搖搖晃晃、無聲無息飄到地面。付雪梨一點都不困, 踮起腳, 依偎著許星純。像只小貓咪,又討好地蹭了蹭他。
“許星純,你口好燙啊, 是出什麼病了嗎?”付雪梨抬頭, 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默了半晌,他斜靠著, 了的頭發,然后說:“心跳不齊整, 臟有偏離。”
“.......”
不愧是學過醫的人, 心跳加速都能說的這麼有文化。
“我今天晚上要跟你睡,你還沒答應我。”退開一點,又重復了一遍。
“好。”
小雪在溫地飄搖,似斷非斷。得到回答后, 付雪梨又湊近許星純,親了親他的下, 不等他有什麼反應, 就立馬跳開,大膽調戲道,“你知不知道自己長得很好看。”
“.......”他始終注視著。
“你別過來,小心我又親你。”似真似假威脅。
許星純過來, 牽住手腕,耐心道,“外面很冷,先進去。”
“你不信我會強吻你?”
“信。”
“嘁。”付雪梨撇,歪著腦袋,“你總是這麼無趣,我不想親了。”
回他房間的路上,突然想到什麼,從口袋出一樣東西,“我有兩顆糖,剛剛吃飯的時候,旁邊家小弟弟跑過來給我的。”
付雪梨攤開手掌,臉低垂,“分你一顆。”
一紅一綠,西瓜和荔枝的味道。
問,“你喜歡吃哪個啊?”
“荔枝。”
這個回答,讓付雪梨若有所思了一會,轉頭看了許星純一眼。
還記得初中有一次,許星純上課突然風,問了付雪梨要不要和他在一起。
Advertisement
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談。
那時先是震驚,心覺像掐了一下。更多的還是莫名其妙,停滯了幾秒,接著就無地拒絕了他。
因為那時候付雪梨是個叛逆,對來說,這個從頭發到腳板心都寫著嚴肅的班長,就算帥,也不能當男朋友。
拒絕許星純后,他對倒是明顯冷淡了下來。視線從來不主和匯,上課下課就悶頭寫作業,但是付雪梨看著他答不理的樣子,征服莫名有些膨脹了起來。
之后幾天,下課時間在班后面和一群男生打牌,他在教室后面掃地。付雪梨耍牌休息的間歇,就看到許星純冷冷地瞪著。
不甘示弱,回了他一個呲牙咧的表。
這種僵的相狀態大概持續了一個星期。某天,付雪梨上課轉頭和別的人講話,許星純抄完板書從講臺上下來。停下腳步,眉頭皺起來,用沾了筆灰的手去提了提快垮到肩膀的T恤領口,遮住出來的肩帶。
呆了一下。
大庭廣眾之下,作完全是下意識地,并且和付雪梨說話的人,看到這一幕后,已經張了小o形。
等許星純從位置上拿了一瓶礦泉水,去外面洗手。后桌拿胳膊撞,恍然大悟道:“嘖嘖嘖,看不出來啊!原來你和班長關系這麼曖昧?”
付雪梨其實也被他剛剛的作弄得有點尷尬。翻了一個白眼,不吭一聲就轉過,一把出屜里的枕頭開始裝睡。
兩人一上午都沒講話。
等到下午第一節課下了,理老師站在門口吆喝,要課代表下節課下了收作業。
許星純坐在座位上寫作業。
把旁邊的窗戶拉上,一不趴了好一會,付雪梨轉過臉問,“喂,圣誕節,你想要什麼。”
Advertisement
他說,“什麼都不要。”
放了一顆荔枝味的糖在他的課桌上,厚臉皮地說,“班長,其實我想要你的理作業。”
“....”半晌,他還是被一顆水果糖收買。出自己的作業本,遞給,“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問我。”
說完這句話,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低頭寫自己的作業。
他皮白膩,從鼻尖到下頜,還未張開的五已經初現致。
付雪梨雙手叉,疊在腦后,不知道怎麼腦子一,鬼迷心竅了調戲道,“吻你啊?”
音調明顯發生了變化。
許星純似乎微微意外,筆尖一頓。慢慢的,耳尖變得有點紅,繃,仍舊不看,面上還是很平靜,“嗯...”
“那我吻啦?”持續腦中,眼睜睜看著他的側臉出神,還有一個可的小酒窩。
“好。”許星純頓了又頓,手里的筆已經被放下。他看著眼睛都直了的付雪梨,說,“可以。”
放隨心慣了的付雪梨四了,逮著機會,湊上去對著許星純的一咬。
的,像果凍。
甜滋滋的。
嘿嘿笑著,付雪梨砸吧砸吧,有點回味。
于是,后半節課,許星純丟下桌上一攤作業本,人就消失了。
學校二樓的男廁所。
水池子里嘩嘩放水,許星純低頭,兩手撐著洗手臺。
他臉紅潤,被得微微著氣,呼吸凌急促。水珠順著額角眉梢滴滴答答往下掉。
怔愣了好一會。
看著冰冷黑灰的墻壁。慢慢地,許星純略微回神。抬起右手,也是的。用手背,帶著一點小心翼翼,輕輕蹭了蹭自己的。
想到這些往事,忽然有些懷念了。
付雪梨收起西瓜味的,剝開荔枝味糖果的糖紙,著放進自己里,然后一把拉過許星純的脖子,住他的下,閉上眼睛,對了上去。
Advertisement
的小舌頭出半截,劃過。有刻意引的意味。
他的像炙熱的冬雪,又像櫻桃的紅,帶著潤冰涼的空氣,齒之間且甜。
有點糟糕。
喜歡好像是互相傳染的。
早以為自己已經變了一個老于世故的大人,見一個煩一個,平平淡淡對待也已經掀不起什麼波瀾。但付雪梨越來越,覺自己...沉迷許星純了。
“你起反應了誒,許星純。”
“嗯。”
“怎麼辦?”腦子昏昏,湊到他耳邊,“要不要進房間,我幫你解決?”
“不用了。”許星純嗓音已經沙啞,換了個姿勢,扣著的后腦勺往自己頸窩里。把人抱實了,不風。
他的呼吸熱熱的,兩人是一偏頭就能親到的距離。
“你看你,又在假正經了?。”付雪梨哼哼唧唧,“你知道以前宋一帆跟我說你什麼嗎?”
他評價許星純,有一段很搞笑,一直都記著,
“許班長吧,就這麼跟你說。從男人對男人深靈魂的了解,班長這人比你想象得還要有,表面正兒八經吧,其實特!”
最后還是沒能幫他解決,許星純獨自去浴室洗澡。留付雪梨一個人在房間里,捂著自己的小肚子,在床上翻滾。
著床頭的燈罩發了會呆,暈暈地著一些。付雪梨剛剛覺自己頭有些干熱,就看到許星純從窗戶邊走過。
他單手端著一杯水,反手關上門。
“我剛剛突然有點害怕。”
等許星純走近了,付雪梨跪起來,手上他的腰。
他彎腰摟過,在耳邊,夜深人靜之時,聲音有種低低的溫,“喝點溫水。”
關了燈,房間里陷一片黑暗沉寂。
Advertisement
付雪梨的手,從被窩里慢慢索到他的頸窩,再到下,“其實我這幾年過得也不好。拍戲老是日夜顛倒,有時候在酒店做夢夢到你,醒來就很失落,發呆的時候還會很愧疚。”
這個話,說的略有些違心。
雖然很沒良心,其實這幾年,付雪梨已經不怎麼敢想許星純。因為只要一想到他,一想到和他有關的事,就被濃重的愧疚包圍,還夾雜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悔意。心里擰著過不去。
太難了。
付雪梨寧愿自己好了傷疤就忘了疼。
從來不是圣人,明知道自己作惡多端,偶爾也會自我鄙夷。
控制不住心里偶爾冒出來的念想。
—許星純這幾年沒了,過得非常孤獨無趣,每到深夜的時候都能忘記的壞,想起的好。
如今重逢,還能用溫填滿他的裂痕。
訥訥說完這話以后,付雪梨想親他,又夠不著,于是略氣惱,還有一些心虛,“許星純你好冷漠,什麼也不對我說,憋在心里會憋出病來的,還是說你完全都不心疼我的。”
“心疼你什麼。”
“什麼?!”付雪梨把他推開,質問道:“你為什麼這麼絕。”
可惜脾氣還沒發完,就被人掰著轉過臉,許星純強迫質地又落下一吻。一個接一個。
比舌纏更要命。
心臟一陣一陣發,被他單手按著,半強迫的味道。付雪梨又掙不開桎梏,唔唔著,雙蹬。
拇指弄的,許星純屈肘,俯首在付雪梨的眼皮上親了親。房間安靜,他聽著自暴自棄,斷斷續續囈語。
“其實...我覺得我很自私。我怕你這幾年過得不好,又怕你過得太好,我雖然知道自己對不起你,但是也不希你沒有我,自己過得很幸福。”
過得幸福?
許星純有些自嘲。
離開付雪梨以后,他別無選擇,只能想盡辦法掩飾一塌糊涂的自己。
剛開始幾年,日子過得很爛,時間過得太慢。
知道了明星,他不敢看電視,不敢看娛樂新聞。
不敢接任何和有關的東西。
無數個深夜都在想。
把手槍藏進外套。
然后乘著火車去找。
因為許星純也不了這樣的自己了。
那樣完完全全著的他。
到近乎迷。
每時每刻,都要瘋他。
作者有話要說:
手槍藏進風,是網易云里看到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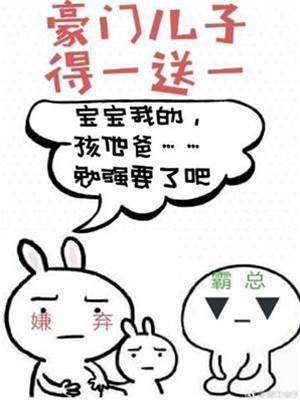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72 章

心機女的春天
韓熙靠著一張得天獨厚的漂亮臉蛋,追求者從沒斷過。 她一邊對周圍的示好反應平淡,一邊在寡淡垂眸間細心挑選下一個相處對象。 精挑細選,選中了紀延聲。 —— 韓熙將懷孕報告單遞到駕駛座,意料之中見到紀延聲臉色驟變。她聽見他用浸滿冰渣的聲音問她:“你設計我?” 她答非所問:“你是孩子父親。” 紀延聲盯著她的側臉,半晌,嗤笑一聲。 “……你別后悔。” 靠著一紙懷孕報告單,韓熙如愿以償嫁給了紀延聲。 男人道一句:紀公子艷福不淺。 女人道一句:心機女臭不要臉。 可進了婚姻這座墳墓,里面究竟是酸是甜,外人又如何知曉呢?不過是冷暖自知罷了。 食用指南: 1.先婚后愛,本質甜文。 2.潔黨勿入! 3.女主有心機,但不是金手指大開的心機。
22.8萬字8 6822 -
完結857 章

重生九零肥妻歸來
中醫傳承者江楠,被人設計陷害入獄,臨死前她才得知,自己在襁褓里就被人貍貓換太子。重生新婚夜,她選擇留在毀容丈夫身邊,憑借絕妙醫術,還他一張英俊臉,夫妻攜手弘揚中醫,順便虐渣撕蓮花,奪回屬于自己的人生。
159.8萬字8 97590 -
完結523 章

重生蜜戀:偏執九爺他淪陷了
前世,云漫夏豬油蒙心,錯信渣男賤女,害得寵她愛她之人,車禍慘死!一世重來,她擦亮雙眼,重啟智商,嫁進白家,乖乖成了九爺第四任嬌妻!上輩子憋屈,這輩子逆襲!有人罵她廢物,醫學泰斗為她瑞殺送水,唯命是從,有人嘲她不如繼姐:頂級大佬哭著跪著求她叫哥!更有隱世豪門少夫人頭街為她撐腰!“你只管在外面放建,老公為你保駕護航!”
88.6萬字8.18 140070 -
完結167 章

聖佛子人設崩了,原是寵妻狂魔
【強製愛 男主偏執 雙潔】南姿去求靳嶼川那天,下著滂沱大雨。她渾身濕透如喪家犬,他居高臨下吩咐,“去洗幹淨,在床上等我。”兩人一睡便是兩年,直至南姿畢業,“靳先生,契約已到期。”然後,她瀟灑地轉身回國。再重逢,靳嶼川成為她未婚夫的小舅。有著清冷聖佛子美譽的靳嶼川,急得跌落神壇變成偏執的惡魔。他逼迫南姿分手,不擇手段娶她為妻。人人都說南姿配不上靳嶼川。隻有靳嶼川知道,他對南姿一眼入魔,為捕獲她設計一個又一個圈套......
29.1萬字8.18 45878 -
完結150 章

垂涎你許久
【破鏡重圓+強取豪奪+雙潔1v1】向枳初見宋煜北那天,是在迎新晚會上。從那以後她的眼睛就再沒從宋煜北臉上挪開過。可宋煜北性子桀驁,從不拿正眼瞧她。某次好友打趣他:“最近藝術係係花在追你?”宋煜北淡漠掀眸:“那是誰?不認識。”後來,一個大雨磅礴的夜晚。宋煜北不顧渾身濕透,掐著向枳的手腕不肯放她走,“能不能不分手?”向枳撥弄著自己的長發,“我玩夠了,不想在你身上浪費時間了。”……四年後相遇。宋煜北已是西京神秘低調的商業巨擘。他在她最窮困潦倒時出現,上位者蔑視又輕佻的俯視她,“賣什麽價?”向枳躲他。他卻步步緊逼。無人的夜裏,宋煜北將她堵在床角:“說你後悔分手!”“說你分手後的每個日夜都在想我!”“說你還愛我……”四年後的宋煜北瘋批難纏,她嚇到想要跑路。逃跑時卻被宋煜北抓回。去民政局的路上,她被他紅著眼禁錮在懷裏:“再跑,打斷你的腿!”
25.4萬字8 8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