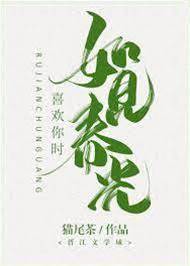《女校》 第一百二十八章 油爆
下午的拍攝,靳譯肯沒有去,他見識過四個人五百張的厲害了,愿待在民宿睡覺養。
吳爾跟著隊伍上了山,但沒跟拍攝,去山林踩點探險去了,而鄔嘉葵和方璇一人一把休憩椅,支著傘,戴著墨鏡,疊著,拍攝開始的時候,倆就這麼一聲不吭地在旁,像坐鎮觀音似的,讓龍七想起當年這對姐妹花撕高寧寧時的陣仗,鄔嘉葵看戲,看戲時候特安靜,自帶一科班生的氣場,可能是被這氣場影響,伍依姍們不再像上午時一邊拍攝一邊科打諢,就好像被監考,突然認真起來了,那林更緘口不言,低調得不行,因為方璇倆眼睛幾乎時時刻刻盯著。
負責導演工作的男生也特有意思,每拍完一條,都會征求意見似的看一看鄔嘉葵,鄔嘉葵這“指導老師”當得一點不害臊,每到龍七的戲份就說“過”,每到那林的戲份就笑一笑。
帶著一聲兒非常輕的“呵”音。
休息時間側著頭,墨鏡遮著眼,輕悠悠地講:“我以為你已經演得夠爛了,真沒想到山外有山。”
龍七正好打上一煙,方璇給遞的火,說那可說不準,人那林演得最好的是自個兒,影后級。
然后往鄔嘉葵的休憩椅踢一腳,弄得鄔嘉葵發尾邊的大耳環一晃:“我給你三秒,你重新組織組織前半句話。”
“你好歹也接一下真實的自己。”
“那怎麼全國觀眾對我在《冷蟬》里的評價比你高。”
“怎麼可能。”
“多久沒上網了?”
《冷蟬》上映已經三天,之前那事鬧騰的,龍七連首映禮都沒出席,但是老坪有替關注觀眾影評,勝就勝在角張力夠足,人設出彩,那麼狠的一個角罩住了,張弛有度,滿目靈氣,從前期觀影反應來看,可以說給出了足夠驚喜的一張績單,而鄔嘉葵演技好歸好,敗在角戲份普通,雖然一場雨中哭戲非常彩,但后續的討論重點依舊放在了龍七的表現上。
Advertisement
鄔嘉葵沒有回話。
照著骨子里那副傲勁兒,是本不信,慢悠悠地朝方璇挪一眼,但方璇不替的好閨出聲兒,眼神還稍微有點躲閃,鄔嘉葵這就懂了,起一步,霎時跟龍七挨得近,煙頭都差點著手臂,龍七撣著煙,被鄔嘉葵目不斜視地盯著。
盯了三秒。
“鎮上有沒有電影院?”
“有!”一直在指教的導演男生,聽鄔嘉葵一問,忙不迭地舉手搶答,“山腳有一家,但比較舊。”
“好,今晚看《冷蟬》,我請客。”
……
“全部人。”末了,鄔嘉葵補。
那邊在換服裝的伍依姍,改劇本的生,補妝的葛因濘和那林,扛著道的男生,還有低頭挑著攝影設備的傅宇敖,聽到這話,都陸陸續續地抬頭,朝火藥味濃重的這一方,看過來。
記得原本是要撕那林來著的。
……
下午的拍攝收后,鄔嘉葵興許上網查過影評了,整張臉就沒放過晴,一回民宿就噔噔噔地上樓回房,龍七覺著可算到鄔嘉葵的死了,打這麼久道,從來就是腦袋機靈溜的笑面小虎,斗輸了沒發過飆,輸了沒發過飆,說演技不如人,發飆了。
還偏偏執著地要去影院“挨打”。
而這件事靳譯肯也很快知道了。
他是傍晚五點醒的,訂的票是晚上七點,睡過一覺后咳嗽算好了點,洗過澡,換了服,龍七在臺的沙發椅上啃蘋果,和方璇發消息,方璇和鄔嘉葵住的房恰好就是之前騰出去的那間,正在考慮要不要告訴們有關老鼠的事。
靳譯肯拿了壺茶出來,從起床到洗澡他就沒講過話,像沒從那一覺中出神似的,問怎麼,他說做了個夢。
Advertisement
“什麼夢?”
他沒講,了臉,垂著腦袋看了手機半晌。
“你倒是說。”
“你跟了司柏林,完事兒被我撬了,我倆暗度陳倉去了日本,我睡了你一禮拜。”
蘋果皮朝他子彈一樣地,他一折子避過,龍七說:“我發現你老惦記著我跟司柏林有點什麼事兒,以前也是,我就奇怪了我喜歡他這好吃鬼干嘛,好吃好喝的從來不分我半個。”
“事實證明你倆就是有事兒也能被我黃了。”
“重點是這個嗎?”
“但我覺得夢里那妞又不是你。”
“就因為我看上司柏林了?”
“因為那妞能跟我正常聊天,聊得還好。”
蘋果皮又要飛,他的子往后條件反地挪了一點兒,龍七最后沒彈出去,收著了,換話題:“晚上電影你別去看了,也沒什麼意思。”
“要去。”
“那你看到有些節別有反應。”
他知道“有些節”指哪些,撂一眼,從果盤里拿個蘋果,啃在里,進屋看電視去,而龍七繼續跟方璇扯皮一些關于小龍蝦的事,伍依姍正在大群里發這幾天拍攝的視頻素材,這邊方璇也把龍七,鄔嘉葵和吳爾拉了個群,在里頭狂發有關小龍蝦的吃法鏈接,微信響聲像是機關槍一樣,發到一半把靳譯肯也拉進了群,但他的手機沒響兩下就沒聲了,看群員,靳譯肯秒速退群了。
方璇懟出一個問號表包。
鄔嘉葵:璇。
這倆人在同一房間還用微信聊,也是有意思,方璇回一問號,鄔嘉葵:安靜點,吵死了。
于是微信安靜如,取而代之的是樓下方璇和鄔嘉葵房間,傳來一陣轟的打鬧聲。
……
六點五十,離電影開場還有十分鐘,龍七已經跟鄔嘉葵坐影院里了。
Advertisement
兩人一人比一人帽檐得低,靳譯肯在右手邊,抬著二郎,撐著臉,方璇在鄔嘉葵的左手邊拉著吳爾打游戲,屏幕照在那兩人臉上,打得熱火朝天的。
葛因濘們稍晚一些到,雖然沒湊上同一撥路程,但到底還是來了,鄔嘉葵給們買的位置在前排,和最后一排的們隔了兩三排,就顯得兩撥人完全沒關系似的,們了座,其他觀眾也陸陸續續進了影院,興許是后排一撥人都太惹眼了些,他們找著座位,時不時往后看過來,又覺得不大可能是們以為的人,所以就只是多看幾眼,沒惹出太大靜。
一陣悉悉索索的座躁后,電影開場了。
開頭便是香港九龍夜市,風的老板娘在店子后巷遭鈍擊打致死,被警方推斷為意外事故,中年偵探臧習浦老板娘弟弟委托接下案件,從現場的蛛馬跡推究,最大嫌疑人是曾在現場逗留乞討食的某個人,龍七。
的第一個鏡頭出現在老板娘弟弟的閃現回憶中,胡扎著的頭發,穿著不合的,過大的服,在店門口直直站立著,盯著食客筷下的食,胖乎乎的禿頭老板招呼進店,給
一碟燒的同時的,只顧低頭把塞進里,連筷子都不用,吃得和手都油滋滋的,直到被老板娘發現,用鍋勺捻出去,抓碗,在扯打下塞完一整碟燒,塞滿了,才折回店里狠踹老板一腳,再被老板娘揪著頭發轟出店,狼狽而逃,逃走時一個回眸的眼神,像吃飽了的小野狼,錙銖必報,滿目的惡。
影評說,這是讓人起皮疙瘩的一個鏡頭。
從這個鏡頭后方璇就沒玩手機了,看得認真,屏幕的照在影院每一個人臉上,龍七的手指輕輕攪著紙盒里的米花,靳譯肯也撐著臉,安靜看,手肘著的手臂。
Advertisement
而后的節展開撲朔迷離,一環套一環,從先開始被懷疑的暴力擊殺者變為唯一目擊人,從拾荒者變為逃命者,臟差的環境都鉆,任何靜都驚警覺,和偵探玩羅生門,和真正的兇手躲貓貓,衫襤褸跳過海,不要命地奔過車流,也在渡船上與狗搶過食,從一起夜市老板娘的兇殺案,牽引到高婦的連環謀殺案,再探到頂上高
層的權謀涌塵封事,案越查越驚心,的份也越來越深,看似輕狂暴斂,善用手段的警察周以聰反而是救命稻草,看似忠良正直,始終陪伴的偵探臧習浦反而是催命符,看似無辜牽扯案,骯臟的渡客龍七,在多次被懷疑,被信任,再被懷疑的反轉中,終最后一層面目。
全片最后一個鏡頭,開放式結局,戛然而止的背景音樂,寒冬的碼頭下,孤的背向波濤洶涌的大海,從臉到眼的大特寫,散著腥味兒的一呼一吸,整個影院都沉在迷霧未散的眼睛里。
野狼茍活,錙銖必報。
好到什麼程度,就是臧習浦和的激戲出現時,是投高點時的張,與無關,與個人也無關,就是已經忘記這個角是演的,就是鄔嘉葵在片尾幕后人員名單放映時,不那麼甘心,但又基于對專業的尊重,輕輕鼓了一記掌。
然后,整個影院被帶,掌聲陸陸續續地響,連著前排那一撥,也無所適從地看著周遭,跟著鼓了幾聲。
那一刻也算有點覺悟。
為什麼向來劣跡斑斑,不公眾口舌照顧的,在攤牌了HIV的事之后,反而到了大量理解和寬容,不全是因為連芍姿的公關運作,不全是憐憫,是因為正巧趕上這時期有作品,給大眾出了一張及格的績單,證明這個人不是一副空殼,的落難織在功的如好評中來,才有了重新起立的底氣,才有資格在于弱勢時接自我的寬容,失敗者的落難才會萬箭穿心,功者的落難只是人生一道“小坎兒”。
殘酷,又實用。
算明明白白了。
而鄔嘉葵請所有人看《冷蟬》這一招也看出來了,不是來挨打的,下午輕得跟撓似的撕法不盡興,這會兒才算鄔嘉葵式的,真正的,神上的撕,不服是嗎,覺著自己牛壞了是嗎,心比天高是嗎,好,都給我來把這電影看了,拉片兒都來一遍,別真把大前輩當空降生了,圈兒都沒進,社會都沒,一個個的抱團霸凌先使上了,年輕狂又牛的一群人活生生在你后頭坐著,哪個不是經了風霜雨一路殺過來的,人惦記你這點小小?小屁孩兒都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
在對手拿手的領域最大化碾對手,實現神凌遲,這一招,當初鄔嘉葵追靳譯肯的時候就把龍七這麼按在地上過,現在又駕輕就地套用在葛因濘這一撥人上,使得爐火純青,要不是結束后特意給那撥人留了個“回去給這片做個拉片”的作業,龍七真沒察覺出來,完事兒,方璇又朝著那林貌似隨口地補一句:“誒那林,你真不記我這高中同學了?我很記得你呢。”
那林在葛因濘和另一孩的后,一愣。
“看你現在過得不錯,你還記得張楊嗎?就你那前男友,他現在也有朋友了,唉,總算是走出來了,想當初你劈,劈的還是張楊親妹妹,你最好閨的男朋友,這倆兄妹可不好過,現在總算彼此都有新出路了,你放心啊,我今天看見你,也會把你的事兒跟他倆匯報一聲的,讓他倆也放心。”
止都止不住,任憑那林臉青一陣白一陣,方璇就這麼跟笑面佛似的,連珠炮掛地懟出口了,長進了,語言組織上比當年對待龍七時文明多了,聽得旁邊幾個生也面面相覷。
葛因濘沒出聲。
就這麼和鄔嘉葵一嚴一松,一唱一和,把人里里外外的火星兒都滅了。
……
夜里九點,空氣里飄著細雨,靳譯肯去提車,吳爾意猶未盡地刷著《冷蟬》的影評,對《小鎮》的前景很有信心,對著方璇嘰嘰呱呱說不停,方璇一頭熱也要跟著投資,服裝贊助那塊兒家包了,而龍七和鄔嘉葵分別靠在影院偏門的兩側,鄔嘉葵給遞了煙,給鄔嘉葵打了火,停車場的照出線,煙氣漫在削瘦的下邊,兩人聊著天,鄔嘉葵說別急,明年《邊境》一上,碾稿名單的頭一號人就是龍七。
龍七說你怎麼這麼可。
“你覺得我可有什麼用,你男朋友不覺得。”
煙氣一陣漫開,龍七問:“奚靜看中的那劇本,你有多想要?”
“本來一般般想要,但搞了那點兒小作后,超想要。”
“雙主懸疑戲?”
“嗯。”
“人設大概什麼樣?”
“不想告訴你,你聽了一定興趣。”
但是三秒后,鄔嘉葵用手指撥著頭發,仍舊說:“一個是全家滅門案的生還者,芭蕾舞者,理智,悲觀,一個是泡在管所長大的未年,暴力,病態。”
“你和奚靜搶的是芭蕾?”
“嗯。”
“給我留的那個還真適合。”
“其實奚靜比我有勝算,”鄔嘉葵說,“舞者更年長一些,是個單親媽媽,我的臉不像是個人,但我這世仇不死,奚靜做任何事都不會那麼容易。”
“我有個想法,你要不要聽一聽。”
鄔嘉葵看。
指頭撣了一記煙,龍七說:“管所給你,芭蕾給我,你需要轉戲路,我不想被固定戲路,你跟奚靜爭芭蕾不一定能贏,但是你跟別人爭管所一定可以,奚靜我太多次,還打著讓我幫數錢的主意,我不樂意,你倆的仇多的是機會慢慢手,這一次我幫你鋪路,我先上,你墊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穿成大佬的嬌軟美人
作品簡介: 按照古代賢妻良母、三從四德傳統美德培養出來的小白花蘇綿綿穿越變成了一個女高中生,偶遇大佬同桌。 暴躁大佬在線教學 大佬:「你到底會什麼!」 蘇綿綿:「QAQ略,略通琴棋書畫……」 大佬:「你上的是理科班。」 —————— 剛剛穿越過來沒多久的蘇綿綿面對現代化的魔鬼教學陷入了沉思。 大佬同桌慷慨大方,「要抄不?」 從小就循規蹈矩的蘇綿綿臉紅紅的點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出格表演。然後全校倒數第一抄了倒數第二的試卷。 後來,羞愧於自己成績的蘇綿綿拿著那個零蛋試卷找大佬假冒簽名。 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蘇綿綿拿出了自己覺得唯一擅長的東西,「我給你跳支舞吧。」 ———————— 以前,別人說起陸橫,那可真是人如其名,又狠又橫。現在,大家對其嗤之以鼻孔。 呸,不要臉的玩意。
34.1萬字8 9661 -
完結794 章

步步逼婚:搶來的老公
“戰少,不娶我,明天你勢必榮登八卦報紙頭條丑聞。”左胸第五根肋骨輕微骨裂,肩、臂、腿等數十處皮下青紫——一紙驗傷單,唐樂樂成功拆散京城最令人艷羨的情侶檔,逼婚仰慕十年的男神,上位戰家少夫人。所有人都在翹首等著戰大少將這個不擇手段的女人踢出這場婚姻,直到兩年后,唐樂樂和最火天王巨星以半裸照香艷出境,她親手將報紙扔到他的臉上,淡笑諷刺,“如你所愿,戰墨謙,我們離婚。”頭頂綠油油的男人卻一把將她遞過來的離婚協議撕成粉碎,“你愛我的時候逼我結婚,現在他媽的老子愛你到死,你想走,除非我死!”——如果愛是一場偏執癥,那麼在她終于痊愈的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
197.1萬字8 18170 -
完結506 章

離婚后,她靠龍鳳雙寶掀翻葉氏財團
五年前,林夕懷著身孕被陷害!深愛多年的男人為了心里的白月光棄她不顧!這種狗男人還留著過年?他不會愛她,也不會是孩子的好爸爸!林夕盯著他走向白月光的背影,毅然決定,“葉景州,我們離婚吧!”五年后,她帶崽強勢歸來,領著龍鳳雙寶虐渣打臉,掀起帝國風云!曾經那個不可一世的狗男人將她逼近墻角,氣息灼熱:“說,這兩個孩子是跟哪個狗男人生的?”林夕面無表情:“關你屁事!”得知狗男人竟是自己,葉氏集團總裁親自上門跪榴蓮,“老婆,我錯了!”龍鳳雙寶突然殺來,“滾!想要娶媽咪,先過我們這關!”
86.1萬字8 31089 -
完結224 章

假千金跑路后爆紅了
沈聽瓷風風光光的活了十八年 才知道自己竟然是個鳩占鵲巢的假千金! 想到夢里她的悲慘結局,沈聽瓷果斷選擇跑路 憑著絕美容顏+神級演技,一頭扎進了娛樂圈 不料第一個綜藝就碰上了真千金和她的前未婚夫 本以為是個大型陰陽怪氣現場 沒想到真千金竟然主動套近乎? 未婚夫還一副被她拋棄的怨夫樣? 傳說中的京城帝少還管她叫姐? …… 說好的炮灰假千金呢? 怎麼成了團寵劇本?
43.7萬字8 8241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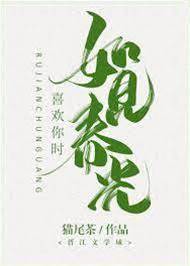
喜歡你時,如見春光
朋友給周衍川介紹了一個姑娘,說她不僅臉長得好看,學識也很淵博。 周衍川勉為其難加好微信,禮節性問:“林小姐平時喜歡什麼?” 林晚回他:“我喜歡看鳥。” “……” 周衍川眉頭輕蹙,敷衍幾句後就沒再聯繫。 後來朋友問起他對林晚的印象,周衍川神色淡漠,連聲音都浸著寒意:“俗不可耐。” · 時隔半年,星創科技第三代無人機試飛,周衍川在野外見到了林晚。 她沐浴在漫山春光之中,利落地將三角架立在山間,鏡頭對準枝頭棲息的一隻小鳥,按下快門時,明艷面容中藏進了無限柔情。 回城的路上,周衍川見林晚的車子拋錨,主動提出載她一程,怕她誤會還遞上一張名片:“你放心,我不是壞人。” “原來你就是周衍川。” 林晚垂眸掃過名片,抬頭打量他那雙漂亮的桃花眼,幾秒後勾唇一笑,“果然俗不可耐。” 周衍川:“……”
28萬字8 19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