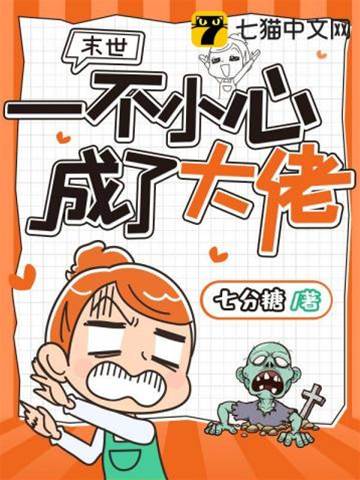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女校》 第七十二章 黑名單 (1)
龍七不躲,對著他灼灼的視線:“有沒有點誠意,倒是先跟白艾庭分手啊。”
靳譯肯再朝走一步,快將整個人到門板上,兩人之間的鼻息相互錯:“沒法分,但是你,我也要。”
“人渣。”
而靳譯肯不在意這兩個字,兩人的鼻息越來越近,心跳聲也越來越清晰,悶熱的樓道里,泛黃的燈,腳踝傳來的余痛與樓外天際的一聲悶雷,都促此刻的曖昧,鄰居家的門突然開啟的時候,龍七側過頭,靳譯肯的過的角,親在的臉頰上,而對門提著垃圾袋出來的姐姐在玄關一愣。
隨后立刻關門下樓,一副“放心我自帶狗糧,我什麼都沒看見“的自清態度,龍七這時重新打開后的門。
靳譯肯抓住的手腕,半個子進了門,半個子仍在外,迅速手:“你連給白艾庭的待遇都沒法給我,還妄圖吃下一個敵視白艾庭的我,靳譯肯你胃口真大。”
“你哥今晚打算在網吧通宵,你舅媽凌晨兩點才結束晚班,你一個傷員,明天怎麼去學校?”
話題一下子調轉,怔了一下,還沒答,他接著說:“我來接你。”
“你的腳傷,”再而說,“我來幫你養。”
龍七扶著墻站在半開半閉的門口,看著平靜地說著這些話的靳譯肯,就好像上一個話題已經如風散去,他的手機這時候響,視線下移,看著他從兜里拿手機。
屏幕上亮著“白艾庭”三個字。
靳譯肯開接聽鍵的時候,龍七幾乎毫不猶豫地關門,但偏偏被他擋住,的力氣大不過他,門仍舊半虛掩,而他一邊穩穩地把著門,一邊將手機擱到耳邊,靜謐的樓道里,白艾庭的聲音夾雜著電磁波,清晰地傳進兩人耳朵:“譯肯,我媽聽說你不舒服,幫你煲了個湯,我現在準備帶過來,伯父伯母在家嗎?在的話我多帶一點?”
Advertisement
“不在。”
“那好,我過來……不打擾你休息吧?”
靳譯肯沒答。
他此刻的眼神真有意思,安安靜靜,十足耐心地盯著龍七,仿佛他的回答全取決于的回應,白艾庭在那方尋求肯定般喊他的名字,龍七的心口輕微起伏。
當白艾庭第三次喊他的名字,而他也正要開口的時候,龍七終于放開手,門板撞墻上,足足地敞開。
多麼強烈的暗示,而靳譯肯多麼聰明的人,直接掛了電話進門,接著,龍家的門砰一聲從里踢上,樓外一聲滾雷響。
多久之后,都始終記得和靳譯肯在龍家有過那麼一次,而那一次,夾雜著虛榮稚的勝負,辛辣刺激,是邁錯的第一步。
靳譯肯是早上六點從龍家走的。
天還沒亮,舅媽還在主臥里睡得鼾聲如雷,凌晨四點回家的龍信義還著上癱在客廳沙發上,龍七的那件外被他當被子蓋在肚子上,他睡得像死豬一樣。
龍七走過散落一地的書包,服,屏著呼吸蹲到沙發旁,從那件外口袋里出自己的手機和錢,隨后再將龍信義私藏已久的煙、打火機和各種人碟片放到茶幾上最顯眼的位置,往電視機柜里塵封已久的DVD里也放了一張,打開電視,將遙控塞龍信義手里。
做完這些后悄聲出門,靳譯肯正倚在樓梯口用手機車,將防盜門關上,遞他錢:“諾。”
他側額瞇了一眼,沒在狀態,龍七說車費,他才往看第二眼,面部表不是那麼喜悅,但也算估清楚了的脾氣,沒接錢,問拿手機。
“干什麼?”
出手機給他,他開微信頁面輸自己的微信號:“我不用現金,你線上轉我。”
Advertisement
所以靳譯肯就這麼搞到了的聯系方式。
下樓后,他幫買了豆漿和早點,龍七的腳已經能著地了,雖然還有些跛,但不影響走短程路。靳譯肯去學校前必須得先回一趟家,想帶著,但拒絕跟著靳譯肯繞大遠路,也拒絕他另幫一輛車,只接先搭他的順風車去附近的地鐵站,自個兒搭地鐵去學校。
早晨六點,天霧蒙蒙的,馬路上車流稀,陣陣冷嗖嗖的風,唯有手里的豆漿熱乎著。等車的過程里,龍七對著馬路發呆,而靳譯肯與司機打完電話確定時間后,手臂突然越過的腰,還呆著的龍七被他往后拉進懷里,肩頭到他下的重量,他就這麼從后抱著,當真像是一對正正經經的,困乏到懶于口,在四月初的清冷早晨,和他互相取暖。
后來,靳譯肯將送到地鐵站,獨自上了早班地鐵。
在地鐵上咬著面包,一邊聽音樂,一邊閑來無事地在校園論壇上搜索“靳譯肯”,有關他的討論帖子有上百條,出乎意料的是只有三四條帖才跟白艾庭有關,才清楚他是個多惹眼的人,后來點進他的主頁,正好上他新發的一條狀態。
不知什麼時候拍的房間窗口一角的照片,老舊的窗臺,窗臺外蕭瑟的街景,天未亮,路燈亮著,配文卻是:朝。
想象此刻靳譯肯正坐在車后座,手指剛按下發送鍵,接著或許開始補眠,或許開始回想昨晚和同床共眠的細節,覺得前者可能比較大。
然后手機的震為送來第三種可能,屏幕上方跳出信息提示,靳譯肯發來一句話。
——晚上接你吃飯。
龍七看著這六個字,面包在里緩慢地咀嚼,手指在鍵盤上長久地停頓,后來沒回復,塞回外口袋。
Advertisement
那時,注意到坐在車廂對座的人。
生,穿著與同一學校的制服,外搭一件雪青的薄針織衫,膝蓋上擱著一本書,正輕輕地翻著頁。
龍七往那兒飄去一眼,的指腹正巧劃過紙頁,發出淅淅瀝瀝的輕微響,額前下的劉海遮住了雙眼,但遮不住偶爾出現的細長睫,作細膩,白,氣質寧靜致遠,越看越眼,但因沒有抬頭,龍七只猜是同校的學生,后來沒再看,繼續將耳機里的音量調大。
大約十分鐘后,對面的人將書合上,龍七百無聊賴地瞄去,看到用手心額,咳嗽一聲,同時從包里拿出口罩戴上,隨后抬起頭。
龍七別開視線。
早班地鐵,乘客稀,每一座上只有三四人,列車經過隧道,隧道墻壁上的照明一陣一陣地掃過車廂,沒人說話,只有列車與軌道的巨大燥聲。
第三次看過去時,生靠著椅背,臉上戴著大大的口罩,雙眼正閉著。
龍七的手機在手心里慢悠悠地轉著。
那時候終于憑著生的雙眼記起“董西”兩個字,腦對這個名字所帶來的回憶里沒有任何負面印象,堂而皇之地觀察,董西的眼睛始終閉著,毫未察覺來自對面的考量目。
而且,心口的起伏漸漸變緩,放在書封上的手指也漸漸到膝蓋上,似進一種淺眠狀態。
龍七笑。
手指輕輕地繞著白的耳機線。
后來,地鐵一次加速,董西的腦袋朝右邊稍微傾斜,龍七安靜地看著,調低耳機里的音樂。
那一次傾斜為一次契機,董西的子越來越偏右,而右邊是空冰冷的座椅,龍七將最后一口面包遞進里,拿起放在旁邊空座椅上的溫豆漿,在手中搖了搖。
Advertisement
董西淺睡著。
吸一口豆漿。
甜甜的豆漿過嚨,看著董西的頭發從肩頭下。
而當徹底往右邊傾斜的那一刻,龍七終于。那一瞬間列車沖出隧道,晨早的第一抹朝灑滿整個車廂,的影在車廂中央快速走過,一個邁步一個轉一個座,地面上有快速轉的影子,發梢尖上閃著,空氣里一陣香氣,坐下的同時,手中的豆漿面輕微晃,董西的腦袋穩穩當當地落到肩頭,這一切都悄無聲息,唯獨心口輕微起伏。
列車外樓宇間有萬丈斜,灑在和董西的上,凝一道形的金邊。
側頭看。
董西毫無察覺,輕緩的鼻息間,似有一書香味。
龍七的指頭在膝蓋上點了點。
隨后,董西在的肩上睡了兩站路。
龍七將手機擺到手臂旁,拍了兩張的照片,角因而輕輕地勾,只是按第三次快門時,董西睫輕。
地鐵正好到達某一站,龍七收手機。
董西將醒的那一刻,列車門開啟,龍七起離座,董西扶額坐起,而龍七頭也不回地往列車外走。
不知道董西有沒有從窗口看看,也不知道后來是否還記得某年四月清晨六點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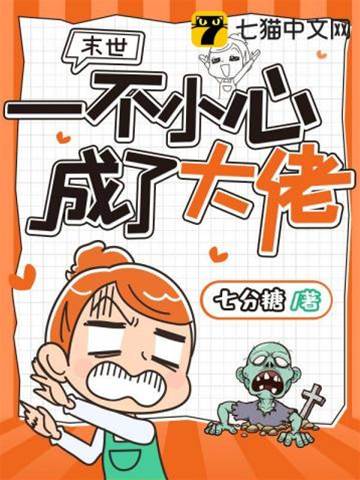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740 章

團寵大佬:真千金又掉馬了
林笙一出生就被扔進了大山里,被一個神秘組織養大,不僅修得一身好馬甲(著名設計師、格斗王、藥老本尊……),本以為有三個大佬級爺爺就夠炫酷了,萬萬沒想到,叱咤商場的殷俊煜是她大哥,號稱醫學天才的殷俊杰是她二哥,華國戰神殷俊野是她三哥,娛樂圈影帝殷俊浩是她四哥。某天,當有人上門搶林笙時:爺爺們:保護我方囡囡!哥哥們:妹妹是我們的!傅西澤一臉委屈:笙笙~我可狼可奶,你確定不要嗎?林笙:我……想要
131萬字8 269482 -
完結1602 章
丑妻逆襲夫人火遍全球了
云綰是被父母拋棄的可憐女孩兒,是她的養母善良,將她從土堆里救了出來。在漸漸長大的過程中,..
142.6萬字8.18 448598 -
連載424 章

咬色
爲了讓她乖乖爬到跟前來,陳深放任手底下的人像瘋狗一樣咬着她不放。 “讓你吃點苦頭,把性子磨沒了,我好好疼你。” 許禾檸的清白和名聲,幾乎都敗在他手裏。 “你把你那地兒磨平了,我把你當姐妹疼。” …… 她艱難出逃,再見面時,她已經榜上了他得罪不起的大佬。 陳深將她抵在牆上,一手掀起她的長裙,手掌長驅直入。 “讓我看看,這段日子有人碰過你嗎?” 許禾檸背身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笑得肆意淋漓,擡手將結婚戒指給他看。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71.8萬字8.18 13158 -
完結283 章

大佬的白月光又野又狂
不小心上錯大佬的車,還給大佬解除了三十年的禁欲屬性。盛晚寧正得意,結果被大佬一紙狀告,進了局子。她憤憤然寫完兩千字懺悔書,簽下絕不再犯的承諾,上繳五千元罰款……暗咒:厲閻霆,有種你別再來找我!……一年後。厲閻霆:“夫人,你最喜歡的電影今晚首映,我們包場去看?”她:“不去,你告我啊。”……兩年後。厲閻霆:“夫人,結婚戒指我一個人戴多沒意思,你也戴上?”她:“戒指我扔了,有本事你再去告我!”……五年後。厲閻霆:“夫人,老大已經隨你的姓,要不肚子裏的小家夥,隨我,姓厲?”她:“憑什麽?就憑你會告我?”……
72.7萬字8.18 132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