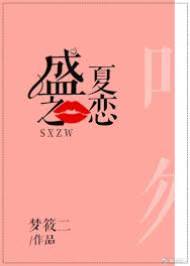《告白》 第67章 告白 這麼多年,標記了數次的來回。……
客廳里只剩下外公和許隨在客廳,外婆也去和他們打麻將了。
下午三點多,天氣很好,室線敞亮,斜斜地打了進來,照得人暖洋洋的。
“一一啊,你家里是哪兒的?”外公拄著拐仗笑瞇瞇地問。
“黎映,在江浙一帶。”許隨答。
“南方啊,那是個好地方。”老爺子說道。
“家里還有什麼人?都做什麼的?”
許隨垂下眼睫,扯了扯角:“爸爸是消防員,初中的時候因為出任務意外去世了,媽媽是老師,家里還有一個。”
老爺子聽著聽著心疼起了這個孩子,安道:“好孩子,你要是不嫌棄我這個老頭子的話,常過來吃飯,外公教你下象棋,你外婆還會花呢,讓教你。”
“好。”許隨彎起角。
心里有一暖意,覺得,周京澤一家都是很好的人。
“瞧我這腦子,陪我下盤象棋怎麼樣?”老爺子拄著拐仗敲了敲地面,“我剛好去樓上拿我的眼鏡。”
“我扶您。”許隨站起。
許隨小心翼翼地扶著周京澤外公上樓,一路扶他進書房。老爺子東翻西翻,只找到了一副眼鏡,他開口:“孩子,我在這先找著,你幫外公去京澤房間看看有沒有象棋,平常他也會拿去玩,就在最里面那間。”
“好。”許隨點點頭。
許隨走了出去,走到臺最里面那間房間,手放在門把扶手,擰開推門走了進去。
周京澤的房間跟他本人的風格如出一轍,冷調,但也,床單是麻灰的,一本飛行航空雜志扔在床頭。
一張沙發,地毯,墻上掛著投影儀,矮柜上一排航模。角落里還放著一把棕的大提琴。
許隨走過去,認真地找象棋,怎麼找都沒有。
Advertisement
視線不經意地一撇,一盤象棋擺在沙發的角落里。
許隨做事一向細心,坐過去,打開棋盤,檢查有沒有掉的棋子,找了一會兒,發現沙發邊上的隙卡著兩顆棋子。
抬手去拿棋子,結果另一個棋子吧嗒一聲掉落,卡在更深的隙里。
許隨只好彎腰,臉頰著沙發,費力地用進隙里去抓。
索了好一會兒,許隨終于抓到那顆棋子,慢慢起,結果一不小心撞到了在沙發墻壁上的地圖。
“哐鐺”地一聲,吸鐵石掉下來。許隨撿起吸鐵石回去,發現地圖上有好幾個標了紅藍的城市記號。
藍圈好的城市是出發點,紅圈好的城市是終點,中間用一線連著。
而這上面有無數紅線。
許隨發現,這些出發城市都統一指向三個終點,分別是香港,京北,南江。
南江是讀研的城市,一個不確定的猜想在心里慢慢產生,許隨的緒說不出來,只覺得呼吸沉重,正盯著上面的地圖。
一道聲音從門口傳來,問道:“一一,象棋找到了嗎?”
“找到了,”許隨回頭,聲音有點啞,“外公,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外公拄著拐杖走進來,他坐在沙發上看了一眼,笑笑說:“說實話,我也不太清楚。孩子啊,你不好奇,我為什麼一眼就認出你來了嗎?”
“為什麼?”許隨覺覺嚨有些難。
下午的很好,周京澤外公坐在那里同許隨說話,他的語序有些混,但許隨還是捉住了一些關鍵詞。
“我記得他讀大學的時候,忽然有一天說要領個生帶回家讓我看看,”外公回憶了一下,說道,“他說,外公,那個孩一一,很乖,也善良,我很喜歡。”
Advertisement
周京澤倚在門口,上沒有了那孟浪氣息,垂下幽黑的眼睫,認真地開口,在想起許隨時不自覺地笑:
“跟在一起,我第一次開始想到了以后。”
老人家以為能見到許隨時,可在親外孫生日那天,周京澤徹夜未歸,飯桌上的菜和長壽面都沒能吃上一口。
他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生日。
“你們當初分手,這孩子就跟瘋了一樣,他一向自律有規矩,可一連好幾天都在酗酒,將自己關在房間里面不出來,課也不去上,十分頹喪,張媽都不敢靠近他這間房間,”外公語氣頓了頓,嘆了一口氣,“當時,他那個混賬模樣,如果我不管他,就沒人管他了。”
“后來,他終于肯出來,緒好了點的時候就跟我下象棋,陪我去花園種樹。我看他狀態好得差不多,肯正常進食了,會出去,也重新撿起落下的課,我以為這事就過去了,可哪能想到有一天——”
在一個很平常的午后,周京澤帶著貓和德牧來外公家吃飯,飯后他帶它們去曬太,1017 原本翻著肚皮在他腳邊曬太,忽然,它瞥見蝴蝶飛來,于是跳上花架去玩了,沒一會兒就不見了。
外公拿著除草剪,彎著腰找了一會兒貓,沒找到,看周京澤坐在長椅上發怔,問道:“貓呢?”
周京澤坐在院子里的長椅上,腳下的荒草蔓延,快要淹沒爬著紅銹的椅子,他抬眼看著正前方,黑漆漆的眼睫有點,紅著眼,聲音嘶啞:
“外公,我把弄丟了。”
小時候周京澤被關在地上室,遭他爸暴打待,一直哭個不停。后來他發現哭不能解決事后,就再也沒哭過。
這是老人家第一次見周京澤紅了眼眶。
Advertisement
外公看著眼前的姑娘,繼續往下說:“后來我就不知道嘍,他后面去國訓練,再畢業,滿世界地飛。可也經常回來,問他怎麼老回來,他就說就是飛機拐個彎的事,一回來就往房間里鉆,現在看來是在鼓搗這個地圖。”
許隨順著周京澤外公的手勢再次看向地圖,的手悄悄握拳,角快要被揪得變形,可還是沒忍住,一滴又一滴的眼淚砸在地上,視線一片模糊。
地圖上,這多年,無數個藍點通往三座城市,標記了數次的來回。
杉磯——香港,距離約11600公里,耗時16小時。
蘇黎世——南江,距離9002公里,耗時10小時。
柏林——京北,距離8984公里,距離8984公里,耗時18小時。
……
這些航程途徑歐洲,里海,中東,亞洲,但都通往同一個地方。
香港是他的終點,京北城是他的終點,南江也是他終點。
許隨在哪兒,哪里就是他的終點。
許隨一個人站在那里安靜地哭,眼睛,鼻尖都是通紅的,外公也沒責怪,只是說:“我家這個孩子,從小的苦比較多,導致格可能有點缺陷,不會表達,也不會去,你多擔待一下他。”
……
后面許隨陪外公下棋的時候,緒漸漸恢復,臨走下樓時,特地去洗手間洗了一把臉,看向鏡子里的自己臉好點了才出去。
周京澤拎著工箱從后花園回來,屁后面跟了兩個小孩。果果一臉高興地走進來,撲到老人家懷里,偏頭給大家看耳邊戴著的小花,語氣有些小驕傲:“叔叔給我戴的小花,他說是因為我漂亮。”
許隨失笑,上午這小孩還怕他怕要命,僅是一會兒的時間,周京澤就收獲了一個位小孩的芳心。
Advertisement
周京澤洗完手,等許隨收拾好,虛攬著的肩膀想帶人離開。外婆忽然喊住許隨,遞過來一個錦盒,語氣溫:
“一一,見到你外婆很開心,第一次見面,外婆也沒什麼禮給你的,這是以前他媽留下的,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許隨打開錦盒一看,是一只很好,翠綠滴的玉鐲子。這哪是什麼不值錢的東西,嚇一跳,忙推了回去,說道:“太貴重了,我不能要。”
“你這孩子,收下!”
許隨覺得兩人老人真的很好,要是知道了不是周京澤朋友,會怎樣失落。想到這,還是擺手,可一抬眼,對上兩位老人期待的眼神,拒絕的話就說不出來了。
最終收下了這個禮。
周京澤開車載許隨回家,一路上,他發現整個人都有點不對勁,失魂落魄的,不知道在想什麼。
“不開心?”周京澤抬手掐了一把的臉。
許隨拍開他的手,說:“沒。”
周京澤打著方向盤偏頭看了一眼,發現眼睛都是腫的,眼眉頭蹙起,
嗓音低沉:“哭過了?”
“沒,前一晚熬夜熬的。”許隨垂下眼睫解釋。
周京澤沉了一會兒,看得出不開心,看了一眼時間,語氣輕哄:“那要不要去吃點東西?”
“我不,”許隨搖頭,猶豫了一會兒從包里拿出那個錦盒遞給他,吸了一口氣,“鐲子你找個時間還給外婆吧……”
車子正緩速向前開,倏地發出一聲尖銳的剎車聲,許隨不控制地向前一磕。周京澤打著方向盤,車子靠邊停了下來。
車一陣沉默,周京澤在一片死寂中開口,聲音沉沉,問:“為什麼?”
“太貴重了,而且才第一次見面……”許隨的聲音有點啞。
周京澤的下鄂線繃,弧度凌厲,眼睛鎖著:“我說過,我喜歡的,他們也會很喜歡。”
氣氛僵持,許隨只覺得嗓子干得厲害,有很多想說的,又不知道該從哪說起。
周京澤心底有些說不出來的無力,他煩躁得想起拿中控臺上的煙,想起什麼又放棄。
最終他摁下車窗,大片的風灌了進來。日落時分,黃昏呈現一種濃稠的昏黃,半晌,他看向正前方,風聲很大,把他的聲音割了碎片,語氣緩緩:
“你要是不想要,就扔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5810 -
連載1085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5萬字8.18 24414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89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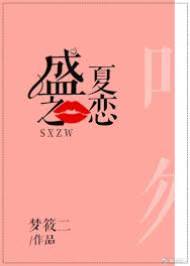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