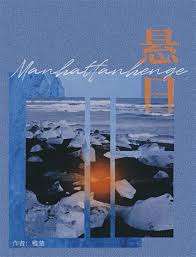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我來自平行時空》 15.15
大晚上的,支巷裡黑燈瞎火。
封北的車龍頭左拐右拐,拐進一條坑坑窪窪的巷子裡,自行車像只青蛙似的蹦跳。
高燃坐在後座,顛的屁疼,“小北哥,你不是隊長嗎?怎麼還騎自行車?”
封北一煙沒完就給滅掉了彈出去,“隊長不是總裁。”
“我窮的叮當響,就這自行車還是二手的。”
高燃蹦出口頭禪,“假的,我不信。”
封北低笑出聲。
高燃拍男人後背,兇的說,“笑屁啊!不準笑!”
封北的面黑了黑,“無法無天的小混蛋。”
高燃脖子,用腳趾頭也能想得到,沒人敢這麼在隊長面前皮,他撇撇,不支聲了。
封北頭往後偏,“怎麼不說話了?”
高燃咕噥了句。
封北聽清了,年說,我怕你生氣。
夜風著一涼意,快秋了。
高燃聽到男人的聲音,“車停在河邊,開不進巷子裡,就不怎麼開。”
他喔了聲,剛要說話來著,自行車突然一蹦老高,像蛇似的扭,一頭栽到前面的那堵牆上。
高燃臉撞在男人背上,疼的他鼻涕眼淚一起往下淌,“臥槽!”
封北雙手夾著年的胳肢窩,把他從後座上抱下來,“流鼻了?”
高燃沒流鼻,流鼻涕了,疼的。
他瞪著男人,眼睛漉漉的,“真是的,你不會騎車就讓我來好了,逞什麼能嘛!看看,跑死巷子裡來了吧。”
封北額角,“你在我耳朵邊嘰嘰喳喳的,我這不就分神了。”
高燃不敢置信的嘖嘖,“你們刑警隊的主要考核容是臉皮的薄厚程度吧?”
封北的面部搐。
小混蛋的皮子可真利索。
高燃吸吸鼻子,“小北哥,你坐後面,我來騎。”
見男人站著不,他催促,“快點坐上去!”
Advertisement
封北挑挑眉,“行,你來。”
結果還沒騎出巷子,高燃就已經出了一汗,“你是不是在使壞?”
封北一臉無辜,“使什麼壞?”
高燃翻白眼,裡嘀咕,“別以為我不知道。”
封北不小心到了年的腰。
高燃渾栗,氣籲籲的說,“你不要我那兒,死了!”
封北哦了聲,小混蛋怕啊。
他稚的又了一下。
高燃抖了抖,他氣結,車歪歪扭扭,差點兒連人帶車的摔地上。
“這是我第一次騎車帶你,也是最後一次,我誓,下次我要是再帶你,我就是小狗!”
封北笑,“小狗。”
高燃,“……”
到公安局的時候,高燃大汗淋漓,累狗了,大口大口著氣,“你……你也不跟我……不跟我換著騎……要不要……要不要臉?”
封北很顯然不要臉。
他沒坐過自行車後座讓誰帶,覺得像個姑娘家家的,別扭,今晚是頭一回,還別說,真舒服的。
當然,前提是對方的車技不錯。
高燃的車技可是練過的,好的沒話說,就是晚飯沒怎麼吃,很吃力。
他出手問男人要大水杯,“給我喝口水。”
封北皺皺眉頭。
高燃反應過來,嫌棄是正常的,能理解,他這麼想著,懷裡就多了個杯子,頭頂是男人的聲音,“我這杯子沒給別人喝過。”
“那我不喝了。”
“嗯?”
“我怕我喝了你的水,中了什麼咒,變你的傀儡,小說裡有這樣的。”
“神經。”
不多時,高燃坐在封北的辦公室裡,他來不及打量,就被對方塞了一大堆照片跟檢驗報告,還有石河村所有人的檔案。
封北在椅子上坐下來,一手夾著煙,一手支著額頭,“你大姨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婦人,上有很多人的影子,比如視兒子如命。”
Advertisement
“比起知道殺死兒子的兇手,你大姨更關心,也更急切的想了解我們都查到了哪些東西,遇事慌張,心理素質很差,出馬腳也不自知。”
高燃不吭聲,默認了。
他看著照片中表哥腐敗的,胃裡一陣翻滾,連忙拿起一摞資料蓋了上去。
封北將年的變化收進眼底,還是太年輕了,“殺害你表哥的兇手非常冷靜,甚至扭曲,存在極強的報複心理,你覺得石河村能備這幾點的會是誰?”
“我不知道。”
高燃是實話實說,人心隔肚皮,誰曉得那副皮囊下面是人是鬼。
表哥的死讓他更清楚的意識到了這一點。
封北靠著椅背煙,“地窖裡沒有工箱,也沒現異常,至於你表哥的房間……”
高燃的心頭一跳,“什麼?”
封北的面部被煙霧繚繞,“我的猜測得到了驗證,那裡的確是命案現場,可惜沒有提取到有價值的指紋跟鞋印。”
高燃鼻子,肯定沒有。
表哥的沒現前,他就在那屋裡住著,就算有,也被他給破壞掉了。
辦公室裡靜了會兒,高燃聽到男人說,“從表面上看,這件事跟你表哥的死無關,但是,往深挖挖就不好說了。”
語氣篤定。
封北吐出一個煙圈,“明天我會讓楊志帶你大姨過來,我親自審。”
高燃猛地抬頭,“你要審我大姨?”
“本來今天下午就該審了,你大姨神狀態不佳才推到了明天。”
封北盯著怒的年,“我的人找遍了你大姨家,包括整個村子和周圍村莊,都找不到王偉的形跡,要不你告訴我,他在哪兒?”
高燃的臉一白,“我怎麼知道?”
封北的眼睛又黑又深,“你給我的覺是,你知道。”
高燃到底還是個小孩子,看不出這是個套,他站起來,緒很激,急於澄清自己,“放屁!我又沒有開天眼,怎麼可能知道王偉在什麼地方!”
Advertisement
封北忽然笑起來,“逗你玩的。”
高燃的氣息紊,他是不知道王偉在哪兒,但他知道大姨的,牽扯著他的,所以他慌。
況且種種跡象都顯示王偉已經遇害了。
跟死了的表哥有關。
封北肯定知道了,只不過表哥已死,關鍵線索在大姨上,如果出事,那恐怕就真的沒人知道前因後果。
本來是一個案子,結果變了兩個。
棘手的是,兩個案子之間究竟存在著哪些聯系,能不能一舉兩得,通過一個案子破了另一個。
要是不能,那還有得查。
封北出聲,“不看看你表哥的檢報告?”
高燃堅決搖頭,“不看。”
封北說,“你的膽子太小。”
高燃臉不紅心不跳的犟,“有人怕小強,怕老鼠,怕蟲,怕土蠶等等等等,那些我都不怕。”
封北的額角一,無言以對。
接下來高燃避過了那些照片跟報告,認真翻起了石河村所有人的檔案。
封北不打擾,他去接杯水喝幾口,坐回椅子上假寐。
離開公安局已經過了十一點,回去是封北騎車帶高燃。
高燃坐在後頭打瞌睡,腦袋一下一下磕著,時不時到男人的後背。
封北了好幾次,怕年掉下去,就讓他把手放自己腰上。
高燃把汗的臉在男人背上蹭蹭,手同時放在他的腰上,抱住。
進了巷子,封北腳撐地醒年,手往後,“你是不是把口水流我背上了?”
高燃的睡意還沒完全消失,舍不得清醒,“沒有。”
封北說是嗎,“那我的是什麼?”
高燃笑嘻嘻的,“你自己流的汗唄。”
封北把後座的年拎下來,推了自行車進屋。
高燃屁顛屁顛跟進去,擺擺手就麻利的翻上牆頭。
封北了褂子一看,背後有一塊口水印,“……”
Advertisement
躺在床上,高燃回想起來,才驚覺自己那會兒在辦公室裡著了道,他沖著天花板罵罵咧咧。
王八蛋!
封北打了個噴嚏,八是被小屁孩給罵了。
他按按眉心,小屁孩有著異於常人的觀察力,也喜歡腦,善於現問題,解決問題,很值得培養。
這次的案子正是個契機。
第二天一大清早,高燃就出門遛彎了。
昨晚封北說今天會審問大姨,他心裡頭的很,想再回老家一趟,又在猶豫。
不能讓人知道自己的。
在這種況下限,考慮的也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解釋不清,很容易被當異類。
高燃買了兩油條一杯豆漿邊吃邊走。
他不知不覺穿過了七八條支巷站在河邊的石子路上。
路邊停著幾輛車,其中有封北的那輛,高燃懶得看個究竟。
這河不是高燃河瓢溺水的那條,水裡也沒有魚,大片的雜草狂野生長,沒人閑得慌跑下去割草。
路一邊是樹,一邊是菜地,種著些黑菜。
這一排住戶的空間要大一些,屋後還能搞出塊菜地種種菜,不像高燃家,住在中間,前後左右都是房屋,狹窄又抑。
家裡想買商品房,沒那個錢。
高燃啃掉最後兩口油條,喝杯子裡的豆漿,他決定去找封北。
這會兒封北應該在家。
前面有人在挖菜地,挖土時會帶出點兒沙沙聲。
高燃的腳步一頓,他快跑過去蹲在旁邊聽,耳邊的沙沙聲變得清晰,跟那次聽見的聲音重疊了。
大姨在挖坑,要埋什麼?
高燃隨便撿了樹枝在地上寫寫畫畫。
全是些掌握到的信息,很零碎,被他用箭頭給標了出來。
他不自覺的念出那幾個字,“不能讓人知道……不能讓人知道……”
啪地一聲響,高燃手裡的樹枝折斷,他猛一下站起來,頭暈眼花。
大姨念叨那句話的時候,正在埋。
是地王偉,他被埋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總裁和他的秘書
【男秘的難以啟齒日常】 【和老闆同處一個辦公室的苦逼日子】 【如何假裝自己對老闆沒意思】 【老闆整天偷窺我,我最近是不是又帥了】 【老闆的兒子不是我生的,我不是,我真沒有】 陳幟禮去面試,面試官問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直男嗎?」 他一臉冷漠答:「是。」 看到男人眼睛就直,算直男。 面試官放心,「那就好,老闆不婚族,想換個男秘,對你沒別的要求就兩點,一是別企圖干擾老闆的感情世界 ,二是老闆顏控,你要控制自己不要長殘,不然影響他心情。」 「好的。」 後來,當初的直男某禮不僅當了老闆的內人,還被搞出個包子來。 攻:總裁,受:男秘 【排雷:有包子,生子文~架空總裁毫無邏輯,沙雕浮誇吐槽風,較真勿入,一切皆為設定服務~】 內容標籤: 生子 戀愛合約 甜文 現代架空 搜索關鍵字:主
37.8萬字8 22958 -
完結239 章

替身受假死之后
許承宴跟了賀家大少爺五年,隨叫隨到,事事遷就。 哪怕賀煬總是冷著臉對自己,許承宴也心甘情願, 想著只要自己在賀煬那裡是最特殊的一個就好了,總有一天自己能融化這座冰山。 直到某一天,賀煬的白月光回國了。 許承宴親眼看到,在自己面前永遠都冷淡的男人,在白月光面前卻是溫柔至極。 也是這時,許承宴才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替身。冰山是會融化的,可融化冰山的那個人,不是自己。 狼狽不堪的許承宴終於醒悟,選擇放手,收拾好行李獨自離開。 而當賀煬回來後,看到空蕩蕩的公寓,就只是笑著和狐朋狗y打賭:不超過五天,許承宴會回來。 第一天,許承宴沒回來。第二天,許承宴還是沒回來。 一直到第五天,許承宴終於回來了。只是賀煬等來的,卻是許承宴冷冰冰的屍體,再也沒辦法挽回。 三年後,賀煬依舊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賀家大少爺。 在一場宴會上,賀煬突然看見了一道熟悉身影。賀煬失了態,瘋了一樣衝上前,來到那個黑髮青年面前。 “宴宴。” 向來都冷淡的賀家大少爺,此時正緊緊抓著青年的手不放,雙眼微紅。 “跟我回去,好嗎?”而耀眼的黑髮青年只是笑著,將男人的手移開。 “抱歉先生,您認錯人了。”渣攻追妻火葬場,1v1。 受假死,沒有失憶。假死後的受一心沉迷事業,無心戀愛,渣攻單方面追妻。
50.5萬字8.18 51834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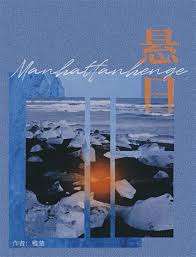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