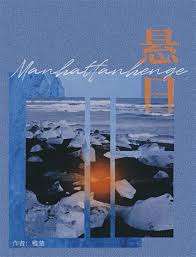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驚悚練習生》 349
他是從惡念中誕生的怪,壞也壞得徹底。
但魔師又是不同的。
對人類來說,這些似乎很重要。
只要不從這個決戰副本出去,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費盡心思想要置對方于死地,更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還是不死不休的宿敵。
惡魔頭一回產生“就算是這樣平淡安逸的日子,但如果對象是魔師的話,一直就這麼下去也不錯”的想法。
很危險,卻不討厭。把對象換魔師的話,一切都是那麼的合理。
他回到了教堂的門口。
兩個城市有時差,公寓那邊還是早上,這邊就已經是下午,天空有些暗淡。
新落下的雪將先前來禱告的行人腳印重新填滿,就像沒有存在過一樣。
等到宗九出來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幕。
穿黑西裝的男人站在雪地里,背景一片全是茫茫大雪,唯有他是格格不的深沉,就像畫布上沾染的那點不同,輕而易舉攫取他人的視線。
“祈禱結束了嗎?”
看到宗九出來,惡魔重新掛上習慣的笑容。
他注意到那束潔白的百合花還留在白發青年的臂彎,并沒有送出去的跡象。
但事實上,比花更吸引他的是抱著花的人。
魔師朝他彎起角,忽然問道:“要和我去一個地方嗎?”
“難得的邀請。”
惡魔挑了挑眉,神辨不出喜怒,“遵命,我的魔師。”
于是宗九帶著他左拐右拐,練地穿行在這座小鎮的彎彎繞繞的巷子里。
或許是今天心的確很好的緣故,他也難得開口解釋。
“這里是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即使十多年過去,這里仍舊如同被定格的老照片那樣,沒有毫的變化。
Advertisement
約莫走了二十幾分鐘,他們來到了一片用黑鐵柵欄圍起來的墓地。
這一片一看就是被專門圍起來的,墓地里矗立著石制的十字架。
來到這里后,宗九就不說話了。
他走上前去,將手里的花放在其中一個墓碑面前。
灰的石頭上書著老修白的名字,和搖曳的花瓣織。
做完這一切后,他轉過去,沒有直視惡魔,有些潦草地抓住那只冰冷的手。
惡魔今天還是那副裝扮,手上戴著白的手套,傲慢地像一位從油畫里走出來的貴族。
然而魔師的手沒有停留,它鉆進了手套里面,與那只滿是疤痕的手相握。
一黑一白沉默地站在那個十字架墓碑前。
很久。
或許是五分鐘,或許是十分鐘,或許更久。沒有人在意。
等到惡魔甚至覺得對方的溫將他燙到之后,宗九才終于開口。
“走吧。”
他說:“我們該回家了。”
從舊教堂回來后,就有什麼東西悄然改變了。
改變似乎是相互的。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兩個人。
可究竟改變了什麼,誰也不敢妄下定論。
魔師很主他,更是從來沒有主求/歡過。
但是今天,這兩樣都被打破了。
回到那間他們共同生活了將近一年的高級公寓后,宗九連外套都沒有,回頭就為另一冰冷的軀獻上一個吻。而惡魔也沒有任何停滯或驚訝,順從了他的魔師的意愿,用舌尖掃過上顎,攫取著對方口中的溫度。
沒有人說話。
惡魔沉默著將自己親手為魔師扎上的發圈解下,任由那一頭銀白長發散落。
他們像兩頭正在博弈的野那樣,狠狠地糾/纏著深吻。
這和第一次的以外,后來的腥戰,甚至是鏡花水月的溫脈脈都不一樣。
Advertisement
激烈,放縱,抓著對方的手腕或勾著脖頸。
比任何一次都要重都要深,男人力道狠厲到像是要把人生生咬碎了融到自己骨里。
夜幕開始降臨。圣誕節夜晚的燈在外面亮起。
一圈一圈的暖黃彩燈纏繞在圣誕樹上,頂端的星星閃閃發亮,每一片冬青樹葉都染上了溫暖又曖昧的澤。
雪越下越大了,從天國落下來的羽像是沒有止境,把視野可見的一切都裹上與魔師長發相近的澤。
“哈哈啊”
青年膛劇烈起伏,一張劇烈痙攣過后,他索著從床頭柜里掏出一包煙。
火苗在充滿水聲的室竄起,在男人的指尖,照亮了那雙充滿暗意的金雙眸。
宗九輕笑一聲,忽然撐起上半,湊到他邊去點燃了這支煙。
煙霧騰起,是冷冽的薄荷味。
魔師的面容在樓下窗外的燈和霧氣里明滅。
白發人一只手夾著煙,慢悠悠地躺了回去,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于挑釁無異。
“再深點。”
簡短的三個字,話音還沒落,他就被影騰空抱起,狠狠地抵到了墻上,足尖不控制地繃。
沒有毫遲疑,惡魔輕而易舉就如了魔師的愿。
月從窗簾外泄,冰冷的劍抓住了這縷,像是要拖著芒沉永無止盡的深淵那樣,自下而上殘忍釘死在墻背上,一下接著一下,如同狂風暴雨,急驟的雨點,永遠沒有止境,像是要就這樣撞到壞掉。
宗九一直在/息,沒有刻意抑。
黑暗中他們都看不到彼此的表,也沒有人說話。
就連最喜歡在這種時候逗弄小魔師的惡魔也反常地沉默,將一切力道集中到了作上。
眾所周知,小魔師不會煙。
Advertisement
但魔師會。并不上癮,卻會借助尼古丁讓自己保持清醒。
早在更早的時候,在宗九從舊教堂里走出來的那個剎那,惡魔看他的第一眼,就清楚這一點。
可現在,他們都心照不宣,沒有人挑明,只有不知疲倦的頂撞。
是的了,只要不挑明,就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沒有什麼無限循環,也沒有什麼非要爭出個你死我活的宿敵,更沒有那些所謂的立場和敵對。僅僅只是魔師和魔鬼而已,僅此而已。
惡魔輕咬著他的肩胛骨,難得溫的作讓人皮疙瘩都起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似乎和往常無二的聲音才在宗九的背后響起。
“寶貝,你今天真熱。”
被按在墻上的魔師哼笑,很快又被卷到斷斷續續的低/里,再也聽不見下文。
數不清這是第幾次攀至巔峰了。
不知道為什麼,惡魔很想看到對方此刻的表。
想親吻他,想和他對視,想和他鼻尖相抵。
想為他帶上戒指,用人類的辦法。明明笨拙又可笑,但諷刺的是,面對魔師,惡魔從來都這麼無可奈何。
想法如同野草那樣瘋長。
然而就在轉的那一刻,男人垂下的手里攥著戒指,僵在了原地。
玫瑰花。
一支含苞放,艷滴,再悉不過的玫瑰花。
決戰副本不可以用任何特殊道,但這卻是由惡魔親手給予魔師的,可以無視一切道使用阻礙的特殊道。
【S級練習生宗九對您使用了B級道:B612星球的玫瑰】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700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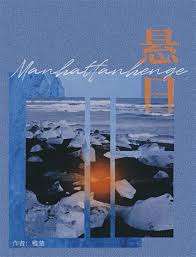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