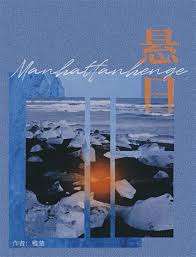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三喜》 83
鎮平侯乃是武人,便是在床笫間,也好直來直往,從不弄虛。今個兒想是吃了酒,也難得懂了些風月:“你里頭抹了什麼,這麼。”沈敬亭聽了耳就一紅,他這個夫君平素正經慣了,就是調,仍是一板一眼,沒想到這樣反倒更是人。他小聲道:“哪有抹什麼,只沐浴時,涂了點香胰……”徐長風那甚是偉,在常人里頭,也該是數一數二的了,再是溫,每次剛進來都有點疼,那香胰不過是潤所用。
徐長風聽了,想是自己魯慣了,弄疼了妻子,今次便比以往更耐心幾分,加上先前有了潤,果真比平日都容易得多。沈敬亭緩緩坐到了底,赤相抱的兩個人都舒服地息一聲,等也等不及,便一起起來。徐長風從他的鎖骨吻下,聲音低啞問:“這樣,疼麼?”
“不疼。”沈敬亭搖了搖頭,又地輕聲說,“人再深些……”
徐長風聞言,雙手托著他的腰,一鼓作氣捅到了深,頭狠狠地在了花芯上。“啊!”沈敬亭便發出個短促的,下腹翹首的玉一晃,頂口就溢出點稀薄的。之后,他就坐在男人上,背朝床外,像是雨打柳,上上下下快意承歡。
氤氳的燭里,兩纏。二人先前還坐著,現在換作男子躺在床上,玉白上的印子深深淺淺,他腰下墊了個枕,下被抬起來,瘦削兩攀住男人壯的腰肢,在那相連之,火龍在玉悍然沖撞,水漉漉的,沉甸甸的囊磨得白玉紅了一片。
那孽退出兩寸,再進十分,回回都頂在要害上頭,沈敬亭兩手在男人背上抓,里迷地喚著:“人……長風,慢些……”說是要慢,卻夾得死,上的男人息愈重,床吱呀搖晃得更加厲害,沈敬亭得更急,舒服得要死去一樣,子一哆嗦,便地丟了。徐長風亦近極,沈敬亭夾了夾,摟著他的脖子,聲道:“在里面……”那水泄在子里,其實并不舒服,可他卻仍想留住什麼,盡管他這子,怕是再不會有……徐長風噙住他的,也堵住了他的胡思想,二人四肢纏抱,直到那種子盡數播在那之地。
Advertisement
事后兩人相摟親吻,沈敬亭緩了緩后,抬起汗津津的臉,他瞧著那右邊臉上的眼罩,不由探出手。徐長風卻將他手腕一扣,拉到邊,吻了一吻。沈敬亭問:“這傷……還疼麼?”
徐長風被奪去的一只眼,這麼多年來,一直是沈敬亭心里最痛的地方。他只怨自己,在這個人最需要他的那時候,他卻不在他的邊。徐長風淡淡一笑,他著自己的妻子,目中溫令人沉醉:“很久以前就已經不疼了。”只要,他的那個年回到他的邊,曾經再痛的傷,也終究會痊愈的。
擁吻之時,那還埋在子里的事又了。兩人分開后,沈敬亭翻了一翻子,男人便從后,這樣的姿勢,能到最深里去。須臾,沈敬亭面泛紅,呼吸微地說:“明日,還有事……”徐長風在后頸唆吻,道,“再一會兒。”說著時,就狠命,沈敬亭閉著眼嗚咽,子如海浪里的孤舟般搖搖晃晃。
徐長風到底食了言,說是一會兒,卻又折騰了半宿,要了一次又一次。一直磨到四更,才喚下人端來水盆。他了,換了服,睡也不睡,就去了校場。沈敬亭一直歇到了已時,方從床上起了,梳洗用膳,一番折騰,到了正午才出去見人。
第74章 番外(四)
有客自遠方來,作為徐家的正君,自然是不能將客人怠慢的,徐瓔珞又有好些年沒回家,沈敬亭早已打定主意,這些天要好好陪他二人游一游京城。不料這才頭一日,他便起晚了,拾掇好了之后,下人方回來道:“爺不必著急,世子和小姐昨個兒喝多了,也才起。”
沈敬亭便命人煮了醒酒湯,好讓二人解解酒,今日也就不出門了,讓他們先好好歇一日再說。到了翌日,沈氏方攜著齊王世子和徐府的大小姐坐著馬車游覽上京。
Advertisement
廂寬敞,能容納五六人之多,車里除了他們還有一個隨侍的婢。車上掛著流蘇遮簾,燒著熏香,一旁的小案還擺著零餞,極是舒適。世子見了,不由心道,這京城的人確實懂得。他看了一圈,目就落在對面坐著的男子上。
今日出游,沈氏著一件天青的深,外罩素紗袍,一頭及肩的青用玉簪盤起,端的是風雅嫻靜。
“鴻兒,鴻兒——”神游之際,徐瓔珞突然拍著他的胳膊道,“那就是我之前同你說過的清河四坊,你看,人多不多?”
李鴻到底也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一聽有熱鬧,便不由拉長脖子湊了過去。
上京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便是條小巷子也熱鬧非凡。云穰雖然富庶,卻也偏遠,全州人口不足京城五分之一,再說這京城里形形的人皆有,世子越發能夠明白,為何父王要讓他千里迢迢護送徐瓔珞京。他只當云穰已是西南第一州,可今生若沒來過京城,就不知這天下還有這等繁華似錦的地方。
馬車緩緩行到京城北巷,停在河川邊上的酒樓前。三人走出來,掌柜早早聽到風聲,出來笑臉相迎:“沈爺、公子、小姐,這兒快請。”他們從另一樓梯走到二樓雅間,和其他座位的客人區隔開來,窗外的景也怡人得很。
“這家酒樓,先前都是你三叔來打理,三爺聽戲,閑時都會到這兒。”沈敬亭解釋道,“過去門閥嚴森,士族和平頭百姓互不往來,這地兒倒不如此講究。”話雖如此,能踏進這家天外樓的,再不濟也是富商之流,能上二樓雅間的,不單錢得夠,份也多非尋常之人。
坐了會兒,就有小二送來名點。這一樣接著一樣,個個巧可,那徐家的沈爺倒也能說會道,拈著塊海棠糕,都能說出些名堂來。徐瓔珞瞧著手掌里那小巧的糕點:“院君知道的可真多,哪像我,就只知道嘗嘗味道。”
Advertisement
沈敬亭笑說:“這些,也全是你三叔告訴我的,我不過是隨口賣弄罷了。”
接著就聽見一樓戲臺傳來好聲,幾人往下瞧去,就見花旦登臺。那是時下正當紅的花臺狀元,人稱“斕仙兒”,曾在萬壽節時宮登臺唱過,聽說他長得和故去的小陳后模樣有七、八分神似,還傳聞他伺候過今上。現在這座位上的,不管是王公貴族也好,多半都是慕名而來聽戲的人。
沈敬亭一貫只挑前頭的好話說,剩下的那些任人自行揣。李鴻端量那唱戲的旦角,唱是唱得不錯,扮相倒不覺如何驚艷,只覺兒氣十足,反是有些不不了。思及此,下意識瞧了瞧前頭。沈敬亭正襟而坐,舉止落落大方,眉眼卻秀致如畫,吐氣如蘭,只見他握著杯子,微微仰首時出纖細頸項,世子本錯開眼去,哪想他如此眼尖,無意間瞥見了那白皙的脖子上,一個突兀的印子。
年雖然不識,卻也明白那印子的由來,霎時間,面攀紅云,竟惶惶不知所措起來。
徐瓔珞回頭見到世子紅了耳,還當他是瞧上了那斕仙兒,嘻嘻笑說:“鴻兒這是開竅了,要給你爹知曉,還不得舅舅打斷你的。”
“你、你莫瞎說,我哪是如此胡來的人!”李鴻說時,不由暗暗瞧向男子。卻見沈敬亭饒有興致地著戲臺,看也不看這頭一眼,不知為何,心里既是慶幸,又覺一淡淡失落。
這一個小小的曲,并沒掃了年人的興致。京城里好玩兒的,說多也不多,說其實也是不。
沈敬亭攜著這對年兩三日里便逛了好幾,花燈初上,徐瓔珞還穿了男裝,去江上游船。這在京中也算多見,源頭是高宗時,有一才扮作男子廣京中才子,著了許多詩句流芳后世,后來京城里便有許多兒效仿。如今世道,對兒家的管束比起前朝,已是寬松了些許,當年的小陳后也是一副書生打扮,邂逅了還是太子的當今圣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4 章
帳中香
千百年后,丝绸古道之上仅余朔风阵阵、驼铃伶仃。 繁华旧事被掩埋在黄沙之下,化作史书上三言两语。 甘露三年,豆蔻年华的华阳公主和亲西域,此后一生先后嫁予两位楼兰君王,为故国筹谋斡旋,终除赵国百年之患,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成为一人抵千军万马的传奇。 *西域主要架空汉,部分架空唐,找不到史料参考的地方私设众多 (雙性,NP)
9.1萬字8 12474 -
完結58 章

離婚
關鍵字:弱受,生子,狗血,惡俗,古早味,一時爽,不換攻,HE。 一個不那麼渣看起來卻很氣人的攻和一個弱弱的嬌妻小美人受 發揚傳統美德,看文先看文案,雷點都在上面。 一時興起寫的,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什麼都不保證。 原文案: 結婚快四年,Alpha收到了小嬌妻連續半個月的離婚協議書。
7.7萬字8 9015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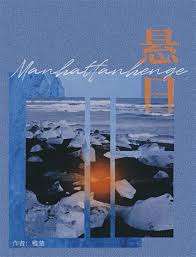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