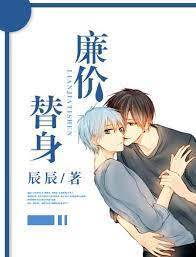《沖喜[重生]》 39
葉云亭快速掃過那些兵,目在書籍上流連。兵書他看過不, 但對比李歧的藏書來說,還是九牛一。
書架上頭的許多兵書,他甚至連名字都未曾聽說過。
“大公子也喜歡看兵書?”李歧見他進門后,目就一直黏在書架之上,便揚眉笑了笑。
“嗯,王爺藏書頗多,許多我都未曾見過。”葉云亭有些赧然,但他平生最大的興趣就是讀書,不拘容,只要是他沒看過的,便都想涉獵一番。
“你喜歡哪些,盡管來拿就是。”李歧意有所指道:“大公子既與我一條心,就不必那麼見外。我這書房不是地,你也來得。”
說完就拍拍側椅子,下點了點:“這些書都放在這里,也不能長跑了,不若大公子先與我說完正事,再去看也不遲。”
他一番話帶著調侃,葉云亭臉頰發熱,只好收回目,在他側坐下。
待坐下后才后知后覺地發現,這乃是主人的座位。
——書房里有一張極大的雕花紅木書桌,上面擺著筆墨紙硯,以及待理的帖子公文等。書桌后置一把同式樣的紅木雕花圈椅,鋪著虎皮毯,是書房主人平日理事務的地方。
但如今葉云亭就坐在這把椅子上。而為主人的李歧,則控著椅,坐在靠墻的里側,與他并排挨著,極近。
意識到這一點后,葉云亭有些不得勁。轉頭想說點什麼,但一側臉,就正對上了李歧湊過來的臉。
——李歧正傾去拿堆在另一側的拜帖,不防他忽然側臉,兩人臉頰對著臉頰,距離不到兩拳。
葉云亭甚至能到他溫熱的氣息。
“……”他下意識往后仰了仰。
Advertisement
李歧恍若未覺,他極自然地長手臂越過葉云亭,拿過拜帖,才后撤,淡聲道:“這些拜帖,都是這兩日各府送來的。”
葉云亭思緒跟不上他,明顯怔然了一下,方才“哦”了一聲,耳有些微微的紅,襯得耳垂上那一小顆紅痣越發鮮艷。
李歧不著痕跡地盯了一下,結滾,收回目鎮定自若地跟他說事:“你先看看認得幾家。”
葉云亭只得接過來,一張張翻看。
這些拜帖疊放在一起,足足有一尺來高。他翻過上頭幾本,發現送拜帖的員職高低不等,有掌實權的一品大員,亦有如壽春伯這等領了虛職的沒落伯爵。他凝眉一張張仔細看過,又發現這些拜帖所用言辭也有十分講究,遣詞用句間能看出不東西。
他將認識的員的拜帖挑出來,單獨放在一邊,其余只約聽過姓名的,則另做一堆。
李歧分別看過,神有些意外:“我以為大公子極出府,認識的員當不多。”
以葉云亭屈指可數的面次數,李歧以為他對朝堂之事應該知之甚才對。然而葉云亭挑出來的這一堆拜帖里,大部分掌了實權有名有姓的員,他竟然都識得。
“我年時有一位先生,他自請離府后四云游,偶爾會給我寫信。信上常會提及如今朝堂形勢,我耳濡目染知道一些。不過也只知其名,不知其面。”
先生常裕安,便是那位給葉云亭啟蒙的恩師。先生邊帶著個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弟子,偶爾會回京打理鋪子,順道便會將先生寫給他的信送過來。
是以葉云亭這些年雖然困于府中,消息卻并不算閉塞。
“那便簡單了。”李歧滿意頷首,在兩堆拜帖里挑挑揀揀,有用的放在面前,沒用的則扔在一邊:“近日我有意設宴宴請同僚。”
Advertisement
“要請哪些人?以什麼名目?”葉云亭問。
“這便是我要與大公子商議之事了。”李歧忽然笑起來,眼微瞇,笑容葉云亭覺得有些不懷好意。
葉云亭心里一突,就聽他接著說道:“我有意將宴席辦得隆重些,最好能將朝臣都請來,但思來想去,卻覺得沒有合適的名目。不過最后倒是終于我想到一個名目,十分合適……”
“?”葉云亭心里越發不安生,卻還是忍不住道:“什麼名目。”
李歧聽他提問,笑容愈盛,慢吞吞道:“大公子府時,我正病重。婚事辦得冷冷清清,連賓客都未到。如今想來十分憾,便有意補辦一場宴席……”他頓了頓,道:“倒也不必都按照婚事章程來辦,一婚二辦,總是不吉利。只將一眾同僚請來喝酒吃宴熱鬧一番即可。”
他眼底芒流轉:“一則,是可借機李蹤做下一步作,二則是……”他說到這里便頓住了,沒有再往下說。
這個理由倒是十分正當,葉云亭略思索了一番,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自朝會鋒之后,皇帝就沒了靜。
監視王府的神策軍早就被撤了回去,如今王府的守衛都是朱烈帶來的玄甲軍親衛。府中下人倒都是宮里的眼線,但他們本靠近不了要之,搜集到的消息都是李歧想讓他們傳到宮里去的。
李歧并不怕李蹤知道他的一舉一,相反的,他就是要將自己的一舉一都傳到李蹤的耳朵里。
李蹤知道的越多,心里就會越不安。
打蛇不死,必遭反噬。如今李蹤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形。
李歧沒死,玄甲軍未除,而兩人之間卻早已勢同水火。李歧就是懸在李蹤頭上的一把刀,卻遲遲未曾落下。
Advertisement
拖得越久,李蹤只會越慌。
一旦他了陣腳,就容易出錯。
李歧從前雖然勢大,卻從不屑于拉幫結派,極私下與朝臣往來結。如今聲勢浩大地宴請朝臣,傳到李蹤耳朵里,必定是李岐另有所圖。這是在迫他手。
他做得越多,錯越多,都是送上門的把柄。
“那二則呢?”葉云亭想明白,才想起來他話只說了一半。
李歧懶散靠著椅背,手指有規律地敲打著桌案,慢吞吞把未盡的話說完:“二則是給大公子正正名,也免得外頭的人不知道我這永安王府里多了個新主子。”
以為能聽到一番高見的葉云亭:“……”
他默了默,笑得干:“王爺說笑了。”
李歧卻不依不饒:“大公子覺得我在說笑?”他一臉義正言辭:“我與大公子畢竟是陛下賜婚的夫夫,前些日子形勢所礙,連累大公子跟著我遭了不白眼,如今既離困境,該有的名分自然要有,否則都如齊國公那般對大公子呼來喝去,我如何心平氣和?”
他說著收斂了笑意:“大公子知道的,我一向脾氣不好。若今日的人不是你生父,可沒機會走出王府大門。”
葉云亭:“……”
他盯著一臉肅然的男人,心想連皇帝本尊都不放在心上的人,還能把賜婚當真不?
別又是想借機捉弄他。
但轉而又想起今日當著葉知禮夫妻的面,他如此回護自己,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永安王重重諾,今日是真心護著他。
葉云亭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他抿了抿,一舉二得之事,他也沒有理由拒絕,便領了這份:“那便依王爺所言。”
“那我便五更與朱烈安排下去了。”李歧目的達,微不可查地勾了勾,又轉回了先前的話題:“宴席當日必定忙,我先將幾個重要的員再同你說一遍,到時候我忙不過來,還勞煩大公子幫忙招待。”
葉云亭點頭,傾去看他手中拜帖,神認真。
李歧看他一眼,也朝他那邊傾了一些,與他挨得極近,才不不慢地給他講起這些員之間的陣營黨派來。
朝臣之間利益糾葛錯雜,各自之間有千萬縷的關系。李歧耐心同他一個個講解,待全部說完時,已經過去了一個時辰。
葉云亭看了看時,微微詫異:“竟然過了午膳時候,我下人擺膳吧?”
李歧眉頭微皺,遲疑著道:“過了時辰,不太有胃口。”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