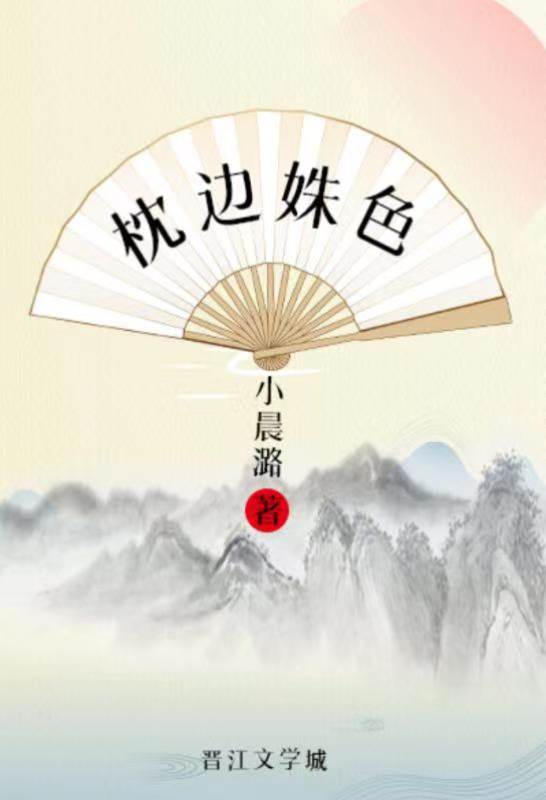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第二十六章
“諾。”離秋應道。
這樣,當得夜值的近宮人,今晚,就唯有蘅月一人。
可,心下,不知為何,總覺得是忐忑不安的。
這份不安,隨著更聲響去,愈來愈濃
鸞宮。
縱李公公申時就傳來了口諭過來,說皇上不會來用膳,陳錦依舊準備了從天巽宮司膳太監口中探聽得知的軒轅聿喜歡的菜式。
只是,看著菜式即便用暖兜溫著,都逐漸冷下去,眼底先前的華亦一并暗去。
就坐在桌旁,上著的,是最珍貴的金蟬,輕若羽翼,又薄得襯得玉骨若現。
這樣的,難道不嗎?
起,在落地的金銅鏡前,再次端詳了一下姿。
纖腰一握,輕盈得仿似不風吹般地。
司徒的教誨猶在耳,軒轅聿素喜的,都是纖瘦的子,眼見著夕因六個月孕,再不復嬛腰楚楚,六宮中,能媲得上陳錦貌,也不過是那早失寵的新藺姝罷了。
失寵的,在想得寵,很難。
呢?
沒有得過君心,意味著,終能有轉折。
縱然,他曾讓跪在天巽宮正殿外時,不帶任何憐惜,知道太后赦免,方能帶著膝上的傷痛狼狽的回宮。
可,又能怎樣呢?
是皇后,每個月,不用他翻牌,月半這一日,唯有,才能伴于他邊。
祖制如此,他不得不遵。
這,就夠了。
只要每月這一次的機會,不相信,自己邀不來他的心。
因為,這大半月,他雖不曾翻牌,獨陪在醉妃旁,可,畢竟,醉妃現在子愈重,本不能承恩。
哪怕,醉妃在他心里有著些許位置,但,更相信,君恩涼薄。
即便涼薄,確是不得不去爭,不得不去要的。
Advertisement
因為,想,或許,在權勢之外,如果,能上給這份權利的那人,也是好的罷。
而,相信,也唯有,是最配他的那一人的。
無論心智,或者其它,,最配他。
斂回心神,聽到,遠遠地,有輦行來的聲音,接著,是太監尖利的聲音,一路疊聲地傳進來。
婷婷會意地取來羅裳替披于蟬外面,一切整理停當,聞到,空氣里,龍*香氣愈濃。
“臣妾參見皇上,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跪叩于地,這一跪,膝蓋是疼痛的。
這宮里,當得起下跪的,僅有兩人,然,這四日間,這倆人都并未傳召過,是以,沒有跪過,再次下跪,原來,膝上的傷仍是在的。
他賜給的傷。
記得。
會要他用寵來償還這份傷。
軒轅聿不發一言,徑直走到椅上坐下,語聲方悠悠傳來:
“平。”
“臣妾謝主隆恩。”
的語音仍是恭謹的。
今晚,不能讓他有毫的不悅。
“皇上,臣妾為您準備了幾樣小點,您可要用了再安置呢?”
說是說幾樣小點,卻都是心準備的。
“哦,皇后有心了。”
一語落,他看上去,邊對含著笑,但眸底,又蘊了千年寒潭般的冰魄。
一如,那晚,他曾用最溫的聲音,說出最無的話一般。
對,是看不徹的,然,正是這份不徹,讓對他有了愈濃的興致。
哪怕,挫折再多,只要興致不減,始終愿意奉陪。
“皇上,這是牛茯苓霜,每晚一蠱,最是滋補的。”
陳錦纖細的玉手從宮的托盤中,端過一水晶蠱放置的甜點,帶著,略低螓首,呈于軒轅聿。
Advertisement
羅袖因著這一呈,向后褪去,顯出里面,金蟬的輝華來,恰映著若霜。
軒轅聿并不接那蠱甜點,佯做怯意,稍抬了目,恰看到他似端詳著出的半截玉腕。
的心里溢出一甜來,看來,連日不曾翻牌的皇上,果真,比以往更容易吸引。
他的手,越過那蠱甜點,輕輕覆到的手腕,如所料一般。
地再次地下臉,靜等著下一刻的砰然心。
下一刻,確是讓怦然心的。
但,這份怦然心,不過是其它的意味。
只這一覆,他收回手,語音冷冷:
“看來,皇后宮中的甜點,甚是養人,才四日不見,皇后倒真是愈見了。”
錯愕地抬起臉,,了?
“都是朕的不是,讓皇后在那殿外,傷及,不得回宮,自是要多滋補一番的。”
這句話,聽著,似帶著關心的味道,實則,卻是截然不是。
“皇上,臣妾——”
方要說些什麼,卻被他冷聲打斷:
“朕素覺得,子一纖瘦娉婷為,皇后今日這樣,倒把先前的仙姿抹去了不,真是朕的不是。”
“臣妾惶恐,請皇上容臣妾幾日,臣妾定不會再如此。”
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難道,真的是這幾日,用了母親特意托人送進宮的補膏,滋補得了嗎?
但,他稱以前的為仙姿,又讓心底起了欣喜之意。
也就是說,是講過他的眼的。
既然,他嫌,那盡快瘦回去便是。
“皇上,這甜點,是臣妾心為皇上準備的,還請皇上用。”
繼續奉上那蠱甜點,這一奉,眼底卻蘊了更多的笑意。
“朕乏了,撤了吧。”
Advertisement
“諾。”忙把甜點復遞還給宮,輕聲,“皇上,既然您乏了,不如,不如——早些安置,可好?”
猶記起,他予迄今為止,唯一一次的臨幸,縱是帶著讓不愿去憶及的點滴,卻,在今日,再再讓帶了子特有的。
“時辰還早,朕并不困。”
“那——那由臣妾為皇上紓解疲勞,可好?”
“甚好。”軒轅聿睨著,薄勾起一道笑弧。
至他的后,將以往宮人替按的手法悉數用到他的上,可,無論怎麼按,一會,他說重了,一會,又說輕了,好不容易調節到他要的輕重,一會,他又說肩疼,一會,又說手臂疼。
于是,這一折騰,就是兩個時辰。
直按到手腕發酸,最初,及他子的悸,漸漸,讓覺到是種煎熬。
可,他不讓停,卻是不能停的。
殿,攏的銀碳溫融,讓的額際都沁出些許的汗意來,手下的力終是再使不出多的來。
“停了吧。”
恰此時,他的聲音悠悠傳來,讓如釋重負地停下手。
他稍側臉,睨了一眼,道:
“怪不得,朕聞到一怪味,原來,是皇后的汗漬。”
瞧得清楚,他瞧向的目隨著這一句話落下時,帶了幾分的不悅。
汗味?
下意識地用帕了一下臉,這一,他睨向的目,驟然轉得更冷:
“皇后看來平素上的胭脂真是不啊。”
“啊?”這一次,終是詫異地驚喚出了聲。
下意識地瞧了一眼,帕上只沾了許的胭脂痕跡。
未帶細想,他語音卻是慢條斯理地響起:
“朕素來喜的,就是清水芙蓉之姿。可惜了——”
他未將這句話說完,只把目從臉上移往更,復道:
Advertisement
“皇后今晚也累了,早些歇下吧。”
“皇上今晚也累了,早些歇下吧。”
“不必了。”他的聲音里,再無一溫,驀地起很,喚道,“起駕回宮。”
此時的更,恰指向亥時。
反正,之于祖訓,他今晚,確是來過,又確實待了足足兩個時辰,即便不留宿,卻是他做為帝王的權利,不是嗎?
他的影消失在殿外時,陳錦的終是被氣得哆嗦了起來。
說什麼嫌,又讓伺候著按,接著,嫌并非清水芙蓉之姿。
分明,就是戲弄!
這兩個時辰,在這宮人面前,他就這樣戲弄凌辱?
陳錦的手狠狠的鉗進指腹中,犀利的目閃到一旁伺候宮上,語音森冷:
“今晚發生的一切,誰若給本宮說了出去,就去奚宮局報道。”
“諾。”
一種宮忙紛紛下跪,語音戰兢。
天巽宮,偏殿。
蘅月亥時進得殿來,替下燕兒、恬。
“娘娘,可要安置了?”蘅月按著規矩請示道。
“本宮尚無倦意。”
“那,是否傳小安子來,為您演一場皮影戲,解解悶?”
小安子?
是記得宮里有個使太監喚做小安子,只是,這使太監,一般是不得進殿伺候的。
畢竟這里是天巽宮的偏殿,要讓一名使太監進殿,自是要有其他的說法,蘅月提了皮影戲,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說辭。
“也好。”允道。
不過半盞茶功夫,兩名小太監抬著皮影戲的道進得偏殿,將那經過魚油打磨后,變得括亮的白沙布戲抬搭方帷在的榻前,接著,四周的燭火悉數暗去,只余了白沙布后的燭火猶自亮在那。
看到,白紗布后,現出一長玉立的影,但,旋即,就是一小小的剪紙人兒躍然在紗布后,那影,終是再瞧不到。
“本宮看戲,喜靜。都退下罷,蘅月,你伺候著就行了。”啟,吩咐道。
“諾。”
殿,隨著宮人的退出,恢復寂靜。
靜到,更聲,清晰分明地得耳來。
“娘娘,您要看什麼戲?”
銀啻蒼的聲音從紗布后傳來,依舊如同往昔一樣。
聽著悉,再細品,終是陌生。
“你給本宮準備的又是什麼戲?”
這一語里,帶著幾分難以抑制的緒外。
“為娘娘祈禱玉安康的戲。”
“玉安康?只不知,看這場戲,所要的代價,又是幾多呢?”咄咄。
白紗布后,再無一聲響,亮堂的燈后,是一子形的剪紙人兒出現。
縱僅是一個剪紙,卻與,是神似的。
仿同就是在白紗的彼側,只是,演的卻是一幕人間死別的悲傷。
子懷有孕,然,在誕下孩子,便是,香消玉損。
孩子,兀自在那啼哭,但,他的母親,卻不會在了。
這,就是結局。
他借著皮影戲,告訴的結局。
若一意要懷這個孩子,結果,只是死,孩子生。
反之,他的藥丸,果真是對孩子不利的。
手扶著床榻旁的帳欄,起,下榻。
走得很慢,很慢。
蘅月,并沒有阻住的步子。
扶著腰,緩緩地,走到白紗布旁,看到,里面的亮,依舊。
只是,誰的心,驟然變得漆黑一片呢?
白紗布圍的方帷,本蹲于地上的那人,終是站起,凝向,縱,他的臉,是平淡無奇的小安子的模樣,然,除了,那鷹形的面外,他冰灰的眸子,是不會被掩去的。
這,亦使得,今晚,他宮見,是怎樣的危險。
其實,他為了,又何止一次陷危險中呢?
可,今晚,并不是去品懷這些的時候。
“遠汐侯,你,又騙了本宮。”
用了一個‘又’字,話語里,帶著冰霜般的嚴寒。
“是,臣騙了娘娘,為了娘娘的玉,任何代價,都是值得讓臣去騙的。”
“本宮真是愚不可及,被你騙了一次又一次,竟還會相信你。”
用極平靜的語氣說出這句話,每一字里,卻分明滲出讓人心寒的利刃鋒芒。
說出這句話,他的目進他眸底的深。
“如果能這麼騙下去,讓娘娘信以為真,臣愿意騙下去。”
能當真嗎?
是,是當了真。
以為,那藥,真的能保一年無恙,換來孩子生。
“如果這麼騙下去,能讓娘娘,玉安康,臣愿意騙下去。”
為了孩子,早就不要自己的子了。
這點,他看穿的同時,原來,只是順著的意思,選擇欺騙。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5 章

登堂入室
元執第一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謀奪家業; 元執第二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栽贓陷害別人; 元執第三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那個乳兄終於不在她身邊了,可她卻在朝他的好兄弟拋媚眼…… 士可忍,他不能忍。元執決定……以身飼虎,收了宋積雲這妖女!
72.5萬字8.18 8869 -
完結1000 章

逆天神醫妃:鬼王,纏上癮
“王爺,不好了,王妃把整個皇宮的寶貝都給偷了。”“哦!肯定不夠,再塞一些放皇宮寶庫讓九兒偷!”“王爺,第一藥門的靈藥全部都被王妃拔光了。”“王妃缺靈藥,那還不趕緊醫聖宗的靈藥也送過去!”“王爺,那個,王妃偷了一副美男圖!”“偷美男圖做什麼?本王親自畫九十九副自畫像給九兒送去……”“王爺,不隻是這樣,那美男圖的美男從畫中走出來了,是活過來……王妃正在房間裡跟他談人生……”墨一隻感覺一陣風吹過,他們家王爺已經消失了,容淵狠狠地把人給抱住:“要看美男直接告訴本王就是,來,本王一件衣服都不穿的讓九兒看個夠。”“唔……容妖孽……你放開我……”“九兒不滿意?既然光是看還不夠的話,那麼我們生個小九兒吧!”
176.8萬字8.18 149187 -
完結972 章

一胎三寶:神醫娘親腹黑爹
四年前,被渣男賤女聯手陷害,忠義伯府滿門被戮,她狼狽脫身,逃亡路上卻發現自己身懷三胎。四年後,天才醫女高調歸來,攪動京都風起雲湧!一手醫術出神入化,復仇謀權兩不誤。誰想到,三個小糰子卻悄悄相認:「娘親……爹爹乖的很,你就給他一個機會嘛!」讓天下都聞風喪膽的高冷王爺跟著點頭:「娘子,開門吶。」
175萬字8 25431 -
完結1546 章

醫女天下:冷麵王爺欠調教
被嫡姐設計,錯上神秘男子床榻,聲名狼藉。五年後,她浴血歸來,不談情愛,隻為複仇,卻被權傾天下的冷麵攝政王盯上。“王爺,妾身不是第一次了,身子早就不幹淨了,連孩子都有了,您現在退婚還來得及。”垂眸假寐的男子,豁然睜開雙目,精光迸射:“娶一送一,爺賺了。”
268.2萬字8 2587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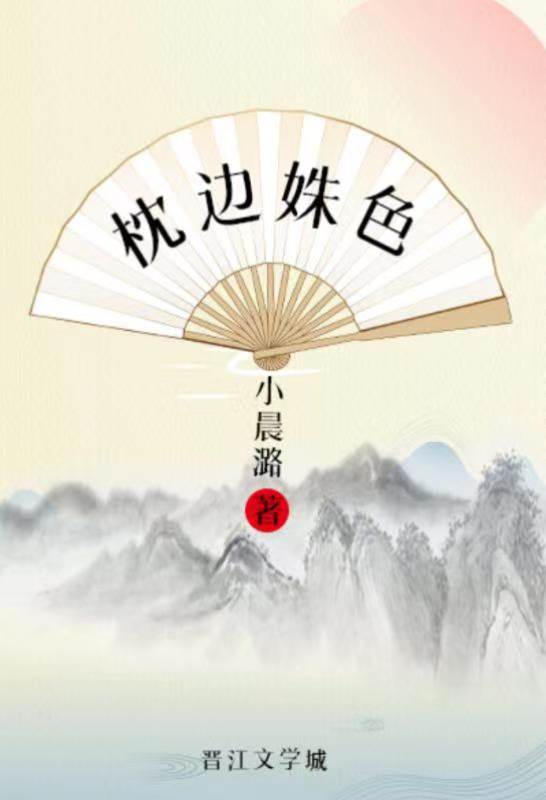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