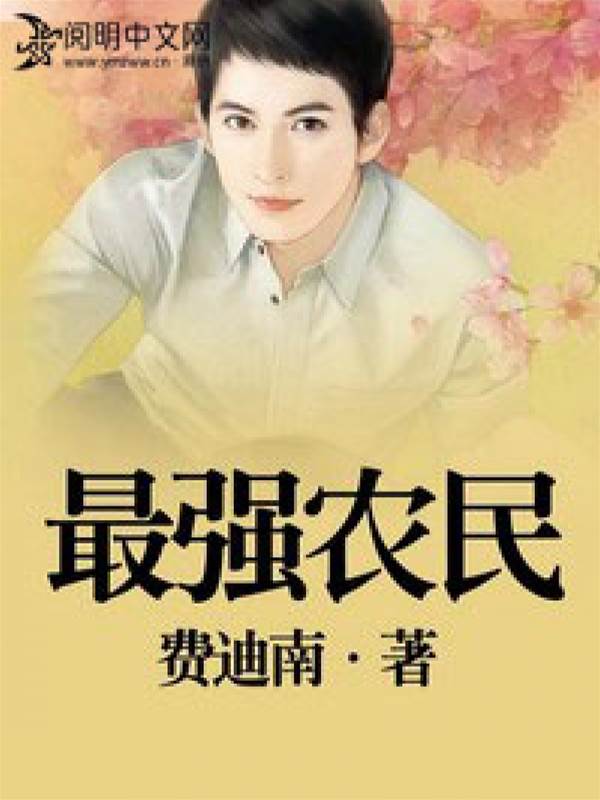《駕校情緣》 第五十四章
“久等了吧?這麼熱,真是辛苦你了!”老趙把車開過去停好,看著孫瀟瀟優雅地走進車旁,“”地問候道。
“不辛苦不辛苦!”孫瀟瀟吃了苦頭,這才發現老趙的好:“教練您天天接送我們才辛苦呢!”
隨著孫瀟瀟彎下腰進來,碩大的山峰著副駕駛前的臺面而過,才q彈地隨著的坐定而安放。老趙眼尖地發現:這個小妞,居然又沒穿?呀!差點忘了!的還在自己車裡放著呢!
老趙這麼一瞟,眼裡的也不由得熱烈起來,看的孫瀟瀟紅了臉:這個老趙,每次都用這種綠瑩瑩的眼看著我,像狼一樣,讓人怪不自在的!可是,他的目跟今天公車上的男人都不一樣,讓人覺得好好害,好啊……
“久等了吧?”老趙繼續之前的話題,打了兩人之間的平靜。
“沒有呢!您來的很快!”孫瀟瀟也是奇怪,自己下車沒多久,就看到老趙了:“您不會在這裡等我吧?”
Advertisement
“沒有!我也是剛到!送完那個學員就來了!”老趙生怕孫瀟瀟懷疑,趕解釋道:“他說他想排隊排在第一個考完,這不,把他送到,我就放心地來接你了!”反正到時候你也不可能去關心第一個考試的是誰!
“謝謝您,教練!”孫瀟瀟果然極了:“我這麼笨,讓您費心了!”
“沒事!誰讓我是你教練呢!”老趙笑呵呵地打著方向盤:“你不要誤會我就好了!其實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啊!”
“嗯!”孫瀟瀟垂著眼眸,心想這個趙教練,真是不老實!他和那個香香姐,我可不是第一次看到了!為什麼還要對我撒謊呢?難道就像趙欣那個的,他喜歡我?不會吧……好像真是有點哎,這個老頭子,真不害臊!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
“你的科目二現在有把握了吧?“老趙見到孫瀟瀟那風雲變幻的臉,猜著這小姑娘正不知怎麼想自己呢,幹脆地拋出了話題。
Advertisement
“啊?”一說到科目二,孫瀟瀟的臉垮了下來,今天練車就練了那麼一把就生氣走人了,這會兒哪裡有把握啊!一說到這個,孫瀟瀟就沒有了底氣:“還……行吧……不是很有把握。”
“科目二可不是考著玩的。現在還沒把握,你還不如馬上回家呢!你可要自信一點呀!”老趙好整以暇地等著孫瀟瀟上鉤。
“可是……”孫瀟瀟皺起好看的眉頭:“可是我每次只要到了考場,就忍不住雙打,總是會熄火,或者對不準!”
“是啊!駕考就是考心裡狀態!心理過關最重要呢!”老趙故作為難:“要不要抓時間,我給你再放松一下?”
“再放松?”孫瀟瀟想起剛剛上午的按放松,不由得面紅耳赤:“這……不大方便吧?”
是說的不大方便,不是不好!哈哈!老趙聽了,高興得一蹦三尺高!這回,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金箍棒!人都是小道通心,把下面那條小道打通了,心也就離你不遠了,老趙是發現了,自己之所以沒有搞定瀟瀟,就是沒有打通這條小道,嘿嘿,這回,老子非要趁機會把你打通了才好!
Advertisement
一想到這裡,老趙忍不住興起來,一邊開車,一邊抖著,心裡唱起了歌:“沒事兒!駕考中心外面有塊大停車場,今天不是周末,考試的人,我們把車停到偏僻一點的地方,還是很方便的!”
“這……看看吧!”孫瀟瀟總算是沒有反對:按好像確實有點效果哎……不管了,反正這次按以後我一定要把我的拿回來。
因為孫瀟瀟的妥協,老趙覺得渾充滿了力量,他把油門一踩,車子駛環城高速,飛快的沖著駕考中心開去。嚇得孫瀟瀟一陣尖:“啊!教練!您慢……慢點兒!”
麻蛋!這聲音真銷魂!孫瀟瀟的讓老趙腳都了,要不是路上行人太多,他真想把拉下來就地正法。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