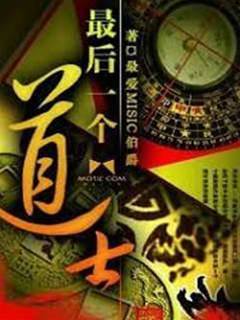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民調局異聞錄》 第四十六章 鬼戲
我看出來了,這個戲班老板也不簡單,最起碼以前是唱過鬼戲的,看他談笑風生的,完全不把這個當回事兒。看著三叔要跟他出去,我看了一眼孫胖子說:“我也去,孫廳,你?”孫胖子打了個哈哈說:“你都去了,我還好意思接著喝酒?一起吧。”
爺爺年紀大了,沒有跟著,倒是蕭老道跟著戲班班主,兩人一路上有說有笑的,我們三個跟在他們的后面。到了戲班老板的臨時住,戲班班主進去拿點東西,要我們四人等一下。
“老蕭,唱一晚上的鬼戲,只要雙倍的戲酬,他倒是不貪啊。”我掏出香煙,一人發了一,邊邊聊著。
蕭老道別看是老道,卻是什麼都不忌諱,兩口將香煙了一個煙屁,說:“不貪?屁!他說的是這十天的戲酬都翻上一番,剩下的錢都歸他了。小辣子,你可別小瞧這幫人,這里面水可深了。”說著將煙彈在戲班老板的門上。
唱戲的水有多深,我沒有興趣。不過這筆錢到底誰出,我倒是想打聽明白。“三叔,這錢縣里不能出吧。”三叔也完最后一口煙,將煙頭扔在地上,用腳踩滅,說:“你爺爺和村長說好了,村里出一半,族里的公費出一半。”
他話剛說完,戲班老板手拎著大大小小幾個袋子,走出房門,我接過幾樣,有燒紙、香和素蠟燭,還有一個袋子,戲班老板親自抱著,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拿齊了需要的品,我們幾個人一路走到了河邊。先上了那艘戲船,在戲船的四周燒了香、紙。戲班老板邊燒邊里念念有詞,他說話的聲音太小,我聽不到他說的什麼,想要靠近去聽聽時,卻被蕭老道拉到了一邊,“別過去,他在祭鬼神,你聽見了不好。”
Advertisement
我看了一眼還在像念經一樣嘮嘮叨叨的戲班班主,回頭對著蕭老道說道:“他一個戲班老板,怎麼連這個都懂?”蕭老道說道:“你太小看唱戲的了,他們走南闖北的,什麼戲沒唱過?以前還有一些地方有風俗,家里死了人,要請戲班子到家里唱戲,和鬼戲比,也就是法不一樣而已。”
沒用多久,戲班老板的香和紙都燒完了,他打開了剛才還死死抱著的袋子。我們幾個都靠了過去,我看得清楚。戲班老板拿在手里的好像是曬干的玉米葉子,當著我們的面,他在每片玉米葉子上都寫了字,我數了數,他一共寫了九張。有鍘案、四郎探母、鎖五龍等等。
是戲牌,班主寫完之后,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走到了船邊,大聲喊道:“今有大戲班伶人二十三名在此,于明日晚為世諸公獻上大戲一場。大戲班有軸大戲九出,請世諸公賞下戲牌。”
班主說完之后,將手里的玉米葉子一片一片地放在水面上。回頭對我們幾個說:“你們過來幫個忙,拿手電照著,看看哪片葉子沉下去,就記上面的名字。”
剛開始的時候,幾片葉子在水里都沒有什麼變化,但過了十秒鐘左右,其中一片葉子忽然毫無征兆地沉到了河底,我看得清楚,是四郎探母。接著,第二片、第三片葉子也相繼沉到了河底。孫胖子在旁邊說道:“鬧天宮、烏盆記。”
班主也不管水面上剩余的玉米葉子了,說:“好了,戲挑完了,我的活兒先到了。大師傅(蕭老道),明天千萬記得,天只要一黑,這條河上下方圓五里地都不準有人隨意進出,沖了戲是小,別再把我們連累了。”
Advertisement
“不能。”蕭老道頭搖得我看著都暈,“明天你就放心,民兵會把周圍五里之都封了。絕對不會有人過來攪局。”
“那就行。”班主頓了一下,又接著說道:“還有件事,唱夜戲的規矩,只要是唱夜戲,主家要派人在戲班里守著,放心,沒事,這個就是個規矩。有主家人坐鎮,我們唱戲的就能圖個心安。”
蕭老道看了我和三叔一眼說:“你們倆都是姓沈的,誰來?”
三叔沒有毫猶豫,馬上說道:“我來吧。”
“三叔,算了吧。”我說道,“還是我來,是吧,孫廳?”
忙了一宿,再回到爺爺家時,天已經漸亮。我們幾個各自回房休息。三叔去了爺爺的屋子里,把房間讓給了我和孫胖子。
我躺在炕頭上,正在醞釀睡意時,就聽旁邊的孫胖子說道:“辣子,你老家這兒的事兒也算是邪了,唱大戲都能把鬼招來。對了,你沒事就泡檔案室,見過類似的事兒嗎?”
孫胖子的話提醒了我,檔案室的文件實在太多,我接到的還沒有百分之一。還沒看到有關鬼戲之類的事件。不過照規矩,這件事也應該向局里匯報了。
我打算和孫胖子商量一下,就說:“大圣,鬼戲的事是不是得向局里報告了?”孫胖子沒有回答,我還以為他睡著了,回頭看他時。這貨正瞪著眼睛看著我。
“嚇我一跳,不放聲,還以為你睡了。”
“辣子,你長當夠了?”孫胖子這才慢悠悠地說道,“不是我說,你剛給你爺爺長了一天的臉,就這麼算了?等二室的那些貨們來了,你的西洋鏡就算拆穿了。誰見過一個廳長加上一個長圍著一群小科員轉悠的?不是我說,你真能指二室的那幫人會替你瞞?”
Advertisement
我明白他的意思,不過還是問了一句,想確認一下他的答案,“你的意思呢?”
孫胖子一骨碌從炕上坐了起來,說:“辣子,咱倆不是剛進民調局,一有風吹草就撒丫子那會兒了。麒麟市的十五層大樓都能闖進去,鬧戲的冤鬼再兇,還能兇得過十五層大樓滿樓的冤鬼?”
孫胖子咽了口口水,繼續說道:“辣子,咱倆帶了家伙過來,八就是老天爺的意思了,就算真有惡鬼,只要它敢頭,對付它也就是勾勾二拇指的事兒。”
我被孫胖子說了,又聊了一會兒后,不知不覺迷迷糊糊睡著了。等睡醒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多鐘了。簡單吃了一點東西后,三叔帶著縣里的警察局局長進來了。
警察局局長姓趙,他帶著人馬一大清早就到了,技人員將昨晚淹死的那個倒霉鬼帶回了縣城進行尸檢。得知兩位領導昨晚尋找破案線索一直到后半夜,現在還沒有起來,趙局長就一直在屋外等著,爺爺幾次想把我們醒,都被趙局長攔下了。
和這樣的人打道,完全就是孫胖子的強項。他哼哈了幾聲,隨隨便便應付著局長。爺爺在后一個勁兒地使眼,我意領神會,說道:“趙局長,我和孫廳長的意思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謠言,這個船河大戲今天先停一天。
趙局長還沒等表態,屋外甘大葉甘縣長已經推門進來。他聽說船戲要停演一天,馬上就表示了強烈反對。對著自己老家的縣長,我這個假長還是沒有什麼底氣。可孫胖子不管那一套,他眼皮一翻說道:“現在已經死了三個人了,湊夠五個就算是群事件了。到時候,為求經濟利益,罔顧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黑鍋是趙局長你背呢,還是你甘縣長來背呢?”
Advertisement
這個帽子實在扣得太大,趙、甘二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不敢接孫胖子的話茬兒,場面一時有些尷尬。
最后還是趙局長撐不住了,他看著孫胖子想說點什麼,不料孫胖子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趙局長張開的又重新閉上,他的結上下幾下,連同他要說的話一起咽了回去。
“算了,那就停一天吧。”無可奈何之下,甘縣長也只能妥協了。
將他們二人打發走之后,三叔將我單獨到爺爺的臥室里。他從炕柜里取出一個小木匣子給我,說:“這東西你小時候見過,晚上帶著壯壯膽兒。記住了,千萬別逞強,你有天眼,覺得不對馬上就跑。保命要,不丟人。”
打開木匣,里面裝著的正是當年三叔把糾纏我的水鬼趕走時拿出的那把短劍。時隔多年,三叔還給短劍配了個劍鞘。以前我想看看他都不讓,現在竟然直接把短劍給了我。
我將短劍別在腰后,抬起頭對著三叔說道:“爹,沒事兒,你就別心了。不就是陪著唱出戲嘛。再說了,怎麼說你兒子我也穿著警服,有氣護,百邪不侵。”以前聽三叔說起過這把劍的來歷,我惦記不是一天兩天了。現在看來九是吳仁荻留下來的。看來今天算是撿到寶了。
“早跟你說明白了,我是你三叔,以后別兒子、爹的瞎了。”三叔嘆了口氣,可能是怕我看見他的眼睛已經紅了,三叔一轉出了屋子。
我跟在三叔的后面,剛出了爺爺的臥室,就看見蕭老道把那戲班子的人都帶了過來。這邊已經開始有人在擺桌子了。院子里臨時起的灶臺也點著了火,煎炒烹炸已經忙開了。
我走到爺爺邊說道:“不是說后半夜唱完了回來再上酒席嗎?怎麼現在就擺上了?”爺爺說道:“聽你蕭爺爺說的,唱完鬼戲不能耽誤,回來卸了妝馬上就要睡覺,這是規矩。”說完走到灶臺那兒又開始忙起來。
我找了一圈的孫胖子,最后在已經落座的戲伶堆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給一個花旦看手相,“小妹妹,看你的手相克夫啊,不過也不是不能化解,你找一個……”沒等孫胖子說完,我已經將他拖了起來,說:“找誰也不能找你,你克妻!”
孫胖子撇了撇說:“難得這麼一個機會,可惜了。”
那邊蕭老道溜溜達達走了過來,“小辣子,還有個岔頭和你說一下,昨晚上(實際是今天凌晨)忘了告訴你了,戲班子在船上唱夜戲只能上九個人,今晚上三出戲你和孫同志要串幾個龍套,別那麼看我,我也得上,到時候跟在我后面就行了。”
沒辦法了,已經到這一步了,龍套也就龍套了。
吃飽喝足之后,縣里出了兩輛面包車,將蕭老道和戲班老板還有我們十來個人送到了河邊。爺爺和三叔不能跟著來,我只能問蕭老道:“老蕭,不是說要把戲船周圍五里地封了嗎?”
蕭老道嘿嘿笑了一陣,說:“都整好了,五里地之,誰都進不來。”
我點了點頭問“現在還有民兵嗎?”蕭老道搖了搖頭說:“不是民兵,他們不好用,都是人,不好意思管。是熊跋帶人把路封了。”
我真是有點出乎意料了,驚訝地問“這封建迷信的事兒熊所長也管?你們還能指使他?”
“我們指使不他,就說是你讓他干的。”蕭老道一臉無賴地說道。
這出鬼戲就可以正式開始開鑼了,沒想到直到七點多天完全黑下來之后,這些戲伶還是沒有開戲的意思。
在天黑之前,我們一行人到了戲船上,按規矩坐到了船艙里。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這些人就逐漸忙碌起來,扮行頭的扮行頭,勾臉的勾臉,戲班老板也很難得地穿上了戲服,還在臉上勾了臉,看扮相是一個老生。
“兩位領導,你們也扮上?”戲班老板走過來,手里還拿著水彩。
孫胖子看著他臉上油膩膩的,脖子就是一,問道:“我們是龍套,還要畫臉?”
戲班老板說道:“沒辦法,唱夜戲的規矩就是這樣,戲班出九個人,剩下的就要由事主家屬來頂上。沒事的,兩位領導,夜戲我們大班唱了也有幾回了,只要規矩做足了,就從來沒遇到過什麼事。”
趁老板給孫胖子勾臉的空當,我向老板說道:“看老板你昨晚的路數的,你們唱戲的還懂這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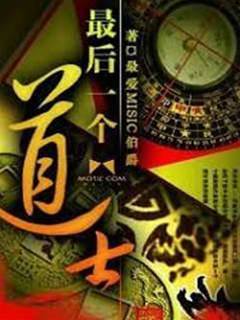
最後一個道士
查文斌——中國茅山派最後一位茅山祖印持有者,他是中國最神秘的民間道士。他救人於陰陽之間,卻引火燒身;他帶你瞭解道術中最不為人知的秘密,揭開陰間生死簿密碼;他的經曆傳奇而真實,幾十年來從未被關注的熱度。 九年前,在浙江西洪村的一位嬰兒的滿月之宴上,一個道士放下預言:“此娃雖是美人胚子,卻命中多劫數。” 眾人將道士趕出大門,不以為意。 九年後,女娃滴水不進,生命危殆,眾人纔想起九年前的道士……離奇故事正式揭曉。 凡人究竟能否改變上天註定的命運,失落的村莊究竟暗藏了多麼恐怖的故事?上百年未曾找到的答案,一切都將在《最後一個道士》揭曉!!!
129.6萬字8 14545 -
完結1700 章

重生冥婚:傲嬌鬼夫求輕寵
【重生+虐渣+1v1+靈異言情】「墨庭淵,我要和你離婚!」 「理由!」 「你醜!」墨庭淵鳳眸微瞇:「有膽子再給我說一遍!」 「老公,你好帥!」 「你才知道?」 蘇溫柔:「……」 重生一世,蘇溫暖帶著仇恨而歸,可卻招惹上一個霸道男鬼!想復仇,男人一聲令下,仇人全部死光,所以還復個毛線仇? 他,帝國總裁,權利大的隻手遮天,外界稱之為最薄情的男人,他不近女色,懟人從不留情,出門必帶麵具,所以至今為止,沒人見過他真實容顏,有人說他英俊,邪魅,也有人說他醜陋不堪如同鬼魅, 蘇溫暖兩者都不信,所以某一天入夜,蘇溫暖將她的爪子伸向墨庭淵,可結果… 「啊!鬼啊!」
154.4萬字8 8309 -
完結3506 章

六指詭醫
先天左手六指兒,被親人稱為掃把星。出生時父親去世,從小到大身邊總有厄運出現,備受歧視和白眼。十八歲受第三個半紀劫時,至親的爺爺奶奶也死了,從此主人公走上了流浪之路。一邊繼續茍延殘喘自己的生活,一邊調查謎團背后的真相,在生與死的不斷糾纏中,我…
661.4萬字8 17343 -
連載751 章

神秘復蘇之詭相無間
一張人皮面,一張生死卷。恐怖來臨,活人禁區,鬼神亂世。當整個世界有彌漫絕望,那我又該何去何從?天地啟靈,五濁降世。人間如獄,鬼相無間。ps:(本作品為神秘復蘇同人作,將與神秘復蘇保持同樣風格,不開掛,不系統,生死一線,搏命鬼神。)ps:(斷更鬼已復蘇,目前無死機辦法,所以講究隨緣更新,成績就是鎮壓斷更鬼的靈異物品,望各位把它封死。)
134.9萬字8.33 1392 -
連載723 章
出陽神
若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犯六千惡,為二十八獄囚。鬼有洞天六宮。道存七千章符。人養三萬六千神!這個世界,鬼不做鬼,人不當人。地獄已空,人間如獄。
131.4萬字8.18 93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