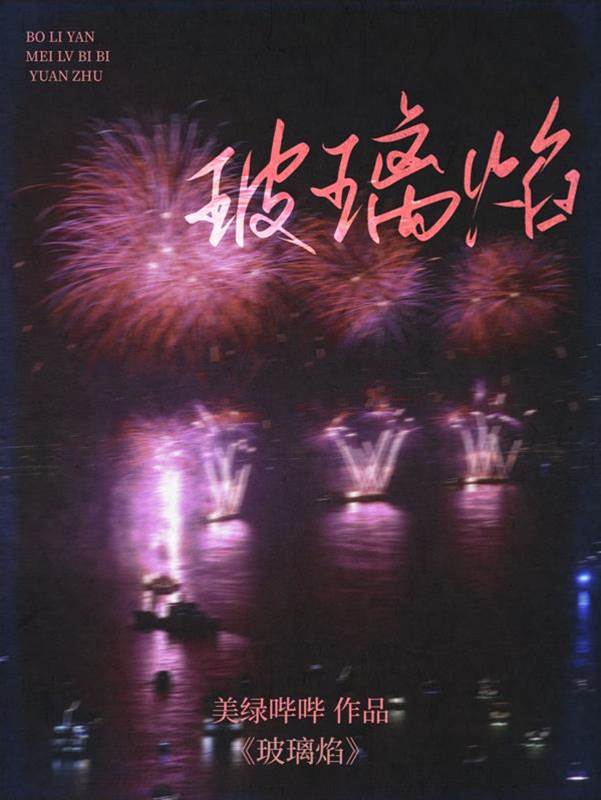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一生一世,江南老》 第一章 千年燕歸還(1)
臺州。
沈氏在江南已經傳承到二十六世,數百年來屹立不倒,本就備關注,沈公這次又是二十幾年來初次返鄉祭祖,自然有不隨其后,把這家事弄得極為熱鬧。
天朦朦亮,祭祖已經開始。
眾人從祠堂一路到堂奉香,最后踏上先祖墓道,行至墓前,開始論資排輩地鞠躬奉香。
一排排白的花,每個人上前時,都會彎腰添上一株。
沈昭昭和姐姐作為小輩,在最后等著。
后的兩個記者,難以到最側,索放下相機開始低聲八卦。
“現在獻花的是沈卿秋,今年在墨西哥競選財政部長,沒想到他輩分這麼低。”
“這種大家族就是這樣,你看他前面的男孩子,看站著的位置比他輩分大,看著也就十五六歲?”
……
聽這話,努力往前排看,沒看到那個男孩子。人實在太多了。
到接近午飯的時間,祭祖終于告一段落,沈家安排了所有境外的人用餐,地點就在老宅,由專門請來的師傅做齋膳。
幾個常年住在臺州的人,負責招待外客的用餐。
母親把兩姐妹給了沈公的兩個孫子沈家明和沈家恒照看,沈家明昨夜見過這對小雙胞胎,給沈家恒介紹說:“都是遠房表妹。秦昭昭,沈昭昭,一對雙胞胎。秦是姐姐,沈是妹妹。”
們的母親才是沈家人,所以是表妹。
“等等,你把我說糊涂了,”沈家恒一頭霧水,“雙胞胎?為什麼兩個姓?”
沈昭昭和姐姐相視,都笑了。
自從昨夜來,這問題們聽了沒有十次也有八次。
“姐姐跟爸爸的姓,妹妹跟媽媽的姓。”
“那平時怎麼區分,大昭和小昭?”
Advertisement
“還大喬小喬呢……”沈家明輕聲對自己弟弟耳語解釋,“他們爸媽分開得早,姐妹倆一人帶一個,沒這種難題。”
沈家恒被解了,仍盯著們,似還有疑。
“是不是還要問,我們為什麼長得不像?”姐姐甜甜一笑,著這位遠房表哥。
說實話,這雙胞胎生得差別真是大。
姐姐下尖尖,鼻高,眼窩深,桃花眼,眉很濃但因為年紀小沒刻意修過,有些雜、不是很齊整;而沈昭昭是鵝蛋臉,面頰有,偏杏眼,眉彎彎,生來就整齊。
那里最不像,姐姐是薄,形偏圓潤。
“我們一個像爸爸,一個像媽媽。”沈昭昭也對兩個哥哥笑了。
是異卵同胞。
父母從小就這麼告訴們。
兩個哥哥要招待客人,要人開車送們去看沈家玉坊。
姐妹倆都表示沒興趣,問人要了一把雨傘,一同撐著出去閑逛。
沈家在這里有三宅院,一捐給了當地政府,一開了玉展館,僅留了這一地偏僻祖宅。
因為位置極偏,完全沒商業化的痕跡,全是一家家的尋常住戶。
橋有,未經過修葺,窄巷有,被連日雨水沖泡的泥濘難行。
們繞了一個大圈,沒看到什麼好景致,反倒連著看到兩個荒廢的空院子,盡是灰墻枯樹,在雨中頗為蕭索。
兩人商量著,還是回去好,
遠看著有家敞開式的糕點鋪,沒招牌,倒是像賣吃食的。
巷子積水多,姐姐腳上是白鞋,怕弄臟,不肯往前再走。
倒不怕,把傘留給姐姐,用手擋在頭前,繞開幾個水,用手擋在頭上,跑到了鋪子前。墻上有一張紙,寫著各式花糕的價格。
屋里沒亮燈,西北角的爐子生著火,照得室半壁亮堂堂的。
Advertisement
面前幾個藤編的籃筐空著,里邊籠屜也是空的,往里看,終于看到的右邊桌子上有剛做好的一排花糕。一只手打開了深藍的布簾子。
終于有人了。
“你好,我想買花糕。”聲音清脆地招呼著店家。
伴隨著的詢問,簾子后走出來一個年。
看上去十五六歲,穿得是一套合的休閑裝,上清清爽爽什麼都沒有,只有手腕上的一塊玫瑰金的表。
短發下的一張臉乍現在眼前,映著爐子里的火,是白是黑都判斷不出來。待他走到自然線下,方才出清晰的五。瘦臉,鼻窄高,眼睛勾外梢,猶如刀裁。眼奕奕。
鼻梁上有一塊新的痕,像方才撞破不久。
沈昭昭沒仔細看他,將斜在背后的銀鏈條包拽到前,打開搭扣。
爐子里出兩聲炸響,是木柴被燒得裂。
被駭得抬眼。
這回是正正好好,目相對。
突然就看不清他的眼和臉,像完全不過氣……極不舒服。這迫和難過只有短短的一剎,很快消散。
肯定是下雨低氣,氣悶了。
沈昭昭默默地緩了口氣,找出零錢,雙眸含著笑對他說:“那個上邊有紅的一點點的,要那個味道的,要三塊。”
隔著低矮的柜臺,遞過去錢,對方沒接。
“紅的那個。”又重復。
他遲疑了一霎,順著小孩的眼神,去看新出爐的各花糕。
“再說一次。”他終于說了第一句話。
“紅的。”
他未,繼續問:“從右邊數第幾個?”
沈昭昭被他的話唬住,沒懂自己哪里說錯了,但還是按照他的方式回答:“右邊第三個、第四個和第五個。”
Advertisement
沈策沒去拿糕,反倒從子口袋里出一個黑錢夾,對著簾子后說,剛才的都包起來,再要三塊花糕。
一個老婆婆笑著走出來,一個勁地道歉著,說來晚了,包好了要的花糕。
直到他結算,終于懂了,這人不是賣糕的。
這是和沈策的初相識。
半小時后,和姐姐被母親帶去見表外公,進了正廳,看到他坐在沈公右手側的椅子上,而他的對面是表哥沈家恒。
“雙胞胎來了。”沈公笑著說。
沈昭昭眼睛睜大,不可思議地著他。
他看著忍著不說話,猛瞅自己的神態,倒是毫不意外,好似知道,一定會有這第二次的見面。在后巷看到的著,還有脖子上掛著的玉墜,他就曉得這孩是沈家的人。這次來祭祖的孩子,每個都被沈公送了個類似的小玩意兒。
沈策,來自澳門的沈家后人。
對于澳門的分支,聽媽媽講過兩回。沈家祖上曾過一次大難,險些被滅族,因此分了支,一支留在臺州,一支南下,幾經輾轉定居到澳門。不過南下那一支在清朝滅亡前亦過重創,人極,但不論男都是人中龍。所以對澳門的沈家人始終有著極好的印象,今天終于見到了。
起初還以為這個哥哥很特別,聽說自己和姐姐是雙胞胎,也沒出驚訝表,也沒問為什麼長得不像。
等到他聽到說兩個“昭昭”,突然抬眸,認真在兩姐妹這里看多了一會兒。
沈昭昭忍不住笑出聲。
姐姐則故意嘆了口氣。
大家都過來。
“怎麼,和這個哥哥很投緣?”表外公和氣地問。
笑著“嗯”了。
他一定會問,為什麼有兩個昭昭。
Advertisement
意外地,沈策盯著兩姐妹看了半晌,只是贊了句:“好名字。”
“算起來,你輩分不低,”沈公說,“這對雙胞胎要怎麼你,還真是個難題。”
“哥哥。”沈策說。
來時他父親囑咐過,十幾代以前就分開了兩支,早沒了緣聯系,這回來不必跟著臺州的人排輩分,按照年紀隨便一些就好。
兩姐妹在長輩的安排下,和這位關系遠到十萬八千里外的哥哥打了正式的招呼后,被人專門送去了到了另一個院子。
這院子在雨停后,早早被人打掃干凈。
庭院里的燈,還有裝飾的木燈籠都被點亮。假山上、湖上也都有燈,全都點亮,為了讓這群孩子們玩的盡興。
今日祭祖結束,明日后大家都會相繼離開,也不曉得能不能再見,所以沈家的孩子們被大人們安排在這里,最后一聚。幾歲的孩子被帶著看走馬燈,大些的一起玩牌九,因為生長環境不同,院子各種腔調,各種語言錯著,英法西居多,還有普通話、粵語、閩南語和四川話混著來。
再加上糯婉轉的吳儂細語,全匯在一,熱鬧得不樣。
姐姐和人玩牌九,在一旁聽大家聊天。
夜幕降臨后,有人開始往花叢里灑驅蚊水,搬了幾盆夜來香放到池塘旁驅蚊。是頭回見夜來香,蹲在花盆前看那檸黃的花,仔細聞了聞,好濃的味道。
一只手拉起來:“這香味聞多了,對人不好。”
提醒自己的是沈家恒,而他后一道來的就是沈策。
這算是今日兩人第三次見面。
旁邊有個四五歲的孩子在玩跑馬燈,在飛快地轉著,一道道影子從他的臉上掠過。他倒不像在正廳里,佯作未見過了,明顯在看到這里時候,笑了笑。
沈昭昭倒背著手,故意沒和他打招呼,和表哥沈家恒細細問起了夜來香。
沈家恒本就喜歡這個生得極漂亮的遠房妹妹,講得仔細。沈策饒有興致聽著他們兩人閑聊,沒話,兩人都只當沒下午那場意外的相識。
“我晚上看不大清楚,”姐姐忽然把手里的骨牌塞給旁的一個孩,“你來吧。”
這是個借口。整晚姐姐贏了太多次,不好意思再贏。
接了姐姐牌的人,很快贏了。
在大家的笑聲里,忽然有人問姐姐:“為什麼晚上會看不清?”是聽了半小時的夜來香、驅蚊草都沒加話題的沈策,終于有了聊天的興致。
“是夜盲。”姐姐沒料到這個人會問。
姐姐下午沒去花糕鋪子,和沈策沒集,僅有的一次見面也就是在前廳了聲“哥哥”。沈策對來說就是純粹的陌生人。
所以兩人的對話出現的很突兀。
沈家恒倒是關心表妹,跟著問:“沒看醫生?醫生怎麼說?”
“看過,好很多了,”姐姐含糊地說,“有時還不行,線暗就不行。”
沈昭昭聽得想笑。
從小夜盲的是沈昭昭,不是姐姐。幾歲時在國,經常因為這個被小伙伴哄笑,也因為如此,姐姐知道不愿承認,經常會幫妹妹,把這件事攬到自己的上。后來年齡大了,的夜盲癥好轉,姐姐反倒喜歡用這個“借口”來搪塞各種問題。
連父母都被姐姐騙得很好,還會慨,這是不是家族傳,小兒好了,大兒卻有了這問題。
后來那晚,
沈昭昭察覺沈策看了兩次自己這邊,開始都不好意思回視,最后發現,他看得是旁的姐姐。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88 章
七零嬌女有空間
花朝大夢一場,帶著空間重生了! 這時候,她才十六歲,還是個嬌嬌俏俏的小姑娘,二哥沒有過失傷人致死,父母也都好好地……最重要的是,她還擁有一個健全又幸福的家! 撥亂反正重活一世,她腳踹渣男,拳打白蓮,護家人,踩極品,還反手捉了一個寬肩窄臀腰力好的小哥哥,利用空間一起玩轉七零,混得風生水起……
105.7萬字8 50643 -
完結552 章

全娛樂圈都在等影后打臉
雲城第一名媛葉傾城重生了! 從此,娛樂圈多了個叫蘇淺的巨星。 從娛樂圈新人到影后,她一路平步青雲,所謂人紅是非多,各種撕逼黑料接踵而至。 蘇淺冷笑! 她最擅長的就是打臉! 越黑越紅,終有一天,她另外一重身份曝光,再次重回名流圈。 看她如何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跪著讓他們唱征服!
97.1萬字8 17046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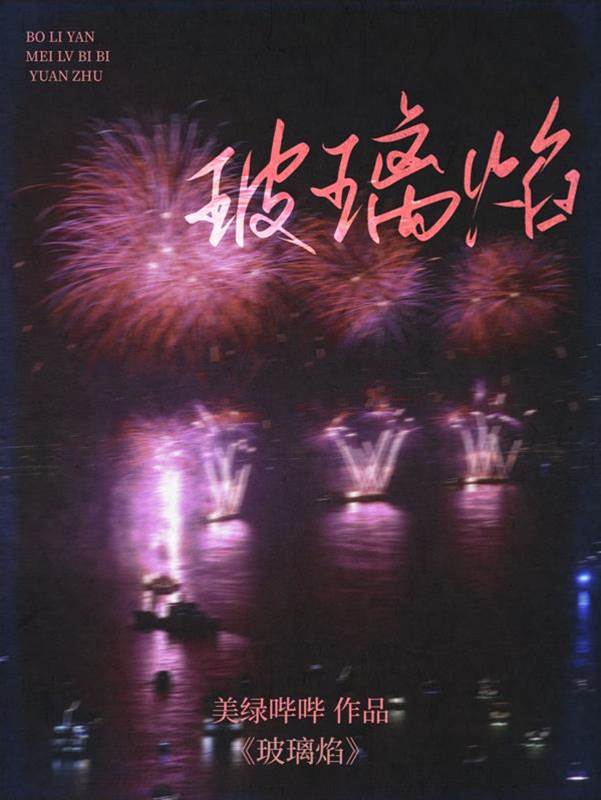
玻璃焰
[已簽約實體待上市]【天生壞種x清冷校花】【大學校園、男追女、協議情侶、強製愛、破鏡重圓】黎幸在整個西京大學都很有名。高考狀元,夠美,夠窮。這樣的人,外貌不是恩賜,是原罪。樓崇,出生即登上金字塔最頂層的存在優越家世,頂級皮囊但卻是個十足十的人渣。——這樣兩個毫無交集的人,某天卻被人撞見樓崇的阿斯頓馬丁車內黎幸被單手抱起跨坐在腿上,後背抵著方向盤車窗光影交錯,男人冷白精致的側臉清晰可見,扣著她的手腕,親自教她怎麼扯開自己的領結。——“協議女友,知道什麼意思嗎?”“意思是牽手,接吻,擁抱,上床。”“以及,愛上我。”“一步不能少。”——“玻璃焰,玻璃高溫產生的火焰,銀藍色,很美。”
25.7萬字8 14204 -
連載274 章

前妻太難追,偏執總裁他步步緊逼
【男主偏執病嬌 女主清冷美人 強取豪奪追妻 1v1雙潔 HE】五年婚姻,陸玥隱藏起自己的本性,乖巧溫順,取悅著他的一切。可圈內誰人不知,傅宸在外有個寵上天的白月光,為她揮金如土,就算是天上的星也給她摘下來。而對於陸玥,他覺得,她性子溫順,可以永遠掌控在手心。直到某天,她一紙離婚協議甩給他,轉身走人,與新歡站在商界巔峰,並肩而立。可在她一回頭,卻看見菩提樹下,傅宸的臉。“想離婚?”他一身純黑西裝,矜貴無比,淡淡道:“做夢。”
30萬字8 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