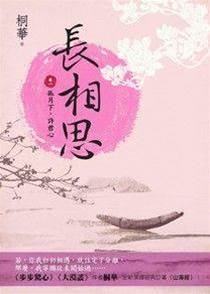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糖寵》 第45章 鳳翎宮
一旁的宮蕊兒給嚴貴妃端了一碗熱茶,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才開口說道:“裴姑娘快起來吧。”
嚴貴妃的嗓音很,瞥了一眼邊上的宮:“蕊兒,給裴姑娘賜坐。”
裴瓊謝了恩,在椅子上坐下。因為走了太多路,坐下時一彎曲,全是麻麻的刺痛,神有些不自然。
嚴貴妃仿佛沒看到似的,的紅勾勒起一個嫵的弧度,笑著問了裴瓊的年齡、喜好等。
雖然嚴貴妃生得麗, 也一直笑著,可裴瓊總覺得的神有一種莫名的沉。
裴瓊乖巧地回答了嚴貴妃的問題。疼, 只想快些回答完就回家。
嚴貴妃雖不喜裴瓊的樣貌, 卻勉強滿意的子,看上去很單純, 像是個容易掌控的。
笑著對裴瓊說:“也不知這裴家是怎麼養的,竟養出這個麼鐘靈毓秀的兒。我這一見到,就得不行。”
剛才迎著裴瓊進來的笑臉嬤嬤站在嚴貴妃邊上, 笑著應和道:“奴婢瞧著, 裴姑娘依稀有幾分娘娘年輕時候的模樣。”
嚴貴妃聞言, 臉上的笑消失了。的手過眼邊的細紋,忽然對裴瓊招招手,“來。”
裴瓊有些不安,忍著疼, 走到嚴貴妃跟前去。嚴貴妃用手沿著的臉描摹了下。
嚴貴妃的手又涼又,的裴瓊很難。
神晦暗,語意不明地嘆:“本宮年輕的時候啊……”
裴瓊被看得有點怕,努力抿出一個甜笑,道:“娘娘國天香,氣度高華,是天下最尊貴的子,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烏溜溜的眼睛黑白分明,認真看著人的時候顯得無辜又真誠。一番話,倒是說得嚴貴妃出今天第一個真心的笑。
Advertisement
嚴貴妃后的嬤嬤適時拉了拉。
嚴貴妃被嬤嬤一提醒,拉著裴瓊的手道:“本宮那小兒子棠兒,與你年紀相似、喜好相仿,若你與他見了,定然合得來。”
裴瓊記得進宮前阿娘和說過,貴妃的小兒子是怡王。一個閨閣兒,怎麼能與怡王私下見面。
嚴貴妃說的話不合禮數,裴瓊的手也被挲得難,但又不能正面反駁。
裴瓊把自己的手從貴妃手里出來,低聲道:“怡王殿下份尊貴,裴瓊哪里配與之相見。”
嗓音很甜,此刻因為怯意而放低了,嗓音里更帶了點糯,聽得嚴貴妃擰起了長眉。
小小年紀就一副狐樣子!
不配與的兒子相見,卻與肅王暗通款曲。
嚴貴妃冷笑道:“依本宮看,裴姑娘與棠兒那孩子正相配。”
裴瓊才不覺得那勞什子怡王與自己相配。一個大男人,也什麼糖兒,不,定然是與這嚴貴妃一樣,是個討人厭的人。
繞來繞去的,就是不接嚴貴妃的話茬。
不識抬舉的東西!
嚴貴妃近日過得艱難。朝中肅王當政,皇帝又冷落,那些人最是趨炎附勢的,一個個作踐起來,養尊優了這麼些年,哪里的住那些氣。
雖然最近陛下對肅王有所忌憚,為此對好了一些,但這翎宮也不復往日的榮耀了。
心眼最小,近日脾氣又暴躁,眼見著連這麼個小丫頭片子都不應承,臉上的笑差點都維持不住。
嚴貴妃不顧后嬤嬤的勸阻,把所有人都趕出去了。
今日不好,滿室的人都退出去之后,這座華致的宮殿就顯得異常冰冷。
裴瓊看看這冰涼得顯得可怖的宮殿,又看看神有些不正常的貴妃,心里有點怕,不自覺地也往后退了兩步。
Advertisement
這會兒人都走了,嚴貴妃的神和這座宮殿一樣冷下來。
“坐下。”對裴瓊命令道。
嚴貴妃看著裴瓊神痛苦,有點艱難地坐下來,眼里似有幾分詭異的滿足。冷笑道:“你看不上我的棠兒,是因為肅王?”
裴瓊沒回答。一聽到阿恒哥哥,就像只領地到侵犯的小兔子,立刻警惕地看著貴妃。
這反應看得嚴貴妃笑出了聲,站起來,高高地俯視裴瓊。
“你以為肅王是什麼好人?他殺人如麻,最是惡毒詭譎,說不定有一天連你也不會放過。”
聽到阿恒哥哥被這樣詆毀,裴瓊忍不住了。
“娘娘不要信口開河!”
見人上鉤了,嚴貴妃反而緩緩坐了下來。端起微涼的茶水,不甚介意地抿了一口。
白皙的指尖著茶蓋晃了晃,狀似不經意地問道:“你可還記得姜嫵?”
裴瓊不說話也不理。從小被寵著長大,去了哪里大家都喜歡,哪里過嚴貴妃這樣的氣,更可恨的是還要詆毀阿恒哥哥,實在可惡。
嚴貴妃見人不說話,也不介意,嗤笑了下,道:“讓我來猜猜,是肅王在公主府救了你,你才對他傾心的?”
停頓了下,見裴瓊臉有了一點變化,才接著道:“你不覺得奇怪嗎?姜嫵素來溫順,為什麼會行刺你?而且,行刺你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沒出現過。”
消失了?
裴瓊有點不安。之前是聽說姜嫵第二日沒回姜府,但人在公主府,們家不敢過問,難道到現在姜嫵還被扣押在公主府嗎?
嚴貴妃繼續說道:“好好的一個人,就算有罪,也該由府置,怎麼就消失了呢?”
此刻外面似乎在刮大風,宮殿里一扇沒關好的窗戶被吹開了,撞到邊上的木架子,在寂靜的宮殿里發出好大一聲響。
Advertisement
裴瓊被嚇得一哆嗦。
嚴貴妃眼角余看到那小丫頭的樣子,出一個笑,“姜嫵已經死了。無論是姜嫵的傷人,還是姜嫵的消失,都不過是肅王設的局罷了。連你的喜歡也都是他的設計。”
裴瓊原本聽到姜嫵死了,擔心得不行。但嚴貴妃后面的話越說越離譜,狐疑地看著嚴貴妃。
喜歡阿恒哥哥,和姜嫵并無關系。一定是這個貴妃不喜歡阿恒哥哥,編些什麼姜嫵死了,阿恒哥哥不是真心喜歡自己的之類的事,來離間他們倆的。
嚴貴妃能探聽到的確實不多,連趙啟恒和裴瓊的事,都是因為公主府那日的事疑心四起,多方打聽,才猜出一丁半點。
原本想讓棠兒娶了這裴瓊,不僅能惡心趙啟恒,有這麼個籌碼在們手里,趙啟恒說不定會有一些忌憚。
沒想到這小丫頭片子這樣不識抬舉,嚴貴妃又不喜歡一副狐樣子。到時候把棠兒的心籠絡了去,讓棠兒與自己離了心怎麼辦?
因此不顧伏嬤嬤的勸阻,想著這小丫頭片子看著笨笨的,倒不如說點什麼,離間了和趙啟恒的關系,說不定有機會見到趙啟恒痛徹心扉的樣子。
想一想那畫面,就痛快。
可裴瓊不進嚴貴妃的套,正道:“姜嫵不見了,同阿恒……同肅王有什麼關系。娘娘沒有證據,張就說是肅王做的,我還能說姜嫵是被娘娘殺了。”
怎麼能讓別人給阿恒哥哥潑臟水!
一涉及趙啟恒,裴瓊就像只張牙舞爪的小貓,也不顧阿娘臨走前的囑咐,對貴妃齜著一口小牙,想保護的阿恒哥哥。
嚴貴妃見這樣信任趙啟恒,有幾分驚訝。但也沒辯駁,一件事不信,多說幾樣,這小丫頭片子總會信。
Advertisement
“小丫頭,你知不知道宣平侯府和高府?”
裴瓊不點頭也不搖頭,眼里是十分的防備。
嚴貴妃也不管的反應,了自己的發髻,把上面一玉簪扶正,自顧自地說起來。
“你家里原本給你定了宣平侯府的親事。你的好肅王為了攪這樁婚事,設計陷害孟慶德,給他扣上不孝荒的名聲。”
“還有高府。高府有意與你家結親之后,京中就開始紛紛傳說高夫人殺人之事。現在查不出人是不是殺的,但已經進了大牢。”
“你以為這些事都是誰做的?這些人原本可以好好過日子,就因為趙啟恒心思狠辣,濫傷無辜,才落得如此下場。”
裴瓊一點也不信任嚴貴妃,看著嚴貴妃的神越來越癲狂,覺得怕不是失心瘋了。
裴瓊辯駁道:“若高夫人真的無辜,怎麼會被抓到牢里?”
嚴貴妃見油鹽不進,神越發猙獰,忽然放輕了聲音,道:“趙啟恒就是個怪胎,從小就心思狠。那些人和我的鈞兒一樣,都是無辜的,都是被他陷害的。就連你,遲早有一天也要死在他的手里。”
裴瓊被這副猙獰的樣子嚇到了,白著一張小臉,想往門外跑,但疼,一時之間站不起來。
看嚴貴妃的神,似乎已經失去理智了。暗地里,數十個暗衛地盯著下面,只要嚴貴妃敢有異,就會即刻出手。
空氣都凝滯了。
轟地一聲,門被踹開。
冬日寒冽的風吹進來,把一室沉都吹散了,小姑娘什麼都還沒看清,就落到了一個溫暖的懷抱里。
作者有話要說: 嚴貴妃說的話雖然大部分是猜的,但除了部分,其他都猜得差不離兒。如果能清醒一點,就會知道自己浪費了一把好牌,不過再也沒有出牌的機會了。(給我一點信任,我是甜珍珠,絕對不會。)
謝不可諼的1個地雷,啊啊啊噢噢噢呀的1個地雷;謝宿煙城的1瓶營養。你們,麼麼噠~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3581 -
完結369 章

權臣心上撒個嬌
蕭懷瑾心狠手辣、城府極深,天下不過是他的掌中玩物。 這般矜貴驕傲之人,偏偏向阮家孤女服了軟,心甘情願做她的小尾巴。 「願以良田千畝,紅妝十里,聘姑娘為妻」 ——阮雲棠知道,蕭懷瑾日後會權傾朝野,名留千古,也會一杯毒酒,送她歸西。 意外穿書的她只想茍且偷生,他卻把她逼到牆角,紅了眼,亂了分寸。 她不得已,說出結局:「蕭懷瑾,我們在一起會不得善終」 「不得善終?太遲了! 你亂了我的心,碧落黃泉,別想分離」
65.4萬字8.18 673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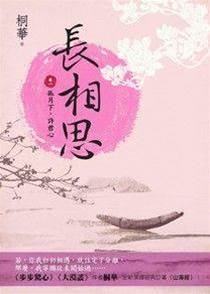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790 章

重生后我被繼兄逼著生崽崽
上輩子的謝苒拼了命都要嫁的榮國候世子,成親不過兩年便與她的堂姐謝芊睡到一起,逼著她同意娶了謝芊為平妻,病入膏肓臨死前,謝芊那得意的面龐讓她恨之入骨。一朝重生回到嫁人前,正是榮國侯府來謝家退婚的時候,想到前世臨死前的慘狀,這一世謝苒決定反其道而行。不是要退婚?那便退,榮國侯府誰愛嫁誰嫁去!她的首要任務是將自己孀居多年的母親徐氏先嫁出去,后爹如今雖只是個舉人,可在前世他最終卻成了侯爺。遠離謝家這個虎狼窩后,謝苒本想安穩度日,誰知那繼兄的眼神看她越來越不對勁? ...
106.2萬字8.18 21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