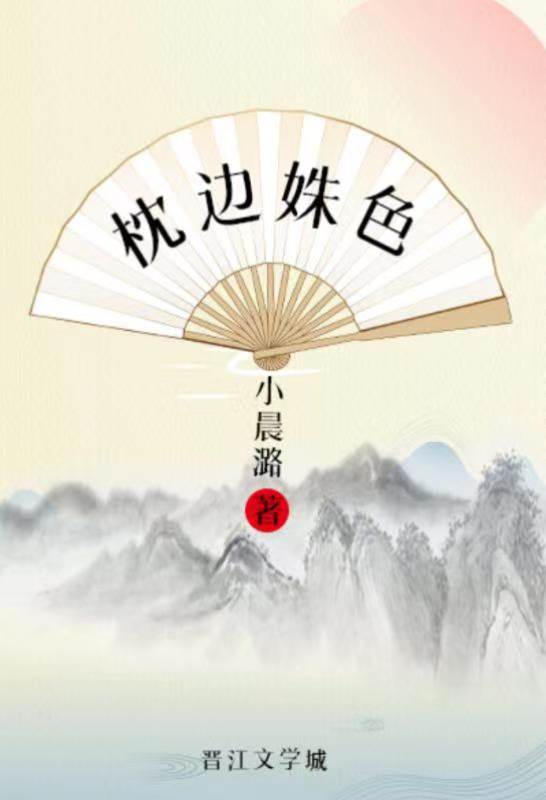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尚書大人,打發點咯》 第六十三章 大婚【三更】
連喻大婚了。
這是整個四九城里都沒見到過的排場。
八人抬的大紅花轎,連轎頂都綴著金走線的連枝花紋。連喻是文,又是大堰唯一一位異姓王的嫡孫,圣上特賜婚禮以侯爵制,迎親的隊伍自連府出發,撒了遍地的喜糖紅包。
老百姓都翹著腳在路邊看著,心里都在納罕,都說連尚書摳的往自己上打補丁,原來全用來攢老婆本了。就今日這通排場,非皇親可與之媲。
方正心里歡喜瘋了,想他一個京城里普普通通的糧商,哪里見過這樣大的排場。他以為這通面子會讓他十分的開懷,但是當方婉之蓋著蓋頭從閨閣里出來的時候,心中又是從未有過的悵然。
他二十年沒疼寵過這個閨,如今要出嫁了,紅鞋邁出門檻的那一刻,說不出來的不是滋味。
盧二娘陪在方婉之的邊,陪著邁過一層一層的臺階。方正急走了兩步,遲疑了許久攥住方婉之的手。他想,他應該是要說些道理給聽的。諸如從今往后要恪盡婦道,出嫁從夫,不能再由著過去的脾氣。再如,繡工不好要多多改進,沒得讓人笑話了去。但是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不知道旁的父親在送出嫁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心,總之他沉默了許久也只說了一句。
“欺負了,就回家。...父親不好,但是...”
后面的話方正再也說不出來了,淚水落在他依舊泛著油的臉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壑。他老了,老到在見到兒出嫁的這一刻,心已經無關了金錢權勢的種種,只是單純的想要他的兒一輩子幸福安康。
握的手掌之間,有淚珠墜落,方婉之在哭。其實很想告訴方正,從來沒有怨恨過他,但是泣不聲。
Advertisement
盧翠花的手里還抱著方婉之親娘的排位,淚眼婆娑的告訴。
“老姐姐,閨出嫁了,咱們一起給送送吧。”
上轎之前,方婉之拜了親娘排位,而后對著方正和盧翠花鄭重行了一個跪禮。
這是在世間唯二的兩個親人了,今日他們送出嫁。可能兒真的要到披上嫁的那一瞬才會知道,曾應無數次想要逃離的那個家,也是如斯溫暖。
京城有踢轎門的風俗,是在給新進門的媳婦立規矩,寓意新娘嫁過來之后要百依百順。連喻聽了以后覺得十分荒謬,直接命喜娘將轎門打開,將方婉之抱了出來。
彼時,方大姑娘還在喜帕下哭的一塌糊涂,連喻拉著方婉之的手將紅綢的另一端放在的手心故意唉聲嘆氣的道
“哭什麼,嫁過來也是你欺負我。”
方婉之又忍不住被他逗笑了。
屋嘈雜的賀喜之聲不覺于耳,一紅綢之間,牽系的是彼此終生相伴的那個人。
喜服的下擺很長,讓方婉之一度擔心自己會摔倒。然而此時心底卻是完全的踏實,什麼都不怕了,因為知道即便摔倒了,也有連喻扶著。
贊禮三唱扣禮。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三拜夫妻,和順榮長。
坐在大紅的床帳之中,方婉之聽到喜娘說了一溜的吉祥話。一個字兒也沒聽清,只知道窩在蓋頭底下傻笑。
蓋頭被掀開的那一刻,方婉之還呲著小牙嗤嗤的笑,撿了多銀子似的,一點也不。
連喻端詳著,忍不住了下的鼻子。
“方婉之,你怎麼笑的跟個傻子似的。”
方婉之就說。
“現在你退不回去了,今后還不一定誰是傻子呢。”
喜娘大概從未見過這麼喜慶的一對新人,年紀雖大了,但是十分懂得識人眼,伺候了合巹酒道過了漂亮話就帶著人出去了。
Advertisement
可嘆連喻也不能在屋里多呆,外頭還有一眾的賓客在等著他呢。
皮皮敲著門口的窗戶氣急敗壞的說。
“您要不去深山老林里結婚去,這會子外頭的人都嚷嚷著找你呢。”
連閣老此生對于應酬一事從來都不陌生,然而今日真的萬分的不想去。
最后還是方大姑娘瞪了眼珠才算不清不愿的出了門。
待到連喻回來的時候,方婉之已經換上了緋的常服,紅燭之下,人嫣然一笑,何等風。
連喻一直靠在門口看著,模樣和神態都有些懶,明明只是微醺,卻無端的覺得自己醉了。
方婉之說。
“倚在門口做什麼?”
連喻沒有說話而是直接將人攏在了懷中。大紅的吉服上染著濃濃的酒香,連喻垂頭嗅著方婉之的長發,嗓音是不同以往的暗啞。
“好像,...是要做點什麼。”
耳邊的熱氣堪堪劃過方婉之的耳際,幾乎燙傷了。手掌之下攥的帕子被做一團,是從未有過的張。
細的親吻自耳畔輕的過,先是額頭,再到鼻尖,再到的瓣,致的鎖骨。連喻似乎是要用勾勒出所有的廓。
紅燭帳暖,衫盡落,兩軀相擁的那一瞬間,所有的嘆息都淹沒在口之間,陌生的栗,由不得自己,也由不得對方,只能遵循著最原始的律,飄沉浮。
這一夜,很長。
方大姑娘就這麼把自己給嫁了,二十歲高齡的姑娘,那樣風的一場婚禮,那樣俊秀的夫君,不知艷羨了大堰多人。
許多人都猜測,方婉之大概是個極其懂得為婦之道的人,至也是朵吳儂語的解語花。
雖然親之后的方婉之依舊張牙舞爪的像個漢子。
Advertisement
初為人婦的幾天,連夫人就接到了不朝中家眷發來的請柬。作為一個商賈出卻坐上尚書夫人位置的人,實在讓人好奇的。
另一層意思來說,朝廷想要跟連喻互相走的員何在數,連喻是個請不的,若是能請的夫人,也算是走了一些關系。
開始的時候,們一直覺得連夫人定然是不太好請的,然而方婉之卻是每宴必到,每席必吃。笑容自進門開始及至上車走人,永遠和善的讓人挑不出病。
但是要打包。
所有的剩菜剩飯,全部打包帶走。誰要是了問連府借銀子的心思,比任何人都看的。吃飯之前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最近手頭總是沒銀子,打個馬吊都不敢輸的太多。....都覺著我們京里的鋪子賺銀子,實際上賠的都在里,唉,在外難言苦啊,都是表面上看著風的,到底也是個尚書不是?”
幾個朝臣夫人聽了之后,再想要開口也只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久而久之,也就沒人再請吃飯了。
因為這些人也都看出來了,那個看似弱弱的連夫人也不是個省油的燈。配在連尚書邊,那就是一對睜著眼睛說瞎話的。
但是人家這瞎話便是說了你也沒本事反駁,連吃帶喝的從你家出來,你還是得卑躬屈膝的給人送出來。
坊間對連夫人的傳言一直沒什麼好話,市儈,世俗,不通理。
方婉之一概不理。
因為面對那些只想要不勞而獲的人,除了銀子,本堵不住他們的。
都說新婚燕爾最是黏糊的時候,連喻跟方婉之也如尋常夫妻一樣過的親香。只是該打仗的時候也打,該鬧別扭的時候也鬧別扭,連喻上的臭病多,方婉之理解這多是承襲了方老爺子的子,但是日懶洋洋的德行就實在不知道隨了誰了。
Advertisement
下了衙門就在屋里歪著,有的時候抱著貓歪著,多走一步都懶怠彈。方婉之說他他就頂,打仗從來沒輸過,睡了幾次書房之后老實多了。
要說他們家老爺子子不好歸不好,也沒見有這麼‘好的口才’啊。
方婉之還為此困擾了很久,直到在第二年的初夏,見到了看錯請柬日期跑來參加‘喜宴’的繞纖塵才有了領悟。
那是一日艷高照的午后,不錯的天氣,不錯的好運氣。打了馬吊回來的方婉之贏了不銀子,正一面塞著小荷包一面往府里走。
連府的院子里種了整整齊齊的一排桃花樹,花開的正好,桃花樹下卻不知何時窩了一個小小的人影。
那是個不大的小男孩,看量也就八,九歲的景,模樣生的很漂亮,圓圓的眼睛,睫特別的長,正盤坐在樹下擺弄自己的東西。
方婉之往近瞧了瞧,是十七八個木頭做的小玩偶,全部都在地面上穩穩的站著,不時隨著男孩手指的作翻兩下跟頭。
方婉之不知道男孩兒是誰,但是認識男孩手中的線。因為見到連喻用過。
這麼小的孩子會用傀儡,沒有吭聲,暗暗猜想對方的份。
小男孩兒早就聽到了靠近,也沒抬頭,依舊玩著手里的東西,張口問道。
“連喻什麼時候下衙?”
聲音清脆稚,卻不怎麼有禮貌。
方婉之覺得很新鮮,不由靠近了兩步。
“還有幾個時辰才回來,你是誰家的小孩兒,找連喻做什麼?”
看見男孩在聽到小孩兩個字的時候明顯蹙了眉。只是沒有發火,挑著眉頭問。
“不是說要親嗎?我來吃喜宴的。你又是誰?他什麼時候家里住過人了?”
方婉之看著那孩子。
“我們去年就親了。.....你不會是,看錯了日子吧?”
男孩聞言低頭,從懷里掏出一張皺的請柬,眼神好像還不太好,瞇著眼睛將紙張拿的遠,模樣神態竟然出些老態龍鐘。
他說。
“哦,看錯了。”
再抬頭看看方婉之,拄著腮幫子說了一句。
“我是繞纖塵。”
“!!!”
方婉之當然知道繞纖塵是誰,前年跟連喻在雁南那會兒,還親眼見過他的筆跡。一本門派辛被他寫的像封上下都不著調的隨筆,閑話家常都要比他寫的統些。
但是繞纖塵不應該有四十多歲了嗎?怎麼是個孩子的量?
方婉之上上下下的打量他,抖了半晌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然而這一不說話,繞纖塵就不滿了。
端著胳膊站起起問道。
“你是不是以為我是個侏儒?”
方婉之將腦袋搖的叮鈴咣啷的。
“哪,哪能啊。”
他的量雖小,但并不是年人的長相,真要說的確切些,又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形容詞。
連喻的師父第一次登門造訪,方婉之雖說到了驚嚇也不好怠慢了人家,待要將人請進去,又覺得這事兒實在匪夷所思。他連聲音都是個孩子呢。
場面僵持之際,卻是一個墻頭突然冒出的人影為解了圍。
人影說。
“繞纖塵,你這麼大一把年紀了跟個小姑娘置氣,真格是好笑的很。”而后抿一笑,對著方婉之頷首。
“他年時練了邪門的功夫,力損,每隔十年都要還一次重新長,你別管他。”
方大姑娘瞠目結舌的看著那個坐在三人多高的圍墻上的老太太,幾乎不記得怎麼說話了。
老太太很老,但是化了妝,灰白都頭發上梳了個流云鬢。得承認,那是個十分有韻味的老者,但是老者太老,以至于調皮的沖著自己眨眼睛的時候讓方婉之上生出了一的皮疙瘩。
看到繞纖塵漫不經心的把玩著自己的小布偶,憊懶的一斜‘老者’。
“師姐,五十步笑百步有什麼意思。算算日子,你今天都該八十了吧?還能嚼的東西嗎?”
凌寶寶聞言用手指卷了兩下鬢角的長發。
“嚼是嚼不了,好在生活還能自理,不至于像某些四十歲的男人一樣,每隔五年還得喝幾個月的米糊。你邊的那個脯大的丫頭呢?如今也有三十歲了吧?怎麼不讓跟在你邊,莫不是擔心人家認你的媽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5 章

登堂入室
元執第一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謀奪家業; 元執第二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栽贓陷害別人; 元執第三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那個乳兄終於不在她身邊了,可她卻在朝他的好兄弟拋媚眼…… 士可忍,他不能忍。元執決定……以身飼虎,收了宋積雲這妖女!
72.5萬字8.18 8869 -
完結1000 章

逆天神醫妃:鬼王,纏上癮
“王爺,不好了,王妃把整個皇宮的寶貝都給偷了。”“哦!肯定不夠,再塞一些放皇宮寶庫讓九兒偷!”“王爺,第一藥門的靈藥全部都被王妃拔光了。”“王妃缺靈藥,那還不趕緊醫聖宗的靈藥也送過去!”“王爺,那個,王妃偷了一副美男圖!”“偷美男圖做什麼?本王親自畫九十九副自畫像給九兒送去……”“王爺,不隻是這樣,那美男圖的美男從畫中走出來了,是活過來……王妃正在房間裡跟他談人生……”墨一隻感覺一陣風吹過,他們家王爺已經消失了,容淵狠狠地把人給抱住:“要看美男直接告訴本王就是,來,本王一件衣服都不穿的讓九兒看個夠。”“唔……容妖孽……你放開我……”“九兒不滿意?既然光是看還不夠的話,那麼我們生個小九兒吧!”
176.8萬字8.18 149187 -
完結972 章

一胎三寶:神醫娘親腹黑爹
四年前,被渣男賤女聯手陷害,忠義伯府滿門被戮,她狼狽脫身,逃亡路上卻發現自己身懷三胎。四年後,天才醫女高調歸來,攪動京都風起雲湧!一手醫術出神入化,復仇謀權兩不誤。誰想到,三個小糰子卻悄悄相認:「娘親……爹爹乖的很,你就給他一個機會嘛!」讓天下都聞風喪膽的高冷王爺跟著點頭:「娘子,開門吶。」
175萬字8 25431 -
完結1546 章

醫女天下:冷麵王爺欠調教
被嫡姐設計,錯上神秘男子床榻,聲名狼藉。五年後,她浴血歸來,不談情愛,隻為複仇,卻被權傾天下的冷麵攝政王盯上。“王爺,妾身不是第一次了,身子早就不幹淨了,連孩子都有了,您現在退婚還來得及。”垂眸假寐的男子,豁然睜開雙目,精光迸射:“娶一送一,爺賺了。”
268.2萬字8 2587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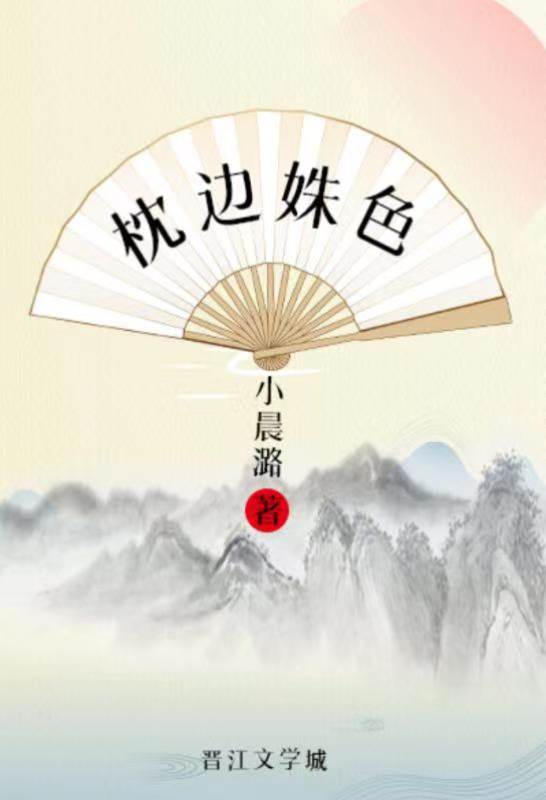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