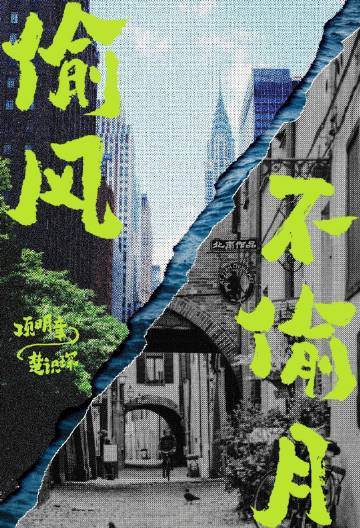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沉浮你懷中》 第20章 游輪失事 失蹤三天基本就意味著死亡……
包廂的角落沒人打攪, 只有兩個人坐在沙發兩側,在鬧中取了一片靜。
“走了。”聶顯忽然道。
陸聞別端起酒杯遞到邊,仰頭喝了一口, 仿佛漫不經心, “誰。”
“小瑟。”
他咽下口中的酒,垂眸凝神片刻, 看著杯中搖搖晃晃的,未置一詞。
聶顯張了張, 看上去忍了又忍, 最后憋出一句, “你連去哪兒了, 多久回來都不問一句?”
“那是的自由。”
“你會這麼說,我還真是一點兒也不意外, 因為我清楚你就是這種人。”聶顯表更煩躁了,抓起杯子就狠灌了幾口。
“你喜歡?”冷不防的,陸聞別淡淡拋出四個字, 短短的疑問句語氣卻像在陳述事實。
聶顯嗆了一下,“你瘋了吧?喜歡?小瑟對我來說最多就跟妹妹一樣, 你自己理不好還把我拖下水, 真有你的。”
陸聞別恍若未聞, 過了會兒忽然放下酒杯站起, “走了。”
“剛來就要走?”
“忙。”
“競標結束了, 許家那邊的問題也解決了, 還有什麼是忙得你現在非走不可的?”
“許家最近會有作, 陸氏要防患于未然。”
眼看著陸聞別要離開,聶顯忽然道:“你對小瑟,真的一點特殊都沒有?”
話音剛落, 原本要走的人腳步微頓,側看向他。
“有些話之前沒問你,因為覺得沒必要。但是現在我想知道,當初你教游泳,對特殊照顧,還有你們發生的那些,是為什麼?”聶顯問。
前段時間之所以覺得沒必要問,是因為他聽說許陸兩家依舊準備訂婚。然而現在陸聞別選擇了打許家而不是聯合的路線,聯姻的事顯然不可能再繼續了。
Advertisement
這麼多年朋友,聶顯清楚陸聞別是個怎樣的人。除開了真心的人或事一切都是利益至上,從不更改已經決定好的計劃,控制強,某種程度上來講很冷。
和許家聯姻之前也曾是他計劃中的一部分,但他的失控導致這計劃終止。
“談叔當時病重,這個消息不能告訴任何人。”
“所以,你只是因為可憐?”
陸聞別神冷淡,眉眼間不知何時多了點沉的惱意,“準確來說,是因為談叔的囑托。”
“就這樣?”
“只是這樣。”
聶顯出幾分難以置信的神,“剛才我說我了解你,但有時候,我又覺得自己不太懂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陸聞別漠然地將外套搭在手臂上,并沒有接他的話,“你之前的想法是對的,這些問題沒必要問。”
“你現在不準備和許詩薇訂婚了。”
“那又如何。”
“為什麼不告訴小瑟?”
“我找談過不止一次,你當初也阻攔過。”陸聞別淡淡道,“我尊重的選擇。”
聶顯睜大眼,差點被氣得一口氣不上來,最后他猛地站起,氣急敗壞道:“為什麼不想跟你談,我又為什麼阻攔你?才多大,十九歲!先見你這個混蛋,再經歷父親去世這種重創,這對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們誰也不知道。”
離得近了,他才看到陸聞別的表遠遠不像他想的那樣平靜。
兩人認識這麼多年,常常一個眼神就能猜到對方在想什麼,因此是真的無于衷還是飾太平,一目了然。
“作為朋友,我最后和你說一句。”他搖了搖頭,“或許你會后悔的。”
**
夕沉稠白云與粼粼水波織的邊緣。晚霞赤的余暉吞沒甲板,無數自然而純粹的在視野中蔓延到極致。
Advertisement
游餐廳里又響起了小提琴聲,陸陸續續有客人前來用餐。
這艘游的終點,是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島。
游上的人們彼此之間并不悉,但他們都留意到了船上一個“神”的年輕人。
年紀不大、漂亮、獨來獨往、很開口和別人談,一日三餐準時得變態,非用餐時間要麼待在房間里,要麼在甲板上吹風,從不參加任何娛樂活,對所有上前搭訕的人也統統禮貌拒絕。
今晚又是在六點準時出現在餐廳,然后吃完晚餐后起離開,仿佛察覺不到其他人好奇的打量。
只不過這一次,甲板上有人舉著單反將鏡頭對準了。
“葛歡,你經過別人同意了嗎就拍照?”
“誒你別煩我,我這調呢。”
片刻后,人按下快門,心滿意足地放下相機檢查果,“你放心,我沒那麼沒素質。”
“你要干什麼?”男人問。
“親自去問問人家介不介意呀。”
話音剛落,就起朝著那道纖細的影走去。
“嗨!”
談聽瑟一愣,轉頭的瞬間已經掛上了禮貌的笑容。站在面前的是個背著單反的人,看上去大概二十五六,淺麥的漂亮,神熱烈友善。
“中國人嗎?”對方問。
點頭,“我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我是個攝影師,那是我的同事,我們一起來采風。”人回指了指,“剛才鏡頭里看見你太漂亮了,沒忍住拍了張照片。如果你介意的話我會刪掉的,當然,刪除之前可以發給你當作旅行紀念。”
談聽瑟接過單反,看見照片時怔了怔。
畫面里的人神平靜,但是卻沒什麼鮮活的表,與背景里的天空、晚霞與海水有種奇異的矛盾。
Advertisement
……都不知道目前的自己在別人眼里是這樣的。
“要留下嗎?”
“……不用了,謝謝你。”
“不客氣。”人干脆利落地刪除,“看,刪掉就沒啦。”
談聽瑟微愣,轉頭和對方四目相對,在那種善意且帶著暖意的目里似乎明白了什麼。
這個陌生人,好像是故意用這種方式來和說話、開解的。
“謝謝你。”心緒難得有了點波,又一次因為這份陌生的善意真誠地跟對方道謝。
“不介意的話我們聊聊天?我跟我那個男同事沒什麼共同語言,這兩天太無聊了。”人出手介紹自己,“我葛歡,歡樂的歡。”
談聽瑟猶豫半秒,說出自己名字的同時回握對方的手,然后忍不住問:“這麼千里迢迢地去采風,是出差嗎?就你們兩個人?”
“也可以說是出差吧。我們有一個小工作室,定期給人文地理雜志供稿,所以平時會天南海北地走走。”
“我還以為你是拍人像的。”
“當然不是啦,或者說不是你想的那種人像吧。”葛歡給展示著存在手機里的備份,里面幾乎都是各植與,以及民生百態。
從照片來看,甚至去非洲大草原拍了大遷徙。
“你很勇敢。”談聽瑟怔怔道,角出一點笑意。
“不算什麼。”葛歡似乎被的眼神和笑容弄得有點不好意思,捂了捂臉又擺擺手,“那你呢?一個人來旅游嗎?你看上去年紀好像不大。”
談聽瑟目微黯,笑容卻更明顯了一點,“嗯,一個人。我還在念大學。”
“我還以為你是明星呢!”葛歡笑著夸贊,沒有刨究底揭人傷疤,“真的,你的氣質很特別,不然為什麼大家總在看你?”
Advertisement
“可能……因為我是學跳舞的吧?”
“我就知道!雖然你看著很瘦,但是手臂的線條很漂亮。你學的什麼舞種,大概學了多久?”
“芭蕾。有十六年了吧。”
葛歡啞然,最后豎了個大拇指,“太厲害了。我小的時候也喜歡跳舞,天天看電視上那些人表演,可惜我吃不了那種苦,所以只能放棄。真佩服你。”
聽到后半句,談聽瑟原本微僵的神漸漸緩和,變得。
“不,以前……平時我只需要完努力跳舞這一件事就行了,就像活在象牙塔里,不懂事的時候那些煩惱都是無病.。你做到的,才是更多人忍不了的辛苦。”
“話可不能這麼說。辛苦不是用來比較的,相對幸福的那一群人也依然有煩惱與痛苦的權利。不然只有世界上最苦的那個人才能說自己痛苦了,可誰又是過得最苦的那個人呢?”
看怔怔的,葛歡停頓片刻后又道:“就像我們不能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人于水深火熱之中,就剝奪其他人幸福的資格。不要對自己有太高的要求,我們都只是渺小的人類,擁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只都沒有不同。”
談聽瑟恍惚地著海面,無意識地點了點頭,“如果我也能活得像你這麼通就好了。”
“你年紀還這麼小,早早看一切還有什麼意思?人生中大多的彩都是在懵懂昏頭的時候得到的。”葛歡搖頭笑了,“我自己的生活也是馬馬虎虎,只不過這幾年見的多了,才有了一點悟。”
包裹著膛的泥土像被一只手撥開,翻出了那顆瑟在厚重掩埋下、微弱跳的心臟。
談聽瑟微微揚起下頜,任海風吹過來,將溢滿淚水的眼眶吹得發涼。
等淚水干,轉頭對著葛歡笑了笑,“謝謝你愿意和我說這麼多。”
“我們才認識多久,你已經對我說了好幾個謝謝了。”葛歡失笑,隨即又壞笑著托住下,“要是真想謝謝我的話,那就個朋友吧?”
……
讓一個習慣為生活的一部分需要很久很久,相應的,要放下它也需要很久。
談聽瑟自記事以來第一次這麼長時間沒有跳舞,甚至連舞鞋的袋子都沒有打開,一直把它單獨放在行李箱的角落里。
也許在這段旅程開始前就清楚自己這些日子不會再跳,但還是毫不猶豫地帶上了舞鞋。
或許是因為現在只有它了吧。
但每晚都因為沒有練習而焦慮到失眠,即便開始旅行之后這種焦慮也沒能緩解。每當這種時候就會陷迷茫,不清楚自己一時沖離開松城的意義是什麼。
想逃避痛苦,但是一切痛苦都沒有減半分,甚至會在夜晚變本加厲地襲來。
于是每天都學著去放空自己,也不和旅途中遇見的人有過多的接,因為不打算和他們建立深的聯系。
但談聽瑟沒想到自己會遇見葛歡。
過去沒有什麼心的朋友,也沒遇見過葛歡這樣的人,在素不相識的時候就能用自己熱烈的心去釋放善意。
再多名利場里往來的技巧,也比不上一個真心的字眼更能拉近距離。
葛歡的那個男同伴蔣力,然而卻并不是什麼“毫無共同語言”的同事關系,他們結伴去過很多地方,甚至還一起遭遇過幾次危險,不過最后都化險為夷。
兩人都很健談,很快就和悉了起來,給講了許多過去的經歷。
談聽瑟這才知道他們不僅拍攝各種圖像和視頻提供給雜志社,還會組織慈善活、參與義工隊伍,救助的對象有人也有各種。
忽然覺得自己曾經參加過的一些慈善活很可笑,甚至不好意思在葛歡跟蔣力面前提起半個字。
游抵達加拉帕戈斯群島以后,他們三個一起停留了一周的時間。島嶼“與世隔絕”的天然景與珍奇讓它像一個伊甸園,時的流逝變得無關要。
談聽瑟塵封起那些不必要的,只調最簡單的聽覺、嗅覺、覺、味覺與視覺去知和記憶這個世界。
“離島之后,你們準備去哪里?”某個夜晚,毫無儀態可言地坐在沙灘上,旁邊是直接躺得橫七豎八的葛歡與蔣力。
“我跟蔣力好了一條菲律賓的航線,這個不對大眾游客開放的。”葛歡緩緩道,“拍一拍瀕危的海鳥,再跟當地一起做一些保護活,最后撰寫稿件發布出去。但愿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吧,我們也只能做這些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16 章
傅先生,別來無恙
"三年前她九死一生的從產房出來,扔下剛出生的兒子和一紙離婚協議黯然離開,三年後薄情前夫帶著軟糯萌寶找上門……傅雲深:"放你任性了三年,也該鬧夠了,晚晚,你該回來了!"慕安晚冷笑,關門……"媽咪,你是不是不喜歡我!"軟糯萌寶拽著她的袖子可憐兮兮的擠著眼淚,慕安晚握著門把手的手一鬆……*整個江城的人都道盛景總裁傅雲深被一個女人勾的瘋魔了,不僅替她養兒子,還為了她將未婚妻的父親送進了監獄。流言蜚語,議論紛紛,傅大總裁巋然不動,那一向清冷的眸裡在看向女人的背影時帶著化不開的柔情。"晚晚,你儘管向前走,我會為你斬掉前方所有的荊棘,為你鋪一條平平坦坦的道路,讓你一步一步走到最高處。""
152.3萬字8 2967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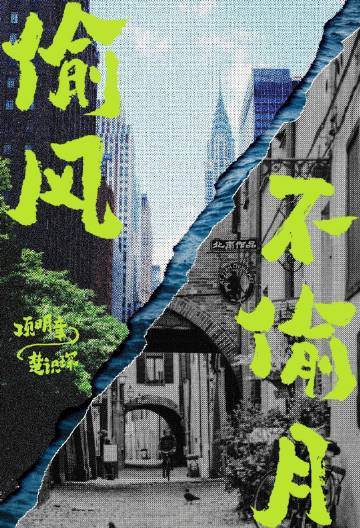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420 章

莫少逼婚,新妻難招架
沈南喬成功嫁給了莫北丞,婚後,兩人相敬如冰。 他憎惡她,討厭她,夜不歸宿,卻又在她受人欺辱時將她護在身後,「沈南喬,你是不是有病?我給你莫家三少夫人的頭銜,是讓你頂著被這群不三不四的人欺負的?」 直到真相揭開。 莫北丞猩紅著眼睛,將她抵在陽臺的護欄上,「沈南喬,這就是你當初設計嫁給我的理由?」 這個女人,不愛他,不愛錢,不愛他的身份給她帶來的光環和便意。 他一直疑惑,為什麼要非他不嫁。 莫北丞想,自己一定是瘋了,才會在這種時候,還想聽她的解釋,聽她道歉,聽她軟軟的叫自己『三哥』。 然而,沈南喬只一臉平靜的道:「sorry,我們離婚吧」
108.5萬字8 44387 -
完結211 章

重逢大佬紅了眼,吻纏她,說情話
那年裴京墨像一場甜蜜風暴強勢攻陷了許南音的身體和心。 浪蕩不羈的豪門貴公子放下身段,寵她入骨,她亦瘋狂迷戀他。毫無預兆收到他和另一個女人的訂婚帖,她才知道自己多好騙…… 四年後再重逢,清貴俊美的男人將她壓在牆上,眼尾泛了紅,熱吻如密網落下。 許南音冷漠推開他,“我老公要來了,接我回家奶孩子。” “?”男人狠揉眉心,薄紅的唇再次欺近:“奶什麼?嗯?” 沒人相信裴京墨愛她,包括她自己。 直到那場轟動全城的求婚儀式,震撼所有人,一夜之間,他們領了證,裴公子將名下數百億資產全部轉給了她。 許南音看著手邊的紅本本和巨額財產清單,陷入沉思。 某天無意中看到他舊手機給她發的簡訊:“心肝,我快病入膏肓了,除了你,找不到解藥。你在哪裡?求你回來。”她紅了眼眶。 後來她才明白,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著多濃烈的愛和真心。 他愛了她十年,只愛她。
38.8萬字8.33 6925 -
完結105 章

被讀心后,她發瘋創飛所有人!
溫馨提示:女主真的又瘋又癲!接受不了的,切勿觀看!(全文已完結)【微搞笑+玩梗+系統+無cp+讀心術+一心求死“瘋癲”又“兇殘”女主+火葬場+發瘋文學】 她,盛清筱一心求死的擺爛少女,有朝一日即將得償所愿,卻被傻逼系統綁定,穿越進小說世界! 一絲Q死咪?是統否? 強行綁定是吧?無所謂,我會擺爛! 盛清筱決心擺爛,遠離劇情,研究自殺的101種辦法,系統卻不干了,又是開金手指讀心術,又是給她回檔! 很好! 既然如此,那大家都別活了! 果斷發瘋創飛所有人,上演現實版的皇帝登基! 后來,幡然醒悟的家人分分祈求少女不要死! 對此,盛清筱表示:關我屁事! 死局無解,救贖無用,唯有死亡! 最想活的系統綁定最想死的宿主,開局則死局! 【女主一款精神極不穩定的小瘋子,永遠不按套路出牌,隨心所欲,瘋癲至極,一心求死最終得償所愿!】 本小說是在作者精神狀態極度不穩定下所創造出來的癲文,沒有邏輯,就是癲。 *回檔很重要
19萬字8 60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