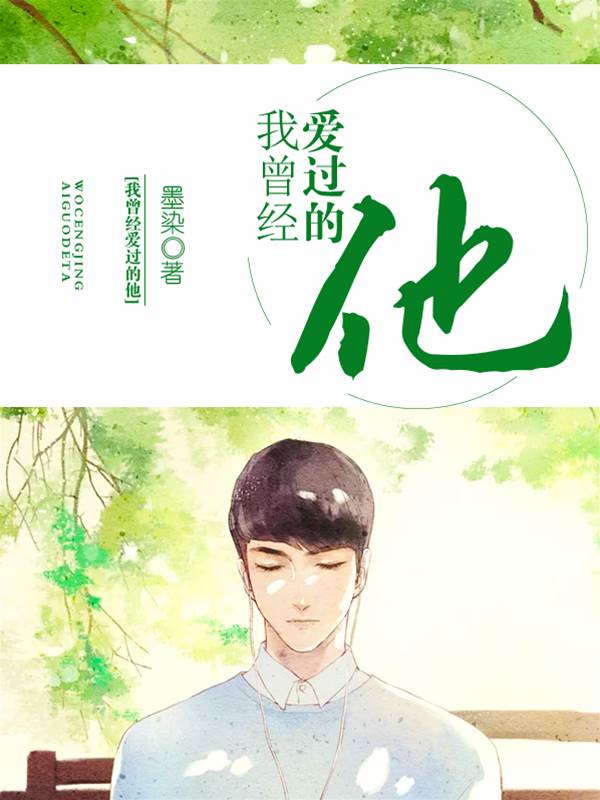《黑白》 第5節
認識他的時候,吃盡了這種苦,最後實在是怕了他了,終於忍不住去問一直跟在唐易邊做事的謙人:你家易……到底是個什麽格的人啊?
謙人的回答非常言簡意賅:紀小姐,您隻要記得,他笑的時候不見得是高興,他冷著一張臉的時候不見得是在生氣。
紀以寧非常聰明地舉一反三:就是說全部倒過來逆向思維就對了?
謙人彬彬有禮道:也不是,有時也是符合正向思維的,對易這個人,您隻能問題分析。
……
問了等於白問。
問題分析。
嗬,談何容易。
一切都將失去深度分析的重量,如果他不。
紀以寧歎了口氣,冷不防看見他的手指正在左上方。
這個作不是不挑逗意味的,但任何作,隻要由他做出來,哪個還會單純呢?
紀以寧沒有想歪,而是忽然很歉然的出聲。
“這個傷疤……不好看,是不是?”
是的,這是上唯一的傷痕。
左上方五公分,有一個十字形傷疤,就像耶穌背負的十字架,深深留在這本該完無瑕的上。
這是那場紀宅大火留在上的唯一印記。
他能夠從火場中把救下,卻沒辦法抹掉上已經留下的印記。
他常常凝視上的這個傷口,表專注得幾近人,好像不單是在看一個傷痕,而是在看一段時,一個無人可的。這種專注,幾乎讓錯覺他對的亦是深重的。
唐易忽然出聲。
“過幾天,國醫學界的幾位專家會過來,我讓他們幫你看看。”
紀以寧下意識地點頭。
其實,想,這又何必呢。
連其軒都勸過,以寧,你這是重度燒傷,想要一點痕跡都沒有,在不做手的況下是不可能的。
Advertisement
隻有他不聽勸。
這兩年來,他從不曾放棄找人醫治上的這一個傷痕,徹底讓見識到了他格中的固執。
哦,或許不是。
他對的固執,早在剛認識他的時候,就已經見過了三分。
兩年前,邵其軒在醫院為剛轉醒的治療上的燒傷。其他的地方自然沒有問題,可是最後這一個地方實在棘手。
邵其軒是醫生,於工作狀態自然不會有其他不該有的想法,下意識地就口而出:“紀小姐,請一下。”
還沒反應過來,就隻聽得站在一旁的唐易忽然邦邦地甩出三個字:“不準。”
其軒轉,莫名其妙地看著這個男人:“不我怎麽治?”
唐易冷冰冰地看著他:“我管你怎麽治,總之不準。”
“……”
邵其軒滿頭黑線:哦,又不準,又要他治,大爺你這是想我怎樣啊?他是醫生,又不是超人。
其軒決定不理他,轉對鼓勵道:“別去管唐易那個變態,我們治我們的。”
邵其軒敢這麽無視唐易的存在,紀以寧可不敢。他說了不準,就不敢了。
其軒實在沒辦法了,隻能親自手去解的扣。
結果那一天,救死扶傷的邵醫生差點被唐易一槍了頭。
其軒再好的脾氣也怒了,拍案而起直吼了一句:“唐易!你當老子沒人是吧?!”他又不是不要命了,誰敢對這位唐大爺的人存非分之想啊。
最後,還是唐勁上前把這位難搞的病人家屬拉走了。
……
如今想起那些往事,紀以寧竟有些懷念。
有傷固然不好。尤其是在部這麽私的地方。為人,每次洗澡後,無意看見鏡子裏的自己,總會下意識地把目避開那一。
Advertisement
莫名地就覺得對他到抱歉。既然已經了唐太太,對他總是有不同的的。
像他那樣的男人,一看就知道是閱盡春的,多人如玉從他眼前過,到頭來,他卻獨獨不放這一個並不完的人。
但擁有這個缺陷,也不是不慶幸的。
它讓看見了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唐易。
紀以寧忍不住開口:“其實,我沒關係的。好看不好看,都是自己的……”
唐易沒有應聲。
隻是定定地看著的口,手指從傷口過。
半晌,隻聽得他間輕聲出一句話。
“……孩子上有傷,始終不好。”
聞言,緩緩抬頭,對上他的眼。
唐易微微笑了下。
“就算父母不為你覺得委屈,朋友不為你覺得委屈,你自己始終還是委屈的。”
每次做 的時候都會下意識地抬手捂住這一個缺陷,不想讓他看見;每次洗完澡,都沒有往鏡子看的習慣,非要穿上服,才會朝裏麵看一眼。這一切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裏。
唐易俯,薄輕吻過口那一個灰的傷痕。然後他抬頭,看著的眼,緩緩開口。
“你心裏的委屈,不管是誰給的,都由我來負責。”
紀以寧看著他,竟覺得嚨口發不出聲音。
忽然就想到兩年前和唐勁的一次對話。那時剛為唐太太,很怕唐易,整個唐家隻敢和唐勁說話。
對唐易,不是不好奇的。
“他有人嗎?”
“他沒有。”
“啊……”毫無心機地歎:“他不像是缺人的男人……”
“他的確不缺,可是他從不給人任何機會。”
“為什麽?”
唐勁笑了。
“以寧,唐易是好人,”唐勁看著,溫地告訴:“……像他那樣的男人,若是給某個子機會,便再也逃不掉了。”
Advertisement
當時,聽得似懂非懂。直到兩年後的現在,紀以寧方才覺得唐勁的話裏有無窮智慧。
至今為止,唐易,隻給過紀以寧機會。
於是,隻有知道,他的多與眷顧,原來,竟可以到這個地步。
紀以寧忽然抬手,摟住他的頸項,抱住他。
“下星期有空嗎?”
年末,是他最忙的時候。
不等他回答,搶先一步開口央求:“下星期是過年,你回來陪我吧……”
他想了想,淡淡道:“下星期你要準備和國的醫生專家見麵。”
“我不想看了,”埋首在他頸窩,固執著剛才的請求:“你回來陪我吧……”
從不這麽對他撒的。
隻此一次,殺傷力無窮。
唐易抱著,聽到自己說了一個字:“……好。”
紀以寧頓時就笑了。
這世上最好的止疼藥,其實是他的溫。
比任何醫生良藥都管用。
小貓&唐勁
■思■兔■在■線■閱■讀■
歲末最後幾日,蘇小貓纏住唐勁不放,整天像隻勤勞的小蜂一樣圍著他轉,再加上這家夥的作息時間和正常人不太一樣,睡得比小姐都晚,起得比都早,於是隻要清醒著,就賴著唐勁不放。
唐勁實在被纏怕了,最後隻能把抱到自己上坐好,掏出一張空白支票。
“要多,自己填。”
沒錯,能讓蘇小貓如此熱洋溢的理由隻有一個:要發歲錢……
小貓樂滋滋地填好一大串數字,一點也不客氣地把支票攤到他麵前,笑容很狗:“要簽字……”
“……”
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蘇小貓的臉皮厚度越來越呈現一種質的飛躍狀態,遇到這麽一塊牛皮糖,唐勁還真就拿沒辦法。
Advertisement
唐勁接過支票,順手朝腦門上敲了一下:“我平時窮到你了麽?”
“當然不是啦,”小貓抱著腦袋笑:“怕你用不掉嘛,我幫你用啊……”
唐勁脾氣好,也不管在一邊胡說八道,在支票上簽完字,遞給。
“今年想怎麽過年?”
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往年都會拉上一大幫同事好友在家裏殺上一整晚,通宵個整夜。還好唐勁這個人無論在格耐心層麵還是質財力方麵都足夠強大,這麽鬧騰他也不大管,開心就好。
聽到唐勁這麽問,小貓想了想,像是想到了什麽,激地抱著唐勁道:“今年我們和寧寧一起過年吧!”
一聽到這話,唐勁挑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似笑非笑地看著:“你不懷疑我跟有一了?”
小貓頓時就采取打死都不承認的態度:“俺木有!木有!”
沒錯,蘇小貓對紀以寧的態度,可是經過了一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矛盾運的。
兩年前,唐易一句話就強搶了民,良為妻(= =)。紀以寧嫁給他以後,問題來了。唐易這個人,從來都是喜怒不形於,讓人無從下手。再加上唐易不是唐勁,沒有唐勁那種‘月之下傾聽心事’的好耐心,於是紀以寧在剛認識他的那段日子裏,兩個人的對話基本於這種狀態——
唐易:“你去睡覺。”
紀以寧:“恩……”
十分鍾後。
唐易:“怎麽還沒睡?”
紀以寧:“睡不著……”
唐易:“睡不著也睡。”
紀以寧:“……”
基於此,大家可以想象,在和整個唐家的人全然無法通的況下,忽然出現了唐勁這麽一枚脾氣好格好守好的三好男人,對紀以寧來說是多麽欣的事。那就是希啊,是最後一救命稻草啊。
於是,每當紀以寧彷徨無措的時候,就隻敢對唐勁傾訴。
紀以寧從小練得好修養,給唐勁打電話也是懂得挑時間的。白天唐勁忙,行電話基本都由助理接聽,紀以寧不好意思打擾他,於是就挑晚上的時間打給他。當然,不會是深夜,知道唐勁是有家室的男人,深更半夜打給他的話讓他太太怎麽想。
紀以寧顧慮左右之後,每次都是傍晚打電話。這個時間最好,剛吃過晚飯,他也會有時間,亦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紀以寧千算萬算,隻算錯了一件事。唐勁家的蘇小貓不是普通人,思維異於常人,於是連帶著行為作風也一並和普通的地球人不一樣。
普通人家吃過晚飯,就是洗洗刷刷看看電視,蘇小貓不是。
甚至不會好好吃飯,運……
這個運,當然不是指跑步打球之類的育運。
很纏唐勁,尤其是在家裏。撲之,抱之,蹭之,啃之,無所不用其極。唐勁不了這種明目張膽的引,往往一狠心就把按倒了事。夫妻嘛,膩在一起不運才奇怪。
於是,就在這兩人火熱做著的時候,紀以寧的電話來了……
可以想象,連續好幾次在和唐勁叉叉圈圈的時候忽然被一個人的電話打斷,蘇小貓的心有多不爽。
唐勁做了個手勢向解釋:“唐易的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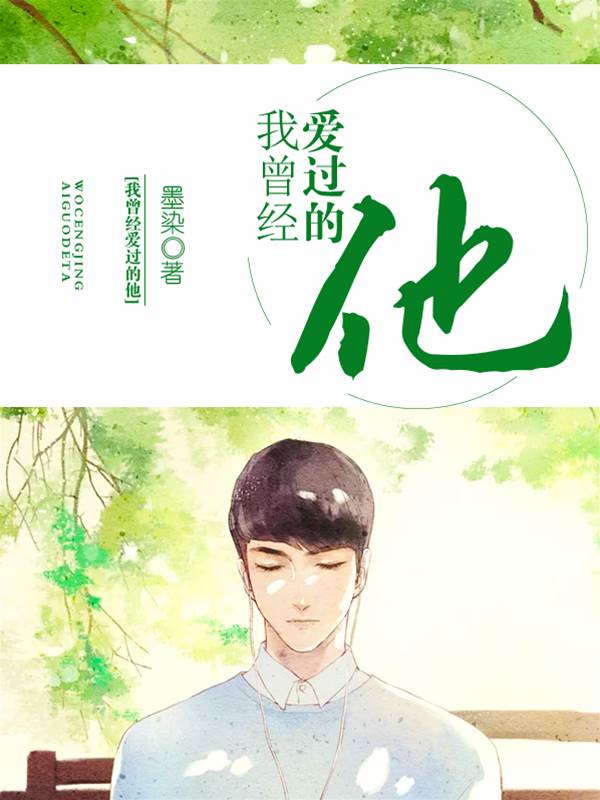
我曾經愛過的他
我為了躲避相親從飯局上溜走,以為可以躲過一劫,誰知竟然終究還是遇上我那所謂的未婚夫!可笑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卻隻有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新婚之日我才發現他就是我的丈夫,被欺騙的感覺讓我痛苦,他卻說會永遠愛我......
33.5萬字8 10343 -
完結1751 章

傅爺,你的替嫁新娘是大佬
一場陰謀,她從精神病院出來替嫁給名震全球的傅家二少沖喜。傅西洲娶了個神經病做夫人,全國人都等著看笑話。廢柴傻子?金麟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變化龍!她妙手回春、打臉虐渣、馬甲富可敵國!濱城名媛千金們紅腫著臉哭著找傅二爺告狀。傅西洲揚言:“我那嬌妻柔弱不能自理。”眾名媛:!?“爺,夫人把盛家砸了,還在盛家養豬!”“隨便砸,讓她養。”“爺,夫人出逃了!”傅西洲帶著萌娃將她堵在機場的墻角:“家里鍵盤被我跪壞了,乖乖,再買個。”顧北笙驚愕的看著她的翻版小女娃和他的翻版小男娃。她什麼時候給他生孩子了?
239.9萬字8.18 227017 -
完結627 章

膚淺關係
27歲的舒菀,始終期盼婚姻,忽然有一天她發現,新上司看她的眼神越來越不對了。新上司白天一本正經,晚上露出獠牙。
104.8萬字8 69432 -
完結185 章

驚春暴雪
李羨被親生父母接回家,第一件事是聯姻。 新婚丈夫是孟家現任話事人,身份貴重,鮮少露面。 市井街頭活了二十五年,婚後李羨也沒放棄記者工作,連夜奔走憔悴黯淡,常爲五斗米折腰,與同場茶話會的貴婦們泥雲之別。 某天閒來無事給花園翻土,不經意回頭,發現有人在亭下喝茶,動作慢條斯理。 細雪微茫中,李羨蜷了蜷沾滿泥濘的手指,問孟先生留下來吃晚餐嗎? 管家禮貌回答:孟先生稍後就走,晚餐請太太自便。 那天她忽然想起第一回見面。 包廂門開了一線,坐在裏面的人被簇擁追捧,忽偏頭看過來,擡頜,微微闔眸。 李羨身旁有人慾言又止,說這位是孟恪。 門縫掩映着,裏面的人帶着與生俱來的居高臨下的凝視感。 無人知曉這樣清貴傲倨的人,有一天也會爲她漏夜趕路。 肩頭覆薄雪,褲腳沾溼泥,他嗓音倦怠,說聯姻是聯姻,你是你。 “我既然拿得起。” “就沒想過放下。” - 我是無邊暴雪。 如果你看向我,我會輕柔地消融。
26萬字8 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