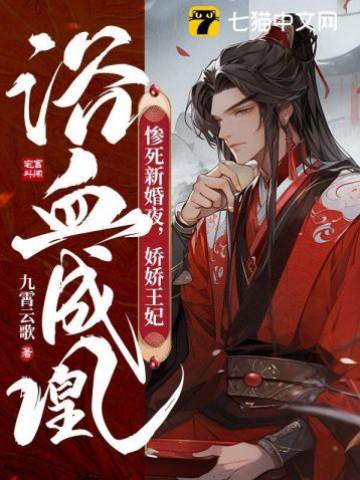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騙婚禦史大人後跑路了》 第10章 潛相隨 “您最懂禮法了,那您教教我呀……
第10章 潛相隨 “您最懂禮法了,那您教教我呀……
三月的最後一日,曉霧空蒙,柳風吹面微寒。
沈宜棠起了一個大早,命府裏車夫套上馬車,向郊外的落霞山行去。
馬車轔轔地踏在道上,沈宜棠和小桃在車裏睡得東倒西歪,飽眠近一個時辰,睜眼已在落霞山山腳。
落霞山綿延近百裏,數峰姿態各異,濃翠如洗。山路難行,不論來人游山還是拜佛,基本只會去玉福寺所在的主峰。主峰不陡不險,砌有石階闌幹,弱的小娘子也能拾級而上。
凝翠苑就修在主峰半山腰,數間軒榭星散在溪林裏,是給客人準備的休憩之所。
山腳停駐著寥寥幾架馬車,今日來客不多。
沈宜棠跳下馬車,和小桃走了一刻功夫的石級路,來到玉福寺。對于神佛,沈宜棠以前裝神弄鬼的時候不怎麽信,但進大雄寶殿,佛祖面前一跪,再離經叛道也虔誠。
念念有詞,“求佛祖保佑我任務功,晏元昭對我神魂顛倒,乖乖奉上他的,讓我賺大錢發大財,領一個小倌館的俏郎君回家。”
說完,認認真真磕了三個頭。
小桃也在上香許願,沈宜棠湊過去聽,小桃求的是“信希再見一面心上的小郎君”。
“誰啊誰啊?”沈宜棠賊笑著問。
小桃半個字也不說,沈宜棠只得作罷。請完用來差的姻緣符和求子符,沈宜棠順手揣懷裏,兩人原路返回馬車。
離巳正還有一會兒,沈宜棠在馬車裏補了補妝,換上絳紅羅金縷,搭雲山藍坦領半臂,腳穿月白綴珠履。
還難得綰起飛仙髻,用青黛勾出纖纖初月眉,抹了石榴口脂。
行走江湖慣扮男子或道士,進沈府後也是草草妝扮,如此按貴份打扮一番,連小桃都看呆了。
Advertisement
“你要是留在春風樓,高低能爭個前五。”小桃道。
沈宜棠自得,“要當就當頭牌。”
“你當不了,”小桃手指前微聳的小山包,“你這兒不夠。”
沈宜棠悻悻勒羅系帶。
時間差不多了。為求低調,沈宜棠戴上帷帽,小桃手提兩個包裹,兩人沿著與剛才相反方向的山路,步向凝翠苑。
沈宜棠這裝束走不快,爬到半山腰用去小半時辰,腳底已硌得發痛了。
離凝萃苑還有百步,不知在哪裏的秋明突然竄到兩人眼前。
“沈娘子?”他試探。
“是我。”沈宜棠應道。
秋明松口氣,不敢直視,“跟我來。”
他將兩人引至一間門窗閉的軒楹,沈宜棠帶著小桃推門進去,晏元昭坐在案幾前手捧書卷,聽到聲音頭也未擡。
沈宜棠走到案前,晏元昭棄卷,擡眼看看小桃。
小桃了腦袋,沈宜棠道:“小桃,你在外面等我。”
小桃把手裏包裹放到地上,出去了。
晏元昭這才正眼看沈宜棠。
帷帽的薄紗垂在細頸兩側,小紅痣似非。沈宜棠飾繁複,舉止輕而緩,頗有弱質纖纖之態。
“晏大人,咱們又見面啦。”沈宜棠摘下帷帽,優雅一笑,那笑在額心花鈿和上點朱的襯托下格外明豔。
晏元昭毫無意識地皺了眉。
不像。
掩在帷帽下的怯郎,盛裝打扮的名門貴,都給他一種格格不的陌生。
晏元昭聲音平平,“沈娘子,我要的東西呢?”
沈宜棠也學著他那樣跪坐在案前,“晏大人,別急嘛,我爬了好一路山上來,總要先讓我喝口水吧?”
案上有茶,沈宜棠自力更生,給自己倒了杯茶。
茶裏映著晏元昭鋒銳的眉眼。
沈宜棠放下茶杯,慢吞吞地打開地上包裹,將布帛包住的琴譜放到案上。
Advertisement
“給您。”
晏元昭取出琴譜,靜靜地看著封面上的墨字,神冷滯。
沈宜棠不敢擾他,啜飲著茶水默默欣賞今日的晏郎君。他著大袖青衫,束木冠,挽半髻,留大多數頭發垂在肩後,不像嚴肅的青年員,倒像是瀟灑俊逸的士。
好看是好看,可怎麽戴個木簪子呢,上也沒佩點兒金銀。
今天的晏史好不值錢。
半晌,晏元昭將布帛合上,喚醒看著他發呆的小郎,“多謝。”
“您看封皮,不翻開確認一下麽?”
“不必了,這就是晏某的琴譜。沈娘子,府上是否還有別的琴譜?”
沈宜棠遲疑,“別的?”
“或許,有家父的。”晏元昭緩緩道。
沈宜棠為難,“我是偶然從父親的一個書箱裏看到的,別的沒注意。我可以再想辦法去翻一下。”
“……算了,你越矩的事還是做。沈娘子,此為你送琴譜的謝禮。”晏元昭拿出一無蓋木匣,匣裏躺著一顆明亮的琉璃珠,閃著熠熠彩。
沈宜棠一眼判斷出這珠子價值,忍不住咽口口水。
“我不能收,給您琴譜是舉手之勞,談何謝字。”
忍痛將匣子推回去。
他上有更大的價值供圖謀,怎能他用顆珠子平了人?
晏元昭沒再堅持,眼裏浮出了然,好似早料到會推拒。
“其實,除了琴譜,我還給您帶了東西。”沈宜棠歡快地指指小桃提來的兩包什。
“晏某不收禮,你還是拿回——”晏元昭在看到拿出的東西時,聲音戛然而止。
是一只布制的金胖頭魚,魚胖的不得了,魚尾短短的,怪可。
沈宜棠獻寶般一樣樣掏出來。
大小不一的線球,灰撲撲的長尾小老鼠,胖乎乎的黃小鳥……
晏元昭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表了。
Advertisement
沈宜棠揪著小灰鼠的繩尾沖著晏元昭晃了晃,“不是送您的,是給府上貓咪的。晏大人平時忙公務,梨茸肯定很寂寞,需要些小玩意兒打發時間。”
晏元昭拿起胖頭魚,魚鰭上有個開口,他往裏一掏,出只小一號的胖頭魚。
沈宜棠:“驚喜吧?”
晏元昭:“……”
沈宜棠嘿嘿笑,“還有給梨茸準備的四季裳,我就不拿出來了。都是丫鬟隨便做的,不值錢,您就收下吧。”
房裏丫鬟以為是給宋蓁兒準備的,制得格外用心。
晏元昭從小一號胖頭魚裏出迷你胖頭魚,反思自己到底還是對梨茸不夠上心,沒考慮過這些。
收下這些玩,好像也不算太越禮。
如果他不收,拿回去也沒用,估計就扔掉了,太浪費。
這幾只魚,梨茸估計會喜歡。布老鼠就算了,梨茸這輩子都沒見過真老鼠,假老鼠也不必見。
“多謝。”晏元昭道。
沈宜棠反應了一會兒才意識到這是收下的意思,忙把東西斂起放到包裹裏,帶笑道:“不謝不謝,希梨茸會喜歡,哎要是我能見到梨茸就好了,聽說很漂亮呢。”
晏元昭看一眼,“梨茸怕生。”
竟然沒明著拒絕?沈宜棠笑意更盛,“我理解,貓貓都是怕生的。”
晏元昭吹了口茶沫,沈家小娘子,任不假,脾氣也是真的好啊。
他放下茶,“沈娘子,晏某還有事要做,就不奉陪了。”說著便喚白羽進來,吩咐他派人將包裹送到山下馬車。
沈宜棠以手撐臉,“晏大人,您還要去做什麽?方便的話,我能和您一起嗎?”
“登山冶游,賞景騁懷。”晏元昭挑眉,“你今日的鞋履,能爬得山麽?”
“能爬能爬,不是問題。晏大人,您帶上我唄,我還能和您解悶呢。”
Advertisement
晏元昭好整以暇地看了一會兒,忽然輕輕地笑了。
沈宜棠以為說他,眼地隔案湊近,卻聽晏元昭道:“別逞能。沈娘子,你要一直這樣恣意妄為,視規矩禮法為無,早晚會栽個大跟頭。”
沈宜棠失落,“您最懂禮法了,那您教教我呀……”
奈何晏元昭郎心如鐵,不管沈宜棠如何說,還是與在凝翠苑門口分了道。
山裏雲氣繚繞,嵐煙漠漠,晏元昭提踏履,走得毫不猶豫。
小桃看著一行人遠去的影,對沈宜棠道:“知足吧,我還以為他不會收咱們準備的東西。”
“不行,不能就這麽回去。落霞山又不是他家開的,他能登山賞景,咱們也能。”沈宜棠摘下頭上叮咣響的步搖,起擺,“咱們悄悄跟著他。”
幾乎是前後腳,一位著栗錦袍的貴人步凝翠苑的另一間軒榭,他上沒有佩飾,但倘若沈宜棠在,立時便能看出他上裳的料子昂貴非常,價值不輸金銀。
軒已有一男子當窗坐著,見到人來,欠微笑,“太子殿下。”
大周當今的儲君趙騫不客氣地坐下,雙臂架在後的坐靠上。他省去寒暄,開門見山,“你搞了一個賭坊?”
“正是。賭坊賺錢,一本萬利,金玉閣一月的進項就足敵一個縣全年的賦稅,誰能不眼紅。以後,我的賽寶樓掙得比金玉閣還要多。”
趙騫很興趣,“你開的時機很巧,正好趕上金玉閣出事被封。”
男子臉上浮出得意的笑,“不瞞殿下,金玉閣出事,正是在下手筆。我找了幾個潑皮許以重金,讓他們去砸場子,他們幹得不錯,捅死了個人,順理章地讓京兆尹查封金玉閣。過些天,就算金玉閣重新營業,生意也必定大不如前。”
“不錯。”趙騫贊許,“你這賽寶樓前景大好,孤也幾分。”
男子笑道:“在下也有此意。李綬被晏元昭整倒,殿下手頭進項張,正是在下效犬馬之勞的時候。賽寶樓有殿下庇佑,必定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我即刻派人去與您商洽事宜。”
“做得些,知道嗎?”
“這個自然,殿下放心。”
日頭偏移,窗外天漸暗,趙騫的眼眉覆上一層雲翳,他拈起中指,冷不丁發問,“那樣東西,拿回來了麽?”
男子道:“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趙騫的聲音陡然提高,“這都幾個月了?”
男子斟酌語句,“殿下也不用太心急,晏元昭既然選擇匿下那東西,或許就不會拿它做文章。”
“哼,孤要的是或許嗎?那東西一日在晏元昭手裏,孤就一日不得心安!”趙騫眼裏湧上戾氣,臉部的微。
男子不慌不忙,“我明白,只是您也知道,公主府圍牆高聳,守衛森嚴,明暗搶都不是法子。要想拿到,只能不走尋常路,所以要多費些功夫。”
趙騫忍下煩躁,勉強道:“孤信任你,這件事只能你辦,你可不要讓孤失。”
“一定不辱使命。”男子道。
趙騫與男子又說了幾句便起離開,男子著窗外的空濛,“殿下,天要下雨,您早些回宮。”
趙騫淡淡頷首,在兩個長隨的陪伴下匆匆走出凝翠苑。
男子站在凝翠苑的山崗,遙趙騫漸漸沒于山嵐裏的影,眉頭皺起。
趙騫走的不是下山的方向,如此急匆匆,他還要去做什麽?
……
沈宜棠與晏元昭拉開距離,躡手躡腳地潛隨其後。
晏元昭的游山路線很奇怪,起初還是沿著石級向上攀登主峰,走著走著就偏到無人走的小徑上,看方向,似是要穿到東峰。
山間霧重,水氣上人,沈宜棠單薄的裳漉漉的。涼意上湧,打了個哆嗦,卻將擺提得更高。小徑上泥土,已往素的履上濺了好幾個髒點子,金縷是在鋪子裏賃的,還得好模好樣地還回去,不能弄污。
林梢之上,雲悄然近。
一顆滾圓的水珠打到織的林葉上,白羽及時地從背上行囊裏出油紙傘撐開。
“主子,沈娘子一直在跟著咱們。”
一黑短打的秋明飛來相告。
沈娘子能耐不小,始終相隔甚遠地跟著他們。起初秋明以為也在游山,觀察一陣後才確定在尾隨。
“簡直胡鬧。”傘下的晏元昭沉聲道,“秋明,你過去和說,不許再跟了,帶下山。”
山雨從零星幾滴到砉然瓢潑,也就是一晃神的功夫。
枝搖葉,戰戰響。急雨裹挾嗖嗖冷風,撲面而來。
沈宜棠躲在山壁上一塊凸起的巖石下,冰涼的水珠順著脖頸淌進衫子裏。的金縷皮,又黏又沉。
片刻前,雨勢還未起來,小桃戴著沈宜棠的帷帽,沖下山去凝翠苑取傘和袍。
沈宜棠凍得瑟瑟發抖,惟願小桃快些回來。
——咔嚓,斷枝砸在頭頂巖上,石頭傳來松的聲音,沈宜棠嚇得忙邁出來兩步。
秋明踩著巖石跳下來,又把驚了一驚。
“秋明,好巧。”沈宜棠拍著心口,尷尬的笑容被雨水一沖即散。
秋明說得含蓄,“沈娘子,雨大,我送您下山。”
沈宜棠抹把臉,“不太行,小桃下山拿傘去了,我要是走了,回來找不到我。”
“那屬下陪您等。”
秋明摘下鬥笠,打算遞給,但左看右看都不知頭上高高的環髻該如何塞進鬥笠。
兩人面面相覷。
雨如麻,唰唰地往上落。雨簾籠在沈宜棠眼前,天地一片模糊。
吸了下鼻子,忽然察覺砸在上的雨點子停了。
一只紫竹傘撐在頭上。
執傘的手修長潔淨,骨節朗,伴著熨帖的淡淡墨香,離鼻尖不過幾寸。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7 章
首輔大人最寵妻
前世她是繼母養廢的嫡女,是夫家不喜的兒媳,是當朝首輔強占的繼室……說書的人指她毀了一代賢臣 重活一世,靜姝隻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卻不想因她送命的謝昭又來了 靜姝:我好怕,他是來報仇的嗎? 謝昭:你說呢?娘子~ 閱讀指南: 1.女主重生後開啟蘇爽模式,美美美、蘇蘇蘇 2.古代師生戀,男主做過女主先生,芝麻餡護犢子~ 3.其實是個甜寵文,複仇啥的,不存在的~ 入V公告:本文7月7日V,屆時三更,麼麼噠 佛係繼母養娃日常 ←←←←存稿新文,點擊左邊圖片穿越~ 文案: 阿玉穿成了靠下作手段上位的侯門繼室,周圍一群豺狼虎豹,閱儘晉江宅鬥文的阿玉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奈何,宅鬥太累,不如養包子~~ 錦陽侯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明明是本侯瞧不上的女人,怎麼反被她看不上了? 阿玉:不服?休書拿去! 侯爺:服……
52.4萬字8 32349 -
完結2123 章

醫妃獨寵俏夫君
21世紀的暗夜組織有個全能型殺手叫安雪棠,但她穿越了。穿越第一天就被賣給了一個殘障人士當妻子,傳聞那人不僅雙腿殘疾還兇殘暴戾。可作為聲控顏控的安雪棠一進門就被那人的聲音和俊美的容貌蠱惑住了。雙腿殘疾?冇事,我能治。中毒活不過半年?冇事,我能解。需要養個小包子?冇事,我養的起。想要當攝政王?冇事,我助你一臂之力。想要生個小包子?呃…那…那也不是不行。
363萬字8.5 1190101 -
完結134 章

棄婦覺醒后(雙重生)
前世蘭因是人人稱讚的好賢婦,最終卻落到一個被人冤枉偷情下堂的結局。 她被蕭業趕出家門,又被自己的家人棄之敝履,最後眼睜睜看著蕭業和她的妹妹雙宿雙飛,她卻葬身火場孤苦慘死。 重生回到嫁給蕭業的第三年,剛成為寡婦的顧情被蕭業領著帶回家,柔弱的女子哭哭啼啼, 而她那個從來冷漠寡言的丈夫急紅了眼,看著眼前這對男女,蘭因忽然覺得有些可笑,她所有的悲劇都是因為這一場不公平的婚姻。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了。 和離後的蘭因買宅子買鋪子,過得風生水起,反倒是蕭業逐漸覺得不習慣了, 可當他鼓起勇氣去找蘭因的時候,卻看到她跟朝中新貴齊豫白笑著走在一起。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蘭因居然也能笑得那麼明媚。 蘭因循規蹈矩從未對不起誰,真要說,不過是前世那個被冤枉跟她偷情的齊豫白, 他本來應該能走得更高,卻被她連累,沒想到和離後,她竟跟他慢慢相熟起來。 齊豫白冷清孤寂,可在黑夜中煢煢獨行的蘭因卻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久違的溫暖和疼愛, 他和她說,你不是不配得到愛,你只是以前沒有遇對人。 大理寺少卿齊豫白冷清克制,如寒山雪松、月下青竹,他是所有女郎心中的檀郎, 也是她們愛慕到不敢親近的對象,所有人都以為像他這樣的高嶺之花一輩子都不可能為女人折腰。 不想—— 某個雪日,眾人踏雪尋梅路過一處地方,還未看見梅花就瞧見了他與和離不久的顧蘭因站在一處, 大雪紛飛,他手中的傘傾了大半,雪落肩頭,他那雙涼薄冷清的眼中卻含著笑。 齊豫白活了兩輩子也暗戀了顧蘭因兩輩子。 這輩子,他既然握住了她的手,就再也不會鬆開。
59.3萬字8 47762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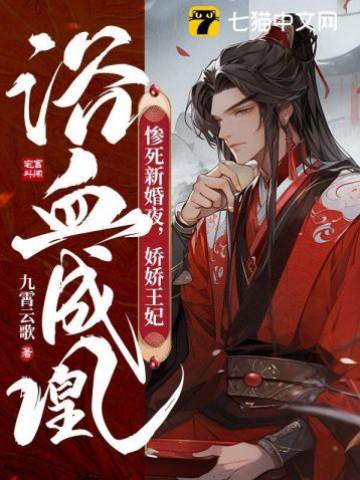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