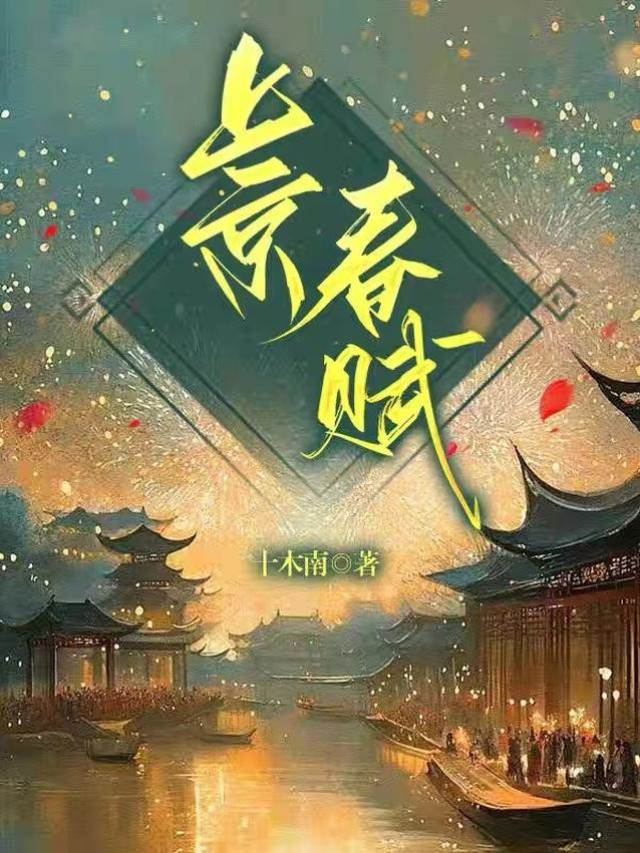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嫁給異族首領後》 第 26 章
第 26 章
巫醫滿頭大汗從殿中走出來,這才一陣陣後怕,剛剛王上雷霆之怒,哪怕要了他的腦袋,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
他剛剛用袖了汗,便聽得邊惻惻的聲。
“巫醫大人今日可有空閑?”
正是姜芙。
“我近日有些不適,若您方便的話,可否為我診脈?”姜芙盯著他,問。
“當然。”巫醫微微俯,便跟著姜芙一起走了。
這日午後,沈桑寧便收到了王上今晚要來的消息。
娜依解釋道:“王後,今夜是月圓之夜,按照慣例,王上是會來王後這兒的。”
沈桑寧:“明白了。”
來西涼已經兩月,上一個月圓之夜,人被蘇勒帶去了河西。出征在外,自然顧不上這等規矩。
當然,那幾日他們每天都在一起,到也不算破了慣例。
只是,近日蘇勒已經很久沒來了。
白日教授騎馬技,隨著逐漸練,蘇勒也不再和同乘一馬。
他騎著追風與并行,只留一人在逐雲的背上。
說起來,總覺得和他偶然的,比初來西涼時了許多。
娜依看已經聽明白了,又含笑道:“王後,以前的西涼首領大多都有數十位姬妾,月圓之夜時常不顧規矩,宿在姬妾而不顧王後,但現在,咱們王上只有您一個王後,您不必擔心他不來。”
沈桑寧點了點頭。
娜依來了興趣,便又哄道:“王後,看您和王上這麽親厚,應當早日懷個小孩子才是呀。”
青嬤嬤立在旁邊,看了一眼。
們三個由沈桑寧從玉京帶過來的婢嬤嬤,都知道沈桑寧并未真正意義上和王上圓房。
但娜依并不知道。
沈桑寧臉紅了,只想趕把這個話題岔過去,有些生地開口:“娜依,昨日教我的那些西涼話,我念給你聽聽。”
Advertisement
娜依暗想,果然大孟子害,這都嫁過來兩個月了,提起這事還會臉紅。
不像當年出嫁,一個月的時間便已從青轉為食髓知味,和丈夫整天胡鬧個沒完,直到後來懷了孩子才勉強消停。
“好好好,怪奴快,咱們不說這個了。”娜依翻開話本,“索現在王上只有您一人,想必很快就會有好消息的。”
晚上,蘇勒如約而來。
殿中的奴婢宮人都已經退了下去,殿只有沈桑寧一人,正在翻看一本醫書。
一盞燈亮在旁邊,燈罩中蠟燭影影綽綽,在的臉上也投下或明或暗的影子。
已經沐浴過,發梢還是的,也因此顯得更加烏黑,散著發,披在肩頭與腰背間,沒有用一釵。皮也并未著黛,像樹梢枝頭的梔子。
實在是一副好嫻靜的畫面,蘇勒邁過門檻的腳步放輕了些。
不過,沈桑寧已經注意到他來了,將醫書一收,站起來。
蘇勒掃一眼書的封面,千方,是一本在大孟很出名的醫書。據說記載了千種疾病和對應的藥方,容詳實全面,而且,實在是很厚的一本。
換言之,還適合消磨時間。
他知曉沈桑寧在這裏應該很無聊。
即便已經在努力融,但一是玉京公主的份,二是如今王後的地位,都在阻止著邊人朝敞開心扉。
與年紀相仿的......頓珠算是一個,還有古麗。
姜芙和海蘭雖也與年齡差不多,但蘇勒已經聽說了上次宴會上的事。
蘇勒暗自羅列了一番,愈羅列,愈覺得沈桑寧在此著實孤單。便決定還得傳信給法依則,讓古麗休時多過來。
上次去河西,看上去與古麗的關系還不錯。
沈桑寧見他不說話,不知在想什麽事,便問:“現在時間還早,王上現在要休息嗎?”
Advertisement
“陪你坐一會兒。”蘇勒道,“你可繼續看你的書,就當本王不在。”
沈桑寧微微笑了:“你在這,我怎麽可能做到當你不在。”
這話落在蘇勒心裏,激起了一番漣漪,仿佛出指尖,輕輕淺淺地在他心湖水面上點了點。
不知為何,他開口解釋道:“今日是月圓之夜,不同房不合規矩。”
“我就在這裏......不做什麽。”
沈桑寧聽出他竟是在認真解釋,詫異地歪了歪頭,又笑道:“我知道的。”
隨後,兩人便無話。
沈桑寧還是翻開了那本千方,就著剛剛沒看的位置繼續看下去。蘇勒起:“我去沐浴。”
很快便有宮人送來熱水,他將外裳解開留在外面,只著一素白裏便進去了。
裏頭傳來水聲,嘩嘩的,沈桑寧有點看不下去書了,挨了好一會兒,等到蘇勒出來。
沈桑寧看了他一眼,飛快地轉過眼來。
他皮是小麥,一顆水珠沿著分明的下頜線滾下來,正滴落在膛,留下一條曖昧的水跡,然後滾進襟不見了。
偏他好像渾然不覺的樣子,披上外衫。
沈桑寧:“......”
繼續低頭做看書狀。
直到蘇勒重新走回邊,疑的聲音從上方傳來:“剛剛我進去時,公主似乎就在看這一頁。”
沈桑寧:“......這頁,這頁的容以前母妃給我講過,我多看看。”
搬出母妃,倒是很快找到了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是嗎?”蘇勒顯然不相信,聲音帶著笑了。
沈桑寧這才低頭認真看書頁上的容,隨後,臉騰地紅了。
這一頁分為兩部分,上面半截是正常的為傷口消毒容,可下半截,竟然是——
治療...男子...舉而不堅...
Advertisement
沈桑寧啪的合上了書頁。
這書到底怎麽編的!
紅如滴的臉對上了蘇勒那一對笑意的金眸。
“沒想到,楚妃對公主的教育倒是很超前。”他還能繼續調侃。
“你,你不懂。”沈桑寧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謅了一個聽上去很正當的理由,“在醫家眼裏,生病就是生病,沒有別之分。”
“是是。”蘇勒笑,“公主有大醫風範,是我的問題。”
“不過,公主在我面前看看倒也罷了,若是被其他人看見,恐怕我的面子會丟得滿西涼都是。”
沈桑寧:“我不看了!睡覺。”
說完,徑直起,往床上躺去。
作間帶過一陣裊裊的風,混著沐浴後上的香氣。
蘇勒含笑看,當真是氣呼呼地側躺在床上,背對著他。
“公主?”他喚了一句。
沈桑寧不理。
“公主。”他走近,也上了床榻。
沈桑寧子了一下,還是沒說話。
“別生氣了。”他哄道,“今日是我不好。”
沈桑寧用被子蒙住了頭。
蘇勒無法,吹熄了床榻邊的蠟燭,躺了下來。
邊一陣窸窣聲,都在提醒今日,又與蘇勒同床共枕了。
只是剛剛討論過那樣的話題......
沈桑寧的手還是涼的,擡起來捂住了臉,試圖給臉降溫。
這小作自然被蘇勒盡收眼底,他怕加重沈桑寧的意,只得裝作沒看見。
也不敢和沈桑寧說,今日躺的位置不合適,有些太靠近自己了。
黑夜中,視覺被封閉,其餘的便更加敏銳。
蘇勒第三次試圖睡失敗,在黑夜中睜開了眼。
之前,上有這麽香的麽?
西域沒有這種氣味的熏香,他也從未在沈桑寧看到熏香的痕跡,所以,那香氣的來源便只剩下了一個。
Advertisement
一片黑暗裏,他得十分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的心猿意馬。
他時常自省,便能輕而易舉知曉自己的心意。
如今他極有好的郎就躺在側,一手就能到的距離,他的定力幾乎四散。
蘇勒開始數自己的呼吸。
好不容易將心跳平緩下來,沈桑寧已然睡著了。
蘇勒強迫自己想了一遍未解決的軍政大事,等到自己恢複了平常獨自眠的狀態,便闔上眼,打算第四次嘗試睡。
好巧不巧,了。
在他邊,沈桑寧睡覺總是不老實。
那就順其自然,仿佛天生契合一般,進了他的懷裏。
沈桑寧渾然不覺自己的行為,呼吸依舊是勻長的,沒醒。
靠近之後,香氣便顯得更加濃郁,如醴如蘭。有一縷烏發搔在他口,得很,從皮直往心口鑽。
子小,可以稱得上玲瓏有致,睡覺時是蜷的姿態,像貓兒,能被人一把抱住——
蘇勒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的手指了兩下,最後,他從背後摟住了的腰。
細腰的形狀是微微凹陷,如同小湖,蘇勒的右手能會到腰下隆起的形狀,但再也不敢往下。
呼吸的時候,細腰的也會隨之起伏,蘇勒能完全會到,不放過纖毫細節。逐漸的,他的呼吸也被相帶,融為一,以同樣的一個節奏,緩緩地脈。
懷中,沈桑寧含糊了一聲,蘇勒聽到了,竟是他的名字。
得實在不清不楚,但蘇勒偏偏能懂。
像是的回應,蘇勒心底的驚喜浮現上來,活在世上二十五載,竟也是第一次有這樣奇妙的會。
他心底似有一頭猛,被這一聲喚醒。
蘇勒生生制著,生怕野出籠,會嚇到。
他知曉沈桑寧初來西涼的幾日睡不太安穩,如今已能在他邊沉沉睡。
而這夜,一夜未眠的人變了他。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農門醫妃:妖孽王爺纏上門
天師世家第八十八代嫡傳弟子阮綿綿因情而死,死後穿越到大秦朝的阮家村。睜開眼恨不得再死一次。親爹趕考杳無音訊,親娘裝包子自私自利,繼奶陰險狠毒害她性命,還有一窩子極品親戚虎視眈眈等著吃她的肉。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姐弟三個過得豬狗不如。屋漏偏逢連陰雨,前世手到擒來的法術時靈時不靈,還好法術不靈空間湊。阮綿綿拍案而起,趕走極品,調教親娘,教導姐弟,走向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可是誰來告訴為什麼她路越走越寬,肚子卻越走越大? !到底是哪個混蛋給她下了種?桃花朵朵開,一二三四五。謊話一個個,越來越離譜。俊美皇商溫柔地說:那一夜月黑風高,你我有了魚水之歡。妖孽皇子驕...
32.6萬字7.73 30934 -
連載1973 章

3歲小萌寶:神醫娘親,又跑啦!
“娘親,你兒子掉啦!”小奶包抱緊她的大腿,妖孽美男將她壁咚在墻上:“娘子,聽說你不滿意我的十八般武藝?想跑?”沈云舒扶著腰,“你來試試!”“那今晚娘子在上。”“滾!”她本是華夏鬼手神醫、傭兵界的活閻王,一朝穿越成不受寵的廢物二小姐。叔嬸不疼,兄妹刁難,對手算計,她手握異寶,醫術絕代,煉丹奇才,怕個毛!美男來..
177.8萬字8 17475 -
連載1305 章

和離后毒妃帶三寶顛覆你江山
虐渣+追妻+雙潔+萌寶新時代女博士穿成了草包丑女王妃。大婚當天即下堂,她一怒之下燒了王府。五年后,她華麗歸來,不僅貌美如花,身邊還多了三只可愛的小豆丁。從此,渣男渣女被王妃虐的體無完膚,渣王爺還被三個小家伙炸了王府。他見到第一個男娃時,怒道“盛念念,這是你和別人生的?”盛念念瞥他“你有意見?”夜無淵心梗,突然一個女娃娃頭探出頭來,奶兇奶兇的道“壞爹爹,不許欺負娘親,否則不跟你好了,哼!”另一個女娃娃也冒出頭來“不跟娘親認錯,就不理你了,哼哼。”夜無淵登時跪下了,“娘子,我錯了……
231.7萬字8.18 9007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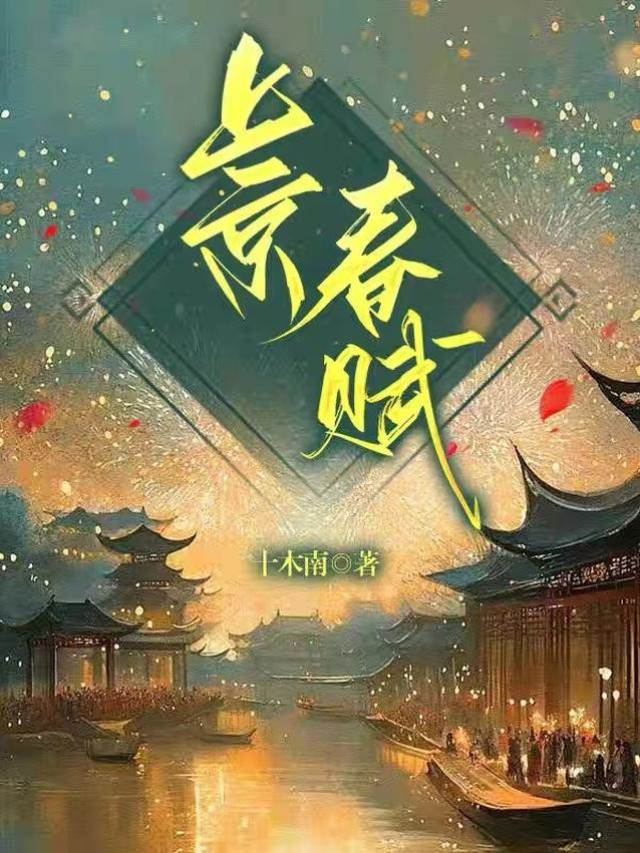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