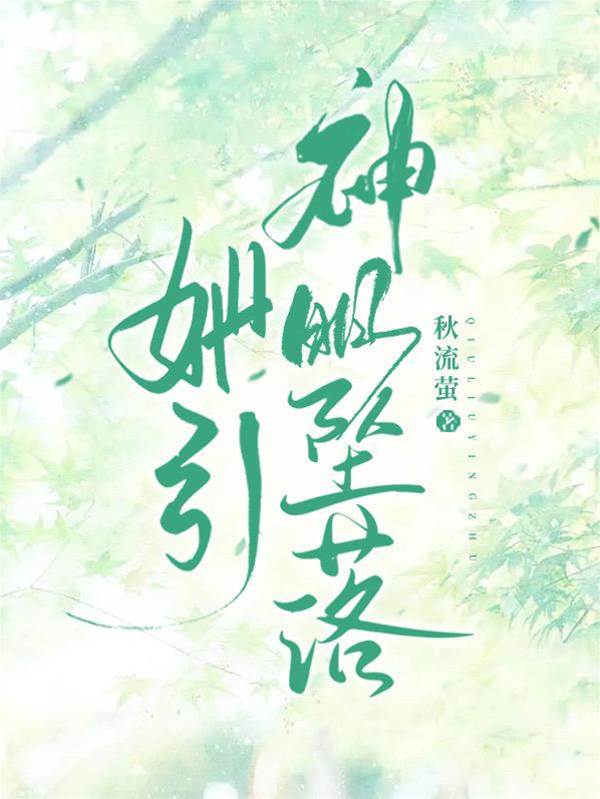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拐個上神當夫君》 第二十四章:再逛窯子又見鬼
說話間那位李執將軍也出場了。
劍眉星目,英氣人。
才不過說了兩句謝禮話,瀲月這桌的食客又開始點評。
“李將軍自那次回來也不打仗了,啃老本過活。”
“是啊,估計九死一生,怕了。”
隔壁桌的大嬸聽見他們這話,十分暴躁的擼起袖子走過來指著那幾個多舌之人道:“李將軍英明威武!是你們這些懶鬼能評頭論足的?”
這一鬧其它大姐們也注意到這邊,紛紛放下筷子朝他們桌走來。
人怒氣沖沖男人也不落下風,很快聚一個陣營,雙方罵。
“怎麼不能說了?他自個兒干了什麼混蛋事人盡皆知!”
“你得了吧!那是神仙眷!”
“神仙眷干嘛不給名分!”
“胡說!”
瀲月跟在人群里認真劃水,不一會就劃出人群,癱坐在長凳上。
這群人可真難鬧騰,瀲月了口氣,白皙的小手抬起去額前細汗。
轉頭向臺上想瞧瞧那將軍怎麼解決,哪知他沒有一點反應,放下酒杯就走了。
倒是那幾個高忙前忙后的疏散人群。
有古怪。
瀲月當下抱起蒜蹄趁人群不注意溜進后院,一路跟著那李執來到他臥房,奇也怪哉大白天不開窗也不開門,他打開一個小側溜進屋立馬就把門關上了。
作雖快,瀲月還是在哪間隙往見了屋子里面正對著大門的畫卷。
一個面容致的姑娘,后是大片大片的銀杏,金黃一片,好似火焰燃燒。
這該就是他們說的銀杏姑娘了吧?
算了,何必多管閑事。
瀲月搖搖頭,抱著蒜蹄往回走,只消去銀杏林找到那位銀杏姑娘就是,何必去管這李執古怪。
蒜蹄在懷里不明所以,小爪子撓撓腦袋:“老大,咱怎麼不跟了?”
Advertisement
“跟進他房里睡覺嗎?”
瀲月蒜蹄茸茸的小腦袋,作迅速溜出后院,大堂前食客還在打架,男男扭做一團,一時間還分不出勝負。
瀲月不嘆:“可真能打。”
出了將軍府一路來到城南畫舫,這兒的人可比將軍府多多,偏偏要去對岸的碼頭正好被畫舫堵了。
瀲月站在碼頭前觀了一會,覺著一時半會大船也不可能開走,正轉準備繞路,小手被人拉住。
轉回頭一看,是個俏姑娘,一雙眸狹長,眼尾赭更是點睛之筆,襯的一雙眼嫵勾人。
子看瀲月回頭,立馬將子上去,前有一下沒一下的蹭著瀲月手臂。
這的讓瀲月又想起那春不及,也喜歡這麼抱自己。
子打了個寒,下意識想把手出來,可那姑娘摟的更了!
“姑娘你別……”瀲月手去推,話還沒說完就被打斷。
“姑娘,既然來了就進去坐坐吧,今兒可是最后一天開張,以后你就是想來也沒機會了。”
要放以前,瀲月絕對是高興的,可自打雛庭樓一事后,是再也沒那個膽兒了,誰曉得面似天仙的弱子是人是妖。
“真別,我就是想去對岸。”瀲月心一橫,也不管姑娘站不站的穩,使力就把手出來。
姑娘也不惱,笑的看著瀲月:“這附近碼頭啊都被我們畫舫給包了,姑娘你若想過岸,只能隨我進去再渡小舟,或者明日再來。”
明日?瀲月想也不想就否決了這想法,要是梵知發現消失了一日,會……不對,他擔心個屁啊!
最后路大爺還是跟著子進了畫舫,名其曰:盛難卻,和某人可沒關系。
畫舫到掛著紅燈籠,紗帳搖曳,若不是人來人往的游客,瀲月真會以為這是夢境。
Advertisement
那姑娘也就是個拉皮 條的,把瀲月帶進畫舫大概說明小舟在哪就走了,瀲月站在原地看著走出畫舫,作麻利的上一個男客,前的有一下沒一下蹭著他的手臂,嫵神勾的人魂都快丟了。
蒜蹄顯然不太喜歡這地兒,小爪子死死著瀲月前襟:“老大咱還是快走吧。”
“行。”瀲月了蒜蹄的腦袋示意安,抬腳往畫舫深走。
也不知繞了多久,還是沒能找到那姑娘說的地方,倒是走廊行走的游客越來越。
瀲月找的累了,子斜斜靠在墻邊,心中不住吐槽:這是什麼鬼地方!
小腦袋四張,確認了方向一手撐著墻面想要直起子。
下一秒子一歪,整個人朝墻那方向倒去。
這所謂墻面就是個巨大的屏風?
顯然是沒料到這個況,瀲月自己摔倒不說,蒜蹄也從懷里飛出老遠。
瀲月趕忙爬起去撿,剛將小兔兒抱起,一枚金的鈴鐺滾眼前。
瀲月皺了皺眉,抬頭朝前去,這條走道藏在屏風后面本沒人發現,瀲月算是那些游客里頭一個進來的。
長廊盡頭是一個紅子。
巧笑倩兮,目盼兮。
隨意倒在比地面高出一截的小臺上罐著酒,大紅擺旁有數十顆金鈴鐺靜靜躺在那。
想來剛才這顆也是周的了。
難得見到一個沒有男客的姑娘,瀲月自暴自棄的帶著蒜蹄走近:“敢問姑娘舫小舟在何?”
子轉頭毫無緒的看了瀲月一眼,抬手指著后方向:“直走便是。”
“謝姑娘。”瀲月道完謝頭也不回的離開,等著上了小舟才松下一口氣。
蒜蹄到的張,心中傳音:“老大你咋了。”
瀲月心有余悸的抹了把額上細汗,緩了緩才開口回答它的問題:“那個不是人,快走為妙。”
Advertisement
那子領有些松散,瀲月明確瞧見細的臉龐下滿是皺紋的脖頸,這也許和冬不歸們一樣,是個妖怪。
瀲月也不知自己最近怎麼了,老是到妖怪,還都是人,難不自己被鬼怪纏上了?
越想越慌,瀲月趕忙搖頭甩去腦中想法,雙手抓著漿使勁劃水,快跑為妙,快跑為妙……
上岸走不過十來步就到了那銀杏林,就好似有什麼結界般那遍地金黃與瀲月腳下的黑土地形了鮮明對比,像是兩個世界。
蒜蹄心里犯慫,抬頭弱弱問道:“老大,咱真要進去?”
瀲月一雙桃花眼死死盯著哪金黃,半響,咬咬牙道:“進!”
也不知去哪能找到銀杏姑娘,一人一兔在林子里漫無目的的走著。
這些樹枝干壯,層層茂金黃的葉子底下還藏著顆顆圓潤的果實,黃果皮,太一照好似個小燈籠。
小兔兒饞的出小舌頭瓣:“老大,這看起來好好吃。”
瀲月撇撇:“這玩意有毒,吃不得。”
蒜蹄不甘心的盯著那小燈籠:“它這麼可,怎麼會有毒!”
瀲月搖搖頭,強行將它倔犟的小腦袋按下:“皮有毒,現下我也沒有工給你弄啊,等日后有機會帶你吃現的。”
“真的嗎?”
“真的。”
得到承諾,蒜蹄也不在著那銀杏果,老老實實的窩在瀲月懷里。
瀲月無奈嘆氣,這兔子可真是吃食最大了。
走到林子深,依舊沒有人煙,連個房子的影兒都沒見著。
瀲月走的累了,干脆抱著蒜蹄在地上蹲下。
蒜蹄看郁悶神態,安道:“都十年過去了,說不定那姑娘早就死了。”
瀲月扁扁,有些不甘心:“頭發可不會爛。”
蒜蹄看不愿放棄,小眼珠子轉了一圈,靈機一道:“你都出來快一天了,你家那位看不見你會著急的,我們快回去吧!”
Advertisement
不提還好,一提瀲月更加難過:“他要真會著急我就好了。”
這人總是一副淡淡模樣,任怎麼拔耍潑都毫無反應。
這可是難倒蒜蹄這小兔子了,疑的撓撓腦袋:“你跟他一起的時候不是可開心嗎?”
“我若不主些,他再走怎麼辦?”
黏是一回事,他在不在乎自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即使他現在毫無反應,瀲月也不敢試探了,有些事不把窗戶紙捅破了反倒是和諧,管他如何想,當下能一起便是。
蒜蹄實在想不明白,干脆岔開話題道:“哪我們快些找,找到了就回去,天可冷了,老大你子才剛好。”
“行吧。”瀲月不是糾結的子,遇上難過事傷心也就難過一時,不會因為自己子耽誤正事。
才剛抬頭,就瞧見前邊大樹旁有一截紅,上面可見的繡花好像是件嫁。
難不找到了?
瀲月細眉皺起,剛要抬腳朝前走,后就傳來一聲巨響。
靜不小,給瀲月嚇了一跳,慌忙回頭除了灰塵又什麼都沒有。
待塵埃散去,瀲月才看見地面上的一個人形大坑。
天外飛妖?!
瀲月咽了咽口水,挪著步子慢慢靠近那大坑,摟著蒜蹄的手也逐漸收。
這要是個妖怪可怎麼好,可如果不看的話一會襲自己又怎麼辦?
兩頭為難,瀲月還是決定一探究竟。
右手召出紅骨劍,擺出防姿勢靠近那大坑。
待走到坑邊,看見坑底那紅底金線的袈裟瀲月才松了一口氣,是個和尚啊。
不過這坑砸的可真深,瀲月瞧著覺都到腰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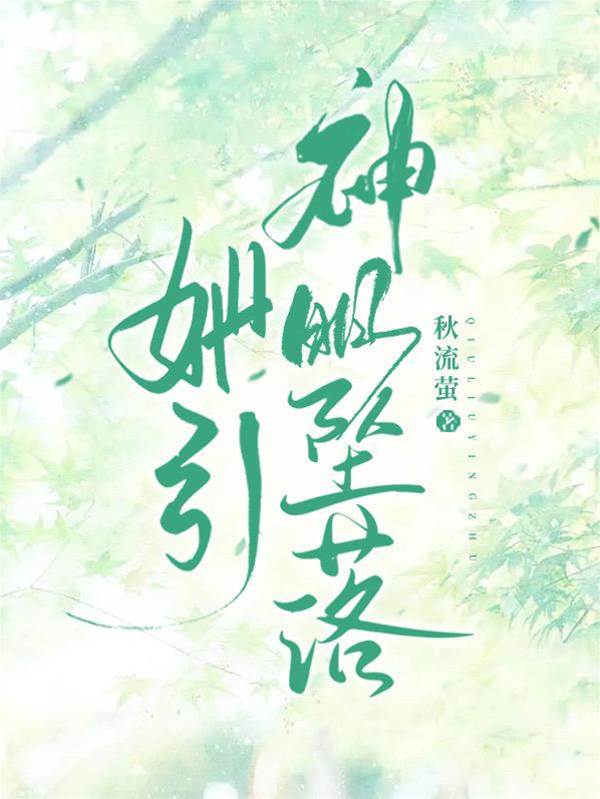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