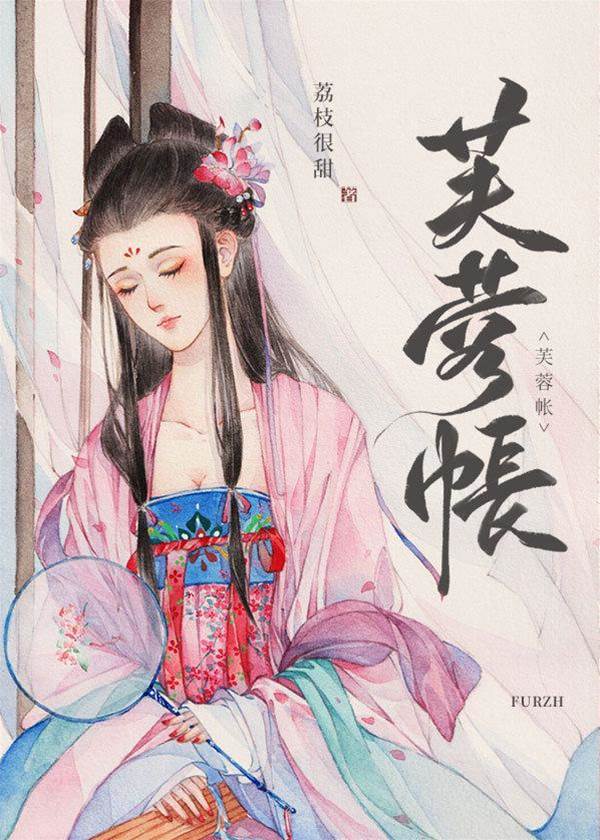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侯門夫妻重生后》 第16頁
那一掌的疼痛于而言只在落下的一剎那,之后就沒了,心不過又比之前更冷了一些。
折騰了一日,累了,躺去床上沉沉地睡了過去。
—
街頭的另一,一人還在逃命。
正是駙馬爺趙縝。
今夜他躺在土里,不知道埋了多久,幸得雨水湍急,把他一張沖刷了出來,一面張艱難呼吸一面吞咽著泥水,等耳邊徹底聽不見說話聲了,才敢破土而出。
雙手抹去臉上的泥水,跪在地上吐了半天的泥沙,抬眼一,只見四周的蘆葦有兩個人高。
瞧來對方鐵了心要毀尸滅跡。
土里呆得太久,臉上的火辣已消去,腫卻沒消,一張臉被人扇了不知道多下,如同發了酵的紅饅頭,一路東躲西藏,生怕被追上,跌跌撞撞地逃到了國公府,門房險些沒認出來,等進了書房,見到鎮國公,雙膝一,人都癱了,“國公爺,救命......”
趙縝好歹也是狀元,又乃當今駙馬,平日里端得是儀表堂堂,可見這文人只適合講道理的世界,一旦遇上不講理的武力,便狼狽得沒法看了。
國公爺頭一眼也沒認出來,半晌后還是從他腰間的那塊玉佩辨出了份,面震驚,“駙馬莫不是從土里鉆出來的?”
趙縝牙關打著,可不就是剛從土里鉆出來的,一埋一淋,如今上的皮都發了白,臉過度蒼白,與死人無異。
瞧出了事態不對,國公爺眉頭一皺,起到他跟前,“怎麼回事?”
Advertisement
趙縝也想知道怎麼回事,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到這會腦袋仍是一團懵,前日他與長公主鬧得不愉快,一人回了狀元巷,昨日一早起來,黑云頂,正值雷閃電,屋里突然竄出兩人來,二話不說綁了他。
劈頭便問:“東西在哪兒?”
他在朝行事穩重,待人一向溫和,除了晏家,他從未沒得罪過誰,再者,他是駙馬,誰會想不開冒著掉腦袋的風險來行刺他?
無緣無故被打一頓,又被帶到了一破院子里關到了今日,索把他埋了。
他約也猜出了對方所說的東西,怕不是金銀財寶,而是另外一樣會引來殺之禍的東西。
這也是他死里逃生后,先趕來國公府的原因。
他能想到,國公爺朱耀也想到了,面上的神逐漸起了變化,屋外天閃映室,那一雙眼睛瞬間被霾覆蓋,聲問:“駙馬曾說過什麼?”
“一句沒說。”他對天發誓。
并非他骨頭有多,而是對方從始至終只一遍遍重復。
“你說不說。”
“你說啊......”
“我讓你說......”
挨了幾十個耳,愣是沒給他開口的機會,不得已他只能裝死,不然這會子他是真死了。
見他這副狼狽樣,倒有幾分說服,國公爺臉緩了緩,上前去扶人,“趙大人可知對方是誰?”
“不知。”
“沒看清樣貌?”
“尚未。”
“嗓音可悉?”
趙縝搖頭,瓣張了張,開口頗有些艱難,“是位姑娘。”這是他如今唯一知道的線索。
Advertisement
姑娘?
朱耀眉頭一,屋外傳來一道急促的腳步聲,一名小廝立在門外隔著門扇低聲稟報:“國公爺,晏世子回來了。”
沒等屋二人驚訝,又道:“宮中來了消息,說是陛下丟了一樣東西,錦衛已連夜封鎖了宮門。”
第07章 第 7 章
第七章
白明霽一覺睡得并不安穩,后半夜那雨砸在瓦片上,像是要把屋頂砸穿一般,天將亮時雨方才停,怎麼也睡不著了。
落雨的緣故,屋里四門窗關得結實,有些悶,白明霽沒去外間歇息的金秋和素商,起走去側面的一扇支摘窗前,推開窗扇,雨后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清涼意滲皮,激得人神抖擻。
一抬頭的功夫,對面的書房走出來了兩道影。
晏長陵。
見了三四回,唯有這回收拾得周正。
穿一件竹月圓領衫袍,玉冠束發,手提一把佩刀,抬邁下踏跺時,腰間一枚玉佩隨步輕,腰窄長的,還是那恣意勁兒,領著他的侍衛,腳步匆匆出了門。
沒穿服,不像是上朝。
昨夜岳梁問他的話,坐在馬車都聽到了,按理說他私自回京,無論什麼樣的理由,也該第一時間應該進宮復命。
瞧那人的舉止,顯然沒打算去面圣。
如今兩人是自掃門前雪,誰也管不著誰,只要他不找死,連累到,他做什麼與無關。
人走遠了,白明霽回到了屋里,經過妝臺的銅鏡,往里瞧了一眼,昨夜雖及時敷了冰,半邊臉還是留下了淺淺的紅印。
Advertisement
可見當時得有多難看,突然明白了昨夜那人被鬼追的腳步,和那道瞟到燈上去的目。
多半是不忍瞧,給留足了面子。
再想起阮姨娘所的耳和那一袋子冰,大抵是母親走后,第一個替鳴不平的人,倒也不枉自己為他攤上了一樁命案。
瞧在這些的面上就此兩清吧,不用他來謝了。
趙縝的死,像是埋在地下的火|藥,遲早得炸。
白明霽一直留意著外面的靜,大半日過去,并沒駙馬爺失蹤的消息傳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19 章
腹黑世子妃日常
一朝穿越,腹黑狡詐的她竟成身中寒毒的病弱千金,未婚夫唯利是圖,將她貶為賤妾,她冷冷一笑,勇退婚,甩渣男,嫁世子,亮瞎了滿朝文武的眼。 不過,世子,說好的隻是合作算計人,你怎麼假戲真做了?喂喂,別說話不算話啊。
39.1萬字7.75 70010 -
完結652 章

重生之嫡女毒妃
枕邊之人背叛,身邊之人捅刀,她的一生,皆是陰謀算計。 一朝重生,她仰天狂笑! 前世欺我辱我害我之人,這一世,我顧蘭若必將你們狠狠踩在腳下,絕不重蹈覆轍! 什麼,傳言她囂張跋扈,目中無人,琴棋書畫,樣樣都瞎?呸! 待她一身紅衣驚艷世人之時,世人皆嘆,「謠言可謂啊」 這一世,仇人的命,要取的! 夫君的大腿,要抱的! 等等,她只是想抱個大腿啊喂,夫君你別過來!
113.7萬字8 2527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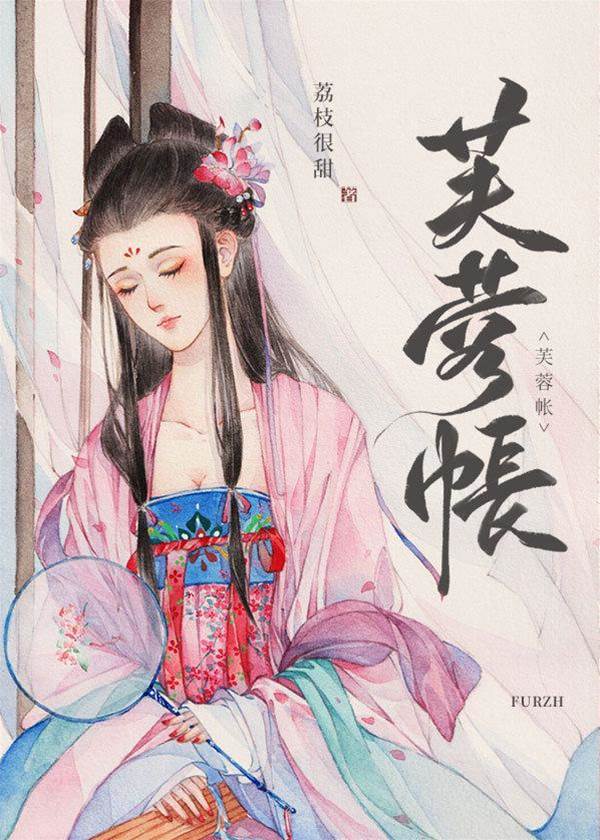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26 章

妃你莫屬:王妃,請低調
作為軍事大學的高材生,安汐無比嫌棄自己那個四肢不勤,白長一張好皮囊的弟弟安毅。可一朝不慎穿越,那傻弟弟竟然翻身做了王爺,而她卻成了那位王爺的貼身侍女;自小建立的權威受到挑戰,安汐決定重振威信。所以在諾大的王府內經常便可見一個嬌俏的侍女,提著掃帚追著他們那英明神武的王爺,四處逃竄,而王爺卻又對那侍女百般偏袒。就在這時男主大人從天而降,安汐看著躲在男主身后的傻弟弟,氣不打一處來。某男“汐兒,你怎麼能以下犯上?”安汐“我這是家務事。”某男頓時臉一沉“你和他是家務事,那和我是什麼?”安汐“……我們也是家務事。”
56.6萬字8 483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