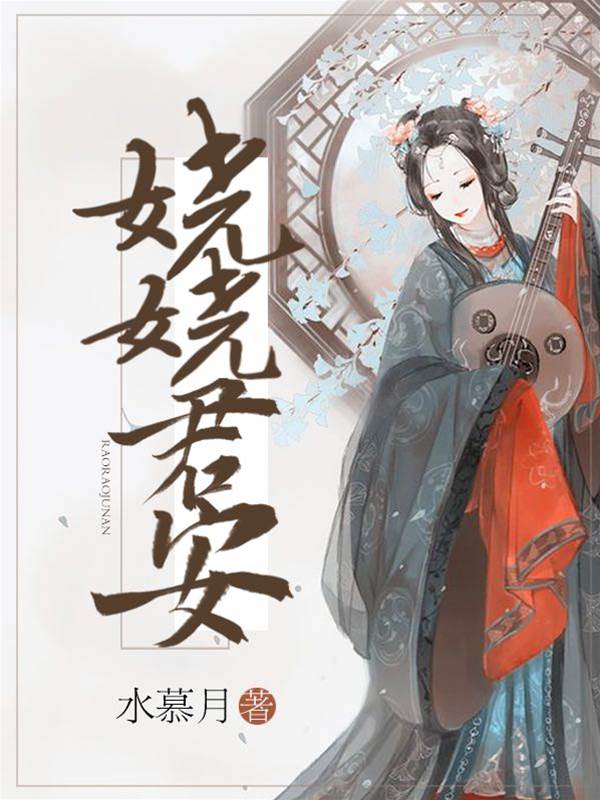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通房丫鬟》 第12章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沒有藥,花容痛得一夜沒睡,蕓娘發現后很生氣,花容再三保證不會耽誤干活才沒被趕出繡房。
舍不得買燙傷藥,花容問了個土方子,托人帶些柏樹枝和香油回來。
賞花宴這日府里熱鬧非凡,宴席持續到傍晚才散。
結束后殷氏立刻問江云騅有沒有心儀的姑娘。
江云騅往里丟了粒油花生,不客氣的說“沒一個能眼的,丑。”
“娶妻當娶賢,容貌是其次,品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永安侯府的二姑娘還有靖安侯府的三姑娘都還不錯。”
“你都有喜歡的了還問我做什麼?”
江云騅冷嗤一聲,起離開,走到院門口時正好聽到殷氏房里的張嬤嬤與繡房的蕓娘說話“這次的團扇很得這些小姐的喜歡,是誰想到把干花繡到團扇上的,夫人有賞。”
Advertisement
蕓娘歡喜道“是奴婢突然想到的,還擔心夫人會不喜歡呢,府里給的月錢已經夠多了,哪能再要夫人的賞。”
江云騅步子一頓,突然想起那日花容被高海山堵住時,手里提著一籃子花。
這個主意不應該是想出來的?
不過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江云騅并未上前探究,仍是大步離開。
他忙的很,哪有功夫管這種閑事?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夜里江云騅夢到了花容,如那日一樣提著一籃子花,卻不是被高海山堵住,而是被他堵在幽暗的山里。
線昏暗,他放肆的很,偏要哭。
第二日醒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來,江云騅的臉黑得不像話,月貌進屋伺候他洗漱,聲提醒“爺今日約了永安侯世子去馬場玩兒,這個時辰了還去嗎?”
Advertisement
“自然要去,我是那種喜歡失約的人嗎?”
月貌默默給江云騅換好衫,等人出了門,便開始整理床鋪,卻在枕頭底下發現了那條被一團的底。
月貌臉微變,又驚又怕。
江云騅已及冠,有這方面的需求很正常,但殷氏已抬月貌做了通房丫鬟,他有需求不找月貌,反而自己憋著。
若讓別人知道,月貌當如何自?
江云騅并不知道月貌在想什麼,黑沉著臉出門,然而馬車沒出多遠,一個怯懦的聲音便傳耳中“請問你知道線鋪該怎麼走嗎?”
見鬼!怎麼哪哪兒都是這個不識好歹的人?
江云騅以為是幻聽,沒有理會,過了會兒卻又聽到一模一樣的問話。
太突突的跳了跳,江云騅到底還是掀開車簾。
Advertisement
今日正好,因有商隊路過,道路有些擁,馬車行的很慢,馬車外,花容穿著一藍白丫鬟,正笑盈盈的看著一位貨郎。
梳著最簡單的發髻,上并無飾品,臉上也沒有脂,因為膽怯,兩頰有些紅,像剛開始的桃子,散發著青稚的香甜。
對著別人倒是笑得很開心!
江云騅本想放下簾子不理會,卻見那貨郎趁機拉住了花容的手,嚇了一跳,卻不敢大呼小,都快急哭了。
“……”
兔子急了還會咬人,怎麼不咬他?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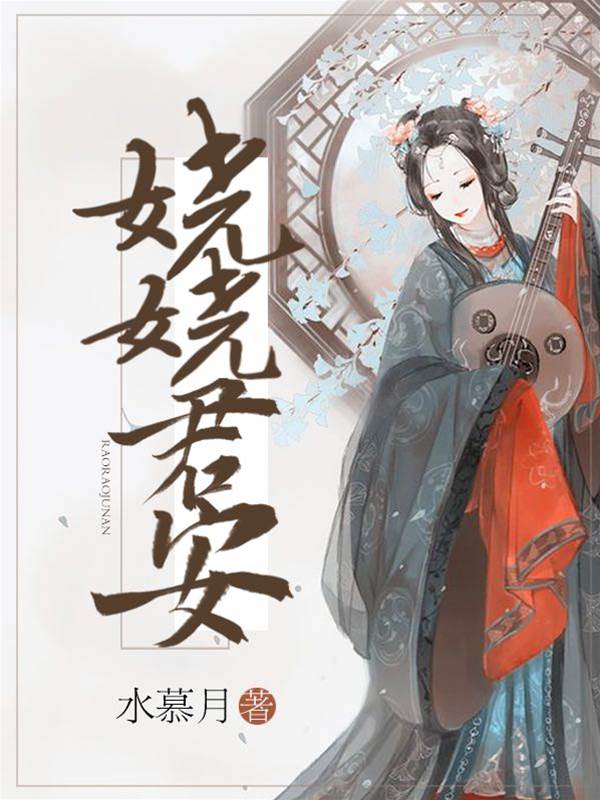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