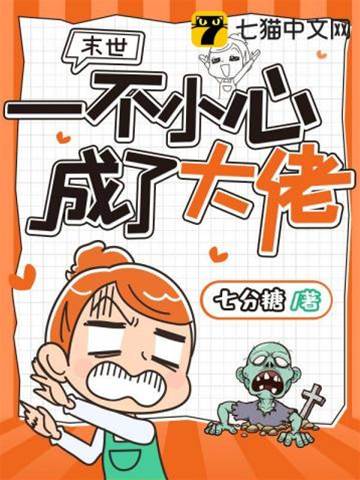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禍水》 第9章 毀容
程洵按照指示調查了何桑的繼父,趕去別墅匯報。
男人正在書房通電話,約聽到人說,“我想你了。”
他走神,沒太專注,“想我了?”
“你明知故問。”人帶點嗔,“你在公司嗎。”
梁紀深停頓一秒,“嗯,加班。”
程洵瞥桌后的男人,又垂首。
宋禾言語曖昧,“我剛洗完澡,有點寂寞,你搬來好不好?”
他不回應。
“紀深,如果我能懷上你的孩子,梁家肯定會接我,拖得越久變數越大,我希盡快為你的妻子。”
梁紀深發現程洵在門外,草草結束,“這邊忙,你吃完飯早睡。”
宋禾六神無主盯著暗了的屏幕,那種生生被掐斷,被忽視的悲憤。
他對自己明顯不復當初。
梁紀深并非為狂熱的男人,卻也一向對憐憫惜,有求必應。
如此冷淡,點燃了宋禾心底的怨念。
那個人的介。
是禍。
梁紀深坐直,靠著椅背,撥弄打火機的金屬蓋,“什麼結果。”
程洵做足了心理建設才敢進去,“黃勇,以前是一家公司的小領導,負責后勤采購,吃回扣太多被開除了,目前無業游民。”程洵小心翼翼觀察他反應,“何小姐...在18歲和19歲報警黃勇擾。”
火苗乍然熄滅,又復燃,男人眼中的寒氣一寸寸蔓延開。
“拿來。”
“我拍下了口供。”程洵將照片擱在桌上,“不清楚什麼原由,何小姐又撤銷報案,雙方和解了。”
筆錄翻到后面,男人眉目越發森,像凝結了一層霜。
雖無實質的傷害,不過看筆錄,黃勇深夜強行闖房間摟抱,窺沐浴,在飯菜里下安眠藥,給何桑的影著實不小。
Advertisement
梁紀深牙出四個字,“我要他人。”
程洵說,“已經關押了。”
男人渾的煞氣,抄起外套,大步朝樓下走。
車行駛至東郊廢品廠一蔽的倉庫外,程洵踢開門,四面破敗的墻壁,滋長出發霉的苔蘚,糜爛的腥臭味。
在一堆腐敗的垃圾中央,黃勇被膠帶封,手腳反捆,見有人來,嗚咽著蠕。
直到他瞧清是梁紀深,眼里的求生變了極度的畏懼。
男人彎腰,揭掉封條,不輕不重地拍了拍他后腦勺,威懾十足,“又見面了,黃勇。”
黑黑染著冰涼的水,黃勇起了一皮疙瘩。
這氣勢嚇得他心虛,跪地求饒,“梁先生,我吐,那一百萬我吐行嗎?”
“吐?”程洵不屑,“你不是還賭債了嗎。”
“我有繼啊。”黃勇巍巍爬到梁紀深腳下,“用抵賬,什麼時候抵完一百萬,咱們什麼時候兩清。”
真是作死。
程洵退到一旁。
梁紀深踩住黃勇的腦袋,鞋底輾軋,他猶如一條喪家之犬,痛苦哀嚎著。
“明白為什麼綁你嗎。”
黃勇臉埋泥土,斜著眼看男人,“我不...不明白。”
“夠的。”男人居高臨下,像對待一灘垃圾,“擾,是嗎?”
黃勇當即臉慘白,掙扎大,“那婊子誹謗我!媽可以作證,我沒有——”
“你利用何小姐母親的安危威脅銷案,梁先生最厭惡欺凌人的敗類。”程洵暴扳住他,一拽麻繩,他翻滾著撞上鐵門。
慣太大,黃勇暈眩干嘔,“梁先生和我繼不是分開了嗎——”
梁紀深坐在對面的木頭板凳上,不耐煩點煙。
程洵揪住他頭發,“分與不分,也不妨礙梁先生和你算過去的賬。”
Advertisement
黃勇驚惶之下雙目充,一個勁的搐。
梁紀深吸完半支煙,走到他面前,“哪只手的。”
“警察都結案了,你們沒——”
男人叼著煙,利落一腳,正中黃勇肋骨,噴的沫子濺在鼻梁,他指腹一抹,“長記了嗎。”
黃勇哪招架得住這頓打,疼得死來活去,也慫了,“我只是抱,一鬧,我就跑了,我沒得逞,真沒得逞!”
梁紀深扼住他脖子,“抱了幾次。”
“就一次...”
力道漸漸發狠,憋得黃勇張大,“兩次!暑假在家,我趁著媽上夜班擾過,子烈,差點捅了我!”
疾風撲面,水泥板斷裂的脆響在靜謐的荒郊炸開,黃勇只覺得頭頂一震,當場昏厥。
梁紀深棄了板子,走出倉庫。
保鏢迎上,“梁先生,放人嗎?”
他面容沉,氣場也強悍,沒開腔。
程洵使了個眼,低聲,“送醫院,清理干凈現場。”
吩咐完保鏢,又通知何桑。
“打了黃勇?”
程洵坦誠相告,“黃勇以您的名義到梁氏集團勒索了一百萬,另外,梁先生得知他的一些罪行,出手教訓了一通。”
何桑堵在晚高峰的十字街口,前方長長的車隊不到頭,“他呢。”
“梁先生應該會去警局。”
握方向盤,沒出聲。
程洵回車上,沿著公路掉頭,“估計是殘廢了。”
梁紀深手臂倚車門,看窗外。
“梁董和夫人若是知曉...您恐怕要遭殃,不如先下手為強。”
梁延章教子嚴格,二房續弦又虎視眈眈挑他病,踏錯一步,連紀席蘭也饒不了他。
男人鎮定自若,“去一趟警局。”
晚上九點,何桑站在監護病房的外面,過窗口,黃勇躺在床上,昏迷的狀態,沒料到傷勢會這麼重。
Advertisement
皮開綻,深可見骨,是下了狠手。
進屋,“媽。”
趴在床邊的人起初沒聽清,何桑又喊了一遍,人呆滯扭頭,淚眼朦朧。
分明剛四十出頭,卻滄桑得像個老嫗。
何晉平在世時,賺得不,顧家,日子很滋潤,沒吃過苦,但何桑知道,不何晉平。,婚姻和,是三碼事。
何桑放下一枚信封,“這里有五萬塊錢,你自己補補營養。”
人直起腰,“是你找人打了你黃叔。”
何桑控制住脾氣,“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醫生診斷他腦震,骨斷裂。”人咄咄人,“你爸死了六年,你非要我守寡孤獨終老嗎?”
話音未落,何桑挨了一掌。
抖捂住臉,不吭聲。
人指著何桑,“你黃叔是我后半生的依靠,把我們攪散了你才滿意嗎!”
“他惹了不該人的人!敲詐是犯法。”何桑也發了,“我爸尸骨未寒,你賣了房子嫁他,我只能住在學校,假期回到你們的家,他什麼德行你了解嗎?”
“慧文——”黃勇及時蘇醒過來,抓住何母的手,“找梁家索要賠償...假如他們不給,讓何桑當證人告梁紀深,我要告到他們敗名裂!”
“告他們?你做夢。”何桑冷笑,“你是自作自。”
“反了...”黃勇瞪大眼咳嗽,“慧文啊,不是我親生的,是何晉平的兒,跟我不是一條心啊!”
“你千萬別氣。”何母哭著摁下急救鈴,“我全聽你的。”
何桑太失了,不再心,“媽,他榨干你的那天,就是你后悔的一天。”甩下這句,摔門離去。
*
次日,何桑到警局,門口停了兩輛車。
因為梁璟在國際外的顯赫地位,梁家的車一律是a0的車牌號,非常顯眼。
何桑叩了叩車窗,降下后,是一個陌生男人,保鏢的打扮。
“程書呢?”
保鏢說,“前面。”
繞到第一輛,程洵在駕駛位吃早餐,何桑敲玻璃,“什麼況了。”
他把最后一口面包塞里,推門下車,“梁家出面了。”
何桑心臟一咯噔,這次的麻煩是因而起。
程洵安,“梁先生既然敢做,一定有辦法應對,而且不是什麼彩事,梁董不會聲張。”
很快,兩名警察送梁紀深出門,其中一名同他握手,“后續的調解賠償,梁先生還是要隨時配合,您舉報黃勇涉嫌敲詐罪,我們也會核實。”
“沒問題。”
他轉過,視線正好對上何桑。
在里面待了一宿,眉宇幾分疲態,下頜的胡茬烏青濃,男人味更重了。
何桑倏地打個噴嚏,鼻頭紅,耳尖也紅,睫上掛著碎碎的冰晶,眨間,格外水汪汪。
梁紀深下臺階,奪過程洵手中的大,“來多久了?”
“半個多小時。”
他走近,將大給,“怎麼不在車里等。”
何桑一邊穿一邊繼續噴嚏,“程書說你馬上出來,就一直等著。”
第二輛車的保鏢這時下來,徑直到跟前,“三公子,董事長讓您立刻回老宅。”又瞟了何桑一眼,“何小姐一起。”
梁紀深把何桑扯到后,表生,“跟沒關系。”
“您認為瞞得了梁董嗎?”保鏢作出請的手勢,“三公子不要為難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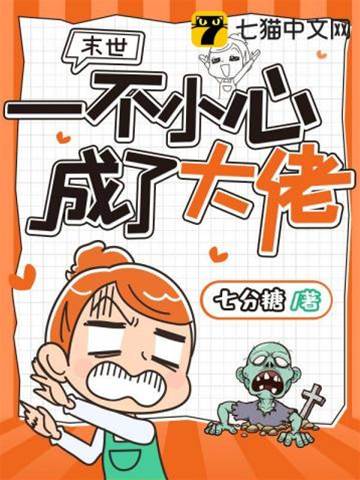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2925 章

影后的嘴開過光
「江小白的嘴,害人的鬼」 大符師江白研製靈運符時被炸死,一睜眼就成了十八線小明星江小白,意外喜提「咒術」 之能。 好的不靈壞的靈?影后的嘴大約是開過光! 娛樂圈一眾人瑟瑟發抖——「影后,求別開口」
524.2萬字8 15366 -
完結486 章

離婚後,虐她上癮的京圈大佬腰酸了
閃婚一年,唐軼婂得知她的婚姻,就是一場裴暮靳為救“白月光”精心策劃的騙局。徹底心死,她毅然決然的送去一份離婚協議書。離婚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裴總離異,唯獨他本人矢口否認,按照裴總的原話就是“我們隻是吵架而已”。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裴總,您前妻要結婚了,新郎不是您,您知道嗎?”裴暮靳找到唐軼婂一把抓住她的手,“聽說你要結婚了?”唐軼婂冷眼相待,“裴總,一個合格的前任,應該像死了一樣,而不是動不動就詐屍。”裴暮靳靠近,舉止親密,“是嗎?可我不但要詐屍,還要詐到你床上去,看看哪個不要命的東西敢和我搶女人。”
86.8萬字8 34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