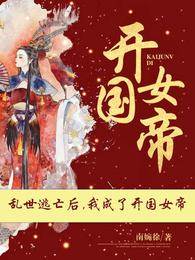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瑤臺春》 第 8 章
溧長公主早便對鄭玉磬說起過聖上想要將迎宮中,但是的位份恐怕除了聖上誰也不敢給一個準信。
“是妾的份教聖上為難了麽?”
鄭玉磬纖細的手指平聖上微蹙的眉頭,反而沒有聖上所預想的張,反倒是多了幾分坦然:“難道宰相們連一個才人或是人的位份也容不得嗎?”
紙裏包不住火,如今聖上無非是用權勢來人指鹿為馬,實則宮中都知道聖上所養的外室才不是中書令鄭家的兒,而是江南某個寒門裏養出來的兒。
早就知道會是如此,秦氏滅門,這些道貌岸然的勳貴們要譴責的不是聖上或是廢太子,而是這個狐主的紅禍水。
既然是禍水,當然不夠資格侍奉一手製造了這些慘禍的至尊天子。
“音音所求便隻有這些麽?”聖上原本是為博人一笑才故意說起此事,聽見這樣說來反而意外。
“位份有什麽要的,而且才人的位份也很高,原先我在宮中的時候遠遠見到服侍聖上的才人還得行禮呢!”在的認知裏,才人大概就是很高的嬪妃了,“隻要能正大明地侍奉聖上,於妾而言便已經是福份了。”
鄭玉磬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要求對於聖上而言有多麽渺小,“若不是這個孩子,便是沒名沒份,我也是該一輩子伺候聖上的。”
鄭玉磬本來就年歲不大,對廷也並不了解,說這話
或許是無心的,但聖上聽來卻覺得心中百般滋味,隻要自己不在乎麵,禮法本就不大能約束得住他,然而鄭玉磬為子,卻不能這樣隨心所。
做了自己藏在道觀的外室,錦食自然遠勝昔日,可卻從原本人人豔羨的探花郎夫人變了被人唾棄的禍水,沒名沒份,心中也會自輕自賤一些。
Advertisement
“這原不是音音的錯,若是當日朕早些看見你,哪裏還會有如此波折?”
聖上從袖中暗袋裏出了一方折疊妥帖的淡黃絹,坐起後遞給了滿麵疑的鄭玉磬,笑著道:“日後宮,你便是宮中的貴妃娘娘了。”
“貴妃?”
饒是鄭玉磬料到了這位份必然不會如才人人一般低,但是也沒有想到聖上竟然是存了為後宮之首的心思,知道男人獻寶的時候總是期待能從子的麵上看見驚喜的神,哪怕沒有欣喜若狂,可是那種沒有見過世麵的震驚並不是作偽,也足以滿足聖上的心思。
借著紅燭微弱的亮,鄭玉磬能瞧見淡黃絹上是聖上的親筆手詔,在洋洋灑灑數百字的讚褒揚之後,清晰地寫著“立鄭氏為貴妃,居錦樂宮,十一月初八日宮。”
聖上的字如其人,氣勢淩人,行草中又帶了些飄逸張揚,不拘小節。
如果記得不錯,這座宮殿上一位主人是掌管六宮的張貴妃,現在或許應該稱之為張庶人。
“若是隨
隨便便冊封一個才人,有什麽好朕煩惱的?”聖上在那張寫滿了疑驚訝的麵容上輕輕親了一下,“從今往後宮中無論是誰,都得向音音行禮。”
聖上知曉對宮裏的事還不太清楚,但是之前張氏那麽奚落,音音應該也能明白貴妃是宮中之首。
往常冊封貴妃的詔書都是由學士書寫的,這還是他頭一回有興致自己來寫這些對被冊封者的讚詞匯,半點不覺得厭煩虛偽,反而寫著寫著便惦念起來,非得過來看一看才安心。
“您怎麽……”鄭玉磬不知道為什麽驚訝之餘又有些不敢置信,雙手捂著臉,不知道那哽咽聲中存有幾分真意,“我哪裏配得上貴妃的位置,您知道的,我連執掌中饋都是勉勉強強,更何況是掌管後宮?”
Advertisement
聖上平日要立高位嬪妃總是不免涉及到其他後妃與其母族的利益,在天子和悅的時候,有些臣子也敢直言進諫,然而他這些日子才下詔廢了先皇後所出的太子,又殺了幾位皇子,朝野皆驚,一時半會也沒有人敢拂天子逆鱗。
這個時候皇帝能把注意力轉移到貴妃上去,反倒他們鬆了一口氣,象征勸了勸也就隨聖上去了。
畢竟聖上說過永不再立後,而貴妃就算是再怎麽得寵,退一萬步來講,哪怕生的是位皇子,的孩子畢竟還太小,聖上天縱英明,總不會立一個繈褓中的小娃娃做太子。
尚且有些回不過神來,但聖上就是喜歡這樣手足無措的模樣,顯德送來了岑建業親自熬好的藥,見聖上正笑著去撥開鄭夫人、或者說是鄭貴妃捂著臉的手,舉止親昵,連忙低下頭去,心跳得有些厲害。
“你是朕喜的子,皇嗣的生母,難道一個貴妃位還不配嗎?”聖上笑道:“如今還是惠妃暫代執掌廷,你現在懷著孕,先在旁邊跟著學一學,以後練些再讓惠妃將印送回來。”
宮中永不再立後,印一直是由掌握宮權的人暫時保管,聖上寵人歸寵,可也希自己的廷井然有序,現在要鄭玉磬立馬接手這些事自然是難為了,還是等多學些日子才能執掌廷。
“我什麽都不懂,接手宮務,惠妃娘娘教導我怕是會頭疼。”
鄭玉磬想想也覺得尷尬,當日宮選秀,幾個妃位上的子都是坐著相看自己未來的兒媳,如今卻要向們覺得連做皇子側妃都沒有資格的鄭氏行禮問安。
說來也有意思,聖上後宮的子何其之多,有些被寵幸之後都不一定會有位份,若一開始便被聖上中意納後宮,或許還得不到這樣的高位。
Advertisement
“進宮之後要是有什麽不明白的就來問朕,音音臉皮薄,心腸又,們若是笑話你便讓人去找顯德,朕替你置們。”
聖上手裏拿了冒著熱氣的藥,自己執勺嚐了一口,酸苦的滋味確
實是一種折磨,但是這不是鄭玉磬把藥倒掉的理由,“是要朕喂你還是你自己喝?”
隨著一道進來的岑建業以為聖上就是再怎麽寵鄭夫人,了不起也不過是把藥吹涼,沒想到聖上喝了子的安胎藥,幾乎是倒吸了一口涼氣,好在夜如墨,倒也沒教聖上瞧出來。
多虧那裏麵多加的是鎮定心神、助人眠的幾味藥材,又是他眼不錯地看著熬藥,要不然萬一損及聖,他便是誅族也不能自贖其罪。
不過鄭夫人看起來倒是十分平靜,大概與聖上這般相已經習慣了。
“妾自己來。”
鄭玉磬沒想聖上喂,特別是還當著這麽多人的麵,從聖上的手中接過碗,待溫度能口時便屏著氣一飲而盡,苦的藥從嚨大口大口地湧胃部,喝完之後不單是苦得失去了味覺,還有些輕微的惡心,隻能閉著雙,眼淚汪汪地看著聖上。
“怎麽這樣苦?”聖上見吃不了這樣的苦頭,微蹙著眉問岑建業道:“就不能稍微改良些滋味嗎?”
岑建業想給聖上說一說這藥材相生相克、十八反的道理,但話到邊,還是低下頭回稟道:“不若臣製一些丸給夫人備著,多加些蜂調和,可以稍微減輕一些苦味。”
“不是夫人,是貴妃。”
聖上看向地上的太醫,岑家在太醫署也做過幾代了,岑建業立刻領悟了上意,以額地請罪:“是臣唐突
,還請聖上與貴妃恕罪。”
室的侍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所驚,但隨即也都反應了過來跪下,臉上喜氣洋洋,齊聲恭賀貴妃封之喜。
Advertisement
們這些人本來大多數就是從廷裏出來的,要是聖上一直不冊封夫人,那才是件麻煩的事。
“朕記得你荔枝,回去人送來配藥。”聖上看鄭玉磬不吃餞,想起素日的喜好,令人從道觀裏尋些荔枝調了水飲給,溫聲道,“朕知道藥不好喝,但是為了孩子和你安康,這些藥還是要喝,一頓也不許免。”
聖上難得記得一個子喜歡吃什麽,岑建業親眼見識到聖上待鄭貴妃的恩寵,但貴妃仍然是一張苦臉,心裏不覺對這位聖上的寵妃又多了幾分重視。
“長公主殿下日日都要我出去散心,聖上又要我喝藥,”鄭玉磬低聲嘟囔道:“我坐在床上安安靜靜待上一日,什麽藥也不用吃。”
為著聖上駕臨,人仰馬翻鬧騰了半夜,聖上飲了那藥也生出些倦意,讓人都退了出去,自己也不顧規矩,解躺在了鄭玉磬的外側。
“要是聖上能天天過來瞧我就好了,”鄭玉磬覺到聖上間的氣已經然無存,主靠近了幾分,“我做什麽都有人替我撐腰,明天要是長公主再派人來請我,便說是伺候聖上累了,正大明睡上一日。”
“溧也是為你好,想要你高興些,”聖上攬了
人懷,像是哄孩子一樣有節奏地拍著的背,便是當年對待他最喜的兒也沒有這樣耐心細致過:“不去就不去罷,你是貴妃,又是的皇嫂,以後溧也要聽你的話,哪能你依順?”
“我是聖上的嬪妃,算是哪門子皇嫂,”鄭玉磬嫣然一笑,睡意漸漸湧上來,在聖上的拍哄中漸漸困得說不出話來,“住在人家的地方,自然要客隨主便嘛……”
聖上嚐了藥之後困乏,躺在床榻上反而無法睡,雖說多麽大的煩惱見到之後也能輕鬆釋然,可是江山後繼之事並不是躲進這一片溫鄉就能回避的。
他的手覆上鄭玉磬的小腹,聲音低沉醇厚,似乎帶了些歎息:“太子無德,那幾個年的又看不出來有什麽出息,這個孩子生出來之後朕打算留在邊,自己親自教導,音音想日日見到朕並不是什麽難事。”
“那三殿下呢?”嘟囔了一聲,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他不是還救過我的命麽?”
“這個孩子半點也不像朕,反倒是隨了他那個生母多些。”夜深枕畔,溫迷鄉,聖上也會卸去些心防,隨口與道:“但也勝在忠心孤直,若是作為君王手中的一把利刃,倒很是適合。”
岑建業不知道在藥裏加了些什麽,鄭玉磬困得大概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了,也不知道聖上說的是什麽,被人抱著輕憐了一會兒,又
覺得男子的膛太熱了,“好哥哥,我太困了,有什麽事明日再說好不好?”
聖上怔了怔,旋即在麵頰上輕咬了一記,不免自嘲和一個什麽都不懂、對朝事也毫不關心的小子說這些做什麽,放去背睡了。
……
詔書下發到三省,皇帝要冊封新貴妃的消息在朝野傳開,溧長公主聞聽之後雖說吃驚,倒也不算太意外,隻是同鄭玉磬閑聊時會偶爾開些玩笑,心疼宮中的玉瓷綢,調侃果然是個禍水,宮中不知道多子知道這道旨意後氣得要摔砸件。
但是三皇子府中卻並沒有半點沾染喜氣的意思,蕭明稷聽心腹說起聖上這位新晉寵妃的時候正在書房寫字,聞言也不過是停了停,灑不羈的走筆凝滯在那,再走下去便了敗筆。
“聖上對子素來薄,倒不想能為一個外室冒天下之大不韙。”
“是,”心腹恭聲回稟道:“如今坊間新出了不話本,聽聞好些子都對廷向往不已,大抵也是了聖上與貴妃的影響。”
他既然寫不下去,索將紙張隨手卷,親手將廢紙放炭盆,瞧著火舌將紙張上的墨痕舐盡,聖上疑心太重,對子亦是如此,因此除了給那個子寫的信與日常上表,他的字跡從不會落於旁人之手。
“貴妃娘娘果然很有幾分籠絡聖心的手段。”他輕聲一笑:“那些人想爬上榻,總得先攬鏡
自照,看看自己配與不配。”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完結139 章

錦衣之下
雨點打得她頭頂上的蕉葉叮咚作響,甚是好聽,胖貓蹲她肩膀上瞇著眼聽。 雨滴順著蕉葉淌入她的衣袖…… 她仰頭看向陸繹移到自己頭頂的青竹油布傘, 心中不禁有點感動,這位錦衣衛大人總算有點人情味了。 “這貓怕水,淋了雨,怪招人心疼的。” 陸繹淡淡道。 胖貓哀怨地將陸繹望著,深以為然。 “……” 今夏訕訕把貓抱下來,用衣袖替它抹了抹尾巴尖上的水珠子, 把貓放他懷中去,忍不住憋屈道, “大人,您就不覺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麼?” 他沒理她,接著往前行去。 傘仍遮著她,而他自己半邊衣衫卻被雨點打濕。
42.9萬字8 12926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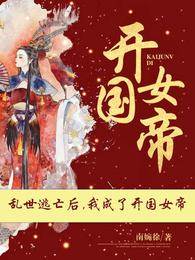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323 章

醫妃仵作鬧翻天
她出身中醫世家,一朝穿越,卻成了侯門棄女…… 從此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她聞香識藥,一手銀針,技驚四座,剔骨剖腹怒斥庸醫,讓蠅營狗茍大白天下。 玉手纖纖判生死,櫻桃小嘴斷是非,誓讓魑魅魍魎無處遁形…… “姑娘?何藥可治相思疾?” 某男賴在醫館問道。 秦艽撥出剖尸刀,“一刀便可!王爺要不要醫?” 某男一把奪下剖尸刀,丟在一邊,“還有一種辦法可治!只要你該嫁給我就行。” 秦艽瞪著他魅惑的臉龐,身子一軟……
58.4萬字8 688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