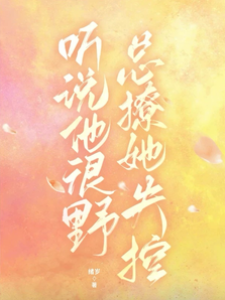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嬌軟美人要抱抱,謝九爺下跪哄她》 第3頁
郁驚畫抬手了自己的臉。
綿綿啊了一聲,好似十分苦惱。
「還不夠嗎?」
「……」
江歡忍著笑移開了視線,知道郁驚畫又開始無辜地氣人了。
許晗被郁驚畫清凌凌的眼認真看著,本說不出反駁的話來。
憋了半天,面對那張濃墨重彩的臉,張了又合,實在說不出違心的話,只能氣咻咻的想走。
剛轉,看到了迎面走來的人,許晗愣了下,「你來做什麼?」
來人是許晗的二哥許思遙。
他看著郁驚畫,目標明確,指間握著一杯紅酒,輕佻又放的舉了舉杯,「郁小姐,好久不見。」
江歡皺眉,上前兩步,半擋在郁驚畫面前。
京南誰人不知道許思遙浪花心的做派,這人之前就沒對著郁驚畫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只是顧及著郁家,沒敢做什麼。
如今郁家困難,想也不會說什麼好話。
「謝九爺馬上要到了,許爺,都是京南人,之後敘舊的時間還長著,我們先走了。」
江歡牽著郁驚畫要走,許思遙還是笑著,卻冷了許多。
「急什麼,謝九爺從來不參與這種場合,不過是個旁聽道說的假消息罷了,還想用來我?」
許思遙擋在們離開去主廳的路上,酒紅西裝大敞,目直勾勾的在郁驚畫上遊走。
「郁驚畫,我知道郁家破產了,沒錢的日子可不好過。」
「正好我還喜歡你,你嫁給我,給我生兩個兒子,保你還能有富貴日子過,怎麼樣?」
Advertisement
郁驚畫攥著酒杯,小聲問江歡,「我能把酒潑他臉上嗎?」
江歡所在的江家也不是什麼大家族,不敢輕易得罪許思遙,只能微微回頭,「不行,他小心眼。」
郁驚畫委屈,「好吧。」
許晗看著郁驚畫那張小臉,說不出什麼心思,彆扭手拽了許思遙一下,「我也聽說謝家主要來了,要不我們還是去主廳吧。」
許思遙直接甩開的手。
酒意上涌,麻痹了他的理智,放大了心的。許思遙鬆了松領帶,又往前走了幾步,目放肆又垂涎。
酒杯中,艷紅酒搖曳,在眼角晃開綺麗澤。
「畫畫,你只要喝了這杯酒,以後就是我許家的夫人……」
郁驚畫側頭看了眼,這是個L型走廊,盡頭就是男洗手間。
從江歡後走出,眼眸純澈,聲調,「喝酒?」
許思遙以為妥協了,興笑著,道,「當然了,畫畫,只要你乖乖的,有的是你的榮華富貴。」
郁驚畫綿綿靠在旁邊牆壁上,眼眸微彎,對著許思遙抬了抬手中酒杯,「那你過來,我和你說句話。」
在許思遙走過來、想附耳傾聽的一瞬間,郁驚畫手疾眼快的拉開旁邊男洗手間的門,一把將人推了進去。
還悄咪咪將手中的酒杯對準人的後背砸了過去。
然後砰一聲關上了門。
指尖一擰一扭,就從外、用掛在鎖孔上的鑰匙把門給關上了。
Advertisement
聽著許思遙在裡面拍門喊的靜,郁驚畫拍了拍手,格外無辜,「許爺可能喝醉了,腦子不太清醒,讓他在裡面醒醒神。」
不等許晗反應過來,郁驚畫已經拉住江歡溜之大吉。
許晗盯著背影幾秒,收回視線,又看了眼正被哐哐拍打的門,心中說不出的煩躁。
「去找服務生開門。」
隨口和後人吩咐了一句,許晗轉就走,也沒多停留。
隨著幾人離開,這塊小地方很快就安靜了下來,只剩不斷響起的拍門聲,和斷斷續續的罵嚷聲。
三樓上,目睹了一場戲的男人收回視線,慢條斯理整理著自己的袖扣。
謝渡被喊上來人時,恰好看到了男人邊還沒散去的一點兒弧度。
「叔叔,喊你下去面。」
謝與微微側頭,那張雕細琢的面容終於展在燈之下,眉眼沉靜疏離,薄微抿,收勢凌厲,弧度冷雋。
他整理好了袖扣,平駁領黑西裝筆,不見一褶皺,白襯衫也一板一眼的扣到了最上方,半掩冷峭結,眼睫微垂,不不慢應聲,「知道了。」
他邁步往樓梯上走,謝渡愣了幾秒才跟上,有些不敢置信的想——他叔叔襯衫領口那點兒紅是什麼?
淺淺的一點兒,似是落在雪地上的紅梅。
如果是京圈任何一個公子哥兒,那無一例外的肯定是人的印。
可這是謝與。
……難道是服本的設計?
Advertisement
謝渡正出神想著,走在前方的謝與卻微微一頓,停住了腳步。
讓他猝不及防之下,險些撞上去。
謝與側頭看他,嗓音低冷,「和藺殷說一聲,一樓的洗手間掛上維修中的牌子,別讓人靠近。」
謝渡更懵了,「洗手間……?」
謝與頷首。
藺殷是他的特助,向來圓明,聽到這沒頭沒尾的命令,必定會探聽清楚,不用說太細,他會明白。
謝與並不打算和謝渡解釋,說完就邁步繼續往下走去,避開人群,徑直進了一樓旁的一個房間。
房間坐著這場宴會的發起人,謝與的母親,沈遐。
Tips: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5 章

難以招架,裴總每天都想強取豪奪
【1V1 雙潔 強取豪奪 強製愛 男主白切黑 天生壞種 追妻火葬場】裴晏之是裴家的繼承人,容貌優越,家世極好,外表溫潤如玉,光風霽月,實則偽善涼薄,是個不折不扣的壞種。他從小就感受不到所謂的感情,不會哭不會笑,就連這條命都是拽斷了一母同胞哥哥的臍帶才留下來。裴家人都說他是沒有感情的瘋子,因此把人送到道觀養了十多年。直到他18歲那年斬獲大獎無數,才被裴家人歡天喜地接回來。都以為他會改邪歸正,殊不知,惡魔最會偽裝。*江予棠自幼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放在人群裏一眼看不到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了裴晏之的私人醫生。都說裴晏之性格溫柔,教養極好。江予棠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兩人交往過程中,他步步緊逼,讓人退無可退。江予棠含淚提了分手。可招惹了惡魔,哪有全身而退的道理。往日裏溫潤如玉的男人像是被惡魔附體,對她緊追不舍,把人壓在牆上,語氣又壞又惡劣,“你要和我分手?換個男朋友……”後來的後來,男人抓著她的手,小心翼翼貼在臉上,嗓音裏滿是祈求,“棠棠今天能不能親一下?”從此以後,上位者為愛強取豪奪,搖尾乞憐。【沉默寡言醫學天才女主X表麵溫潤如玉實則陰暗瘋批偽善涼薄男主】
22.6萬字8.18 17507 -
完結72 章

遲來童話
城南池家獨女池南霜從小千嬌百寵,衆星捧月,是洛城圈內出了名的矜縱任性。 偏偏在二十四歲生日這天,被池老爺子安排了一樁上世紀定下的娃娃親,未婚夫是洛城地位顯赫的謝氏掌權人謝千硯,據說明朗俊逸,只是鮮少露面。 衆人皆道這門婚事佳偶天成,老爺子更是態度堅決。 氣得她當場把生日皇冠扔在地上,放言: “我要是嫁給謝千硯我就不姓池!” 抗婚的下場是被趕出家門,千金大小姐一朝淪落爲街頭商販,自力更生。 在屢屢受挫之際,是隔壁的窮小子宋宴禮多次出手相助。 對方溫柔紳士,品貌非凡,且人夫感十足,除了窮挑不出別的毛病。 相處中逐漸淪陷,池南霜毅然決然將人領回家。 老爺子聽說後,氣得抄起柺杖就要打斷這“軟飯硬吃”小子的腿。 然而柺杖卻沒能落下來—— 窮小子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熟悉的臉。 “爺爺,”他溫柔地笑,“不是您說,只要我把南霜追到手,這門親事就還算數嗎?” 池南霜:???
24.8萬字8 160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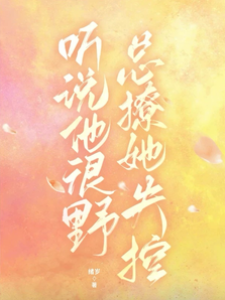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