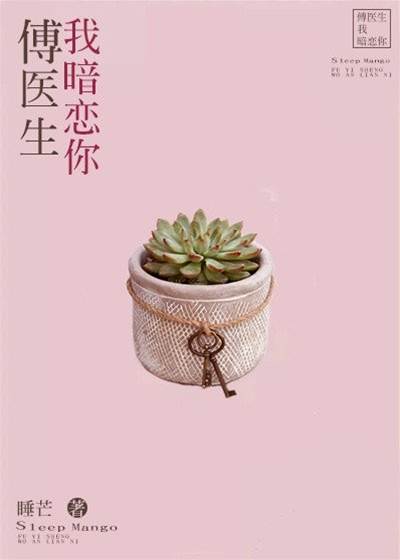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方尖碑》 第10章 微笑瓦斯 06
總管的胡子和眉伴著他的一起抖了幾下。他看向莫名其妙消失了一個人的營房,再看向說了“把我也關進去”的上尉,最后留下一個惻惻的笑容。
“我認為還是要把這幾個人抓起來,嚴刑拷打,”他用手指撥弄著門上的銅鎖,發出哐哐的聲音說,“他們在我們找不到的地方挖了地道,不然一個人怎麼會無緣無故消失在房子里?”
說罷,他斜眼瞧著營房里的幾個人:“誰能第一個說出那個雜種怎麼逃跑了,我發誓他在收容所解散之前,都會得到比咱們這位上尉還要優厚的待遇。”
所有營房都發出了聲,顯然是被“收容所解散”這個詞激起的。
總管對此報以“果然如此”的笑容,然后用更加兇惡的目視營房里的每一個人:“你怎麼想,大個子?還有這位戴眼鏡的先生,你們到底把地道挖在了哪里,天花板?”
他們都沒有說話。
事實上,不論說什麼,都沒有好的結果。
告訴總管,每到午夜十二點,這座營房就會進另一個與白天不同的時間嗎?
這樣做只有兩個結果。要麼,總管認為這些科羅沙人在用拙劣到令人發笑的理由來搪塞他,繼而然大怒。要麼,總管相信了這個說法,把他們轉移到了別的營房——那他們就失去了在夜間探查整個收容所的機會。
如果總管知道他們在夜間走遍了大半個集中營,并看到了那些劇毒的化學藥劑與二樓的解剖臺,他們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
當然,也不排除有人愿意供出來,以此獲取那個“優渥的待遇”。
“他每天都會得到滿杯的牛,涂滿黃油的面包,不必再用勞贖罪……”總管的目從一個人移到另一個人:“你知道他怎麼逃掉了嗎?大鼻子,你的鼻子像一個蟾蜍那麼大。”
Advertisement
郁飛塵的余看著那個大鼻子男人——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和他們一起出去的人,只是旁聽了他們回到營房后簡單代的彼此況。這人自然也不知道修士所謂的“消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形。或許,他還真以為修士功逃了。
總管似乎看出了什麼,目在大鼻子上停止不,而大鼻子的脊背并不直,目略有閃躲——郁飛塵快速掃過這間營房里的兵力況,如果大鼻子真打算出賣他們,他得做好最壞的準備。畢竟從昨晚來看,這是個極度膽小的人。
這時候,他看見那位上尉也有了一個微小的作——他的手指按在了配槍柄上。
就在這時,大鼻子的囁嚅了一下。
郁飛塵微蹙眉——
大鼻子咳嗽了兩聲。
“我沒看見什麼。”他甕聲說,“長。”
總管從鼻子里哼了一聲,目轉到郁飛塵上。
“這里沒有地道,”郁飛塵說,“您可以隨意搜查。”
“誰知道你們科羅沙人在玩什麼把戲,或許是用了什麼惡魔的法,”總管背著手在門外踱步:“偏偏是你們這間營房出事,我得換個地方把你們關起來——”
話到一半,卻又停下了,換他常有的那種沉的笑容:“過了今晚再換也不遲,畢竟我們英明神武的安菲爾德上尉要親自探詢你們消失的原因。”
原來這位長名安菲爾德,不是個很難記的名字。
總管拿出鑰匙給他們開門,那個昨晚被強行撬開的銅鎖現在完好無損:“贖罪去吧,叛神之人。”
經過安菲爾德邊的時候,郁飛塵聞到了與昨天別無二致的冰雪寒意,只是多了一鮮的氣息。
俘虜們一天的工作開始,但今天的營房里已經有至十人起不來。他們中有的是因為昨天勞累過度,難以站立,有的則是因為被鞭打后的傷口在的營房里發炎流膿,導致高燒不退。
Advertisement
他們在地上痛苦的時候,郁飛塵正從營門離開。清晨的寒氣撲面而來,他微微側回,目穿過重重營房,見那位安菲爾德上尉的影佇立在一片塵埃彌漫的昏暗中,只有鉑金的長發出微。
總管手持皮鞭,正要驅趕其中一個人站起來。下一刻他一轉頭,瞥到安菲爾德,角搐一下,揮鞭的作頓了頓,最終沒有做出。
“這就是真理神對叛徒的懲罰。你會流膿到發臭。”他對著地上不止的科羅沙人啐了一口。
郁飛塵離開。
很多時候,神是借口而非真實。這也是他始終無法對樂園里的那位主神產生實的原因之一。
磚窯的工作還像昨天一樣。唯一有變化的或許只有那幾位當地看守。他們昨天還只是懲罰不賣力干活的人,今天已經演變對任何看不慣的科羅沙人下手。皮鞭聲比磚塊的撞聲還要頻繁。那種牲畜一樣的屈辱又出現在了每個科羅沙人臉上,但這只能招致更殘暴的毆打。
午間短暫休息的時候,郁飛塵的手輕輕搭在一個亞麻頭發的男人肩上。
“如果他背對你,”他用只有他們兩個能聽到的聲音道:“用一塊磚頭干掉他,你可以嗎?”他的目看向磚窯門口拿槍的衛兵。
那男人轉頭,用警惕的目看著他:“你要做什麼?”
“看守手里只有鞭子,我同伴能把他們放倒,”郁飛塵說:“還差一個人,幫我搞定那兩個衛兵中的一個。”
“你瘋了嗎?”那男人說:“衛兵隊會給他們報仇的。”
“那時候我們已經消失在橡山里了。”郁飛塵說。
“你要逃走?”
“不然呢?”
那男人猶豫片刻,搖了搖頭:“他們會殺了我們的。”
Advertisement
——郁飛塵已經第四次聽見這個答案了。這半天的時間他都在觀察自己的俘虜同伴們,找到看起來過訓練并且有勇氣的幾個,但是無一例外,都被拒絕。
帶所有人集逃出不是完全靠他一個人能做到的事。但同伴們的心難以控制,這不是郁飛塵擅長的差事。
他聲音大了一點兒,對那男人說:“沒關系。”
這聲音驚了持槍的衛兵,那個大塊頭衛兵轉過頭來大喝一聲:“雜種,你在做什麼?”
“報告長,”郁飛塵說,他用上了那種常年混跡雜牌軍隊的人會染上的口音,“我們在打賭,如果公平比武,是您撂倒我,還是我撂倒您。”
那位衛兵像聽到笑話一樣咧開了,鼓起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他,迸出興又殘暴的神,用野的語調道:“我會讓你這輩子都沒法再下窯子,雜種。”
“那我的夫人大概會很高興。”
“你的老婆會比你的姘頭們更生氣,小子。”
“我不想和磚頭打道,長,”郁飛塵看著他的眼睛:“您也站了四個小時了。”
他轉而用律師特有的彬彬有禮的真誠腔調說:“這地方比窯子無趣太多。”
這話顯然正中了衛兵那位的下懷,他咔噠一聲解開配槍的系扣,把它丟給同伴。
“滾開,雜種們,”他說:“最后想念一次你老婆的脯吧,小子。”
周圍的科羅沙人用惶恐又驚懼的目看著這一幕。郁飛塵直視那位士兵,活了一下筋骨。關節咔咔作響,郁飛塵笑了笑,他沒什麼東西可想,也不太喜歡這種下流句子。
——但現在和衛兵對峙,還從“雜種”變“小子”,接下來的事只需要用拳頭解決,這種覺比營房和磚窯舒服多了。
Advertisement
他接了話,說:“我已經想念完了。”
“你要是能挨住我三下,”衛兵把腰間的酒袋也解下來,丟在地上,“今晚你就能喝醉一次,壞小子。”
郁飛塵沒說話,把灰工作服襯衫的扣子解了兩顆,左手稍稍在前抬起。
他還不知道這個世界赤手搏斗的風格,但是——
一聲怒吼由遠及近過來,沒有任何佯攻,一記野蠻到了極點的掄拳從郁飛塵左上方砸了下來!
郁飛塵剎那間飛快側,左手肘抬起,和衛兵鋼鐵一樣的右手腕沉悶相撞。整條胳膊的骨頭都在劇震,他咬牙關,生生扛下了那一刻的發力。與此同時,右瞬間發力,一記凌厲的低位側踹正中對方小骨!
衛兵那碩大的塊頭差點一個趔趄,人在左吃痛的時候,會反揮右拳——
半秒鐘后,右邊的影當頭罩了下來,鋪天蓋地,這一拳如果打實,當場人就廢了。
但郁飛塵等的就是這第二個右拳!
他不是左撇子,右手比左手好使。所以早在最開始就放左手在前,引對方右拳來攻。而對面揮右拳的時候,左邊必然是空檔——他抓住那轉瞬即逝的破綻,不留任何余力,右手拳狠狠砸在衛兵的左太上!
論力量,這位年輕律師當然比不上衛兵那烙鐵一樣的拳頭,但用這手的人是他,也夠用了。
一擊即退,趁衛兵頭部擊,郁飛塵快速和他拉開距離。當然,力量反震,他的手也麻了半邊。
他用右手比了一個“1”。
只見衛兵猙獰地笑了一下,追擊上來,出直踹!
這衛兵骨架大而沉,極為發達,重可想而知更為可怕。型的差距在搏斗里幾乎不可逾越。風幾乎是呼嘯而來,這一條的力量足以折斷一個正常型人的脊椎。不過,這也限制了他的速度——而下部防守的最好方法,只有上進攻!
出拳原本就比出快,這次,郁飛塵的左拳打中了他的右太。
同樣,吃痛的人作會有稍微的遲緩,郁飛塵步伐再,在三步遠的地方,緩緩比了“2”。
衛兵的雙眼出紅,不再咧笑了,而是緩緩把右手橫過前,做了一個防守的作,意思是,你來。
——他就那樣微躬防守,小山一樣的形鼓脹,堅不可摧。
這樣的防幾乎無法突破,但現在才算變了郁飛塵最擅長的局面。絕大多數況下,只有他主打人的份。
再加上先前那正中頭部的兩拳,已經讓這衛兵對他有了心的畏懼。畏懼的下一步就是躲避。
他上前,右左拳同時虛晃!
衛兵早有準備,側移步躲開,右在前,左在后,右拳橫掃!
郁飛塵向左閃,左側踹,這時衛兵的拳頭離他左邊膛只有一寸之差。
只見他忽然擰向前,生生吃了這一拳!
骨相擊的聲音沉悶炸開,幾乎能聽見骨骼的碎裂聲。沒有一個人敢出聲,科羅沙人們的目瞬間充滿絕。
就在這時——
郁飛塵左還沒收,整個人騰空躍起,同時扭轉,右小帶著整個的重力直直撞上對方右膝彎側面!
郁飛塵落地。右邊從肩膀發出劇痛。
但他落地是穩的,衛兵則斜著打了擺子。
換郁飛塵笑了一下,拇指與小指并起,比了一個“3”。
這是他們約好的,三下。
衛兵卻從膛里發出隆隆的聲音。
“再來。”
郁飛塵說:“好。”
又是三次。
這次結束的時候,他左邊胳膊也挨了一下,沒站穩。
但對面斜著趔趄了好幾步才停下。
“再來。”
“好。”
人群中傳來一聲泣聲。誰都看得出來,兩人抗擊打的能力是不同的,就算占了上風,也沒人扛得住一直繼續下去。
這位大律師的縱然鍛煉得宜,但和刀口的士兵相比,也僅僅是“得宜”了。
這次傷的地方換了右腹部。郁飛塵嚨里翻涌著味,眼前一陣陣發黑,就像剛剛的打斗完全是靠意志力支配著這,一次次突破速度和力量的極限那樣,他現在也全靠著意志力才站住。
猜你喜歡
-
完結581 章
總裁的午夜情人
黑暗房間,男人將柔軟甜美的女人壓在牀上,溫柔又瘋狂,不顧她的求饒…第二日他全酒店通緝,發誓找到昨夜青澀又惹火的女人."我娶你!"身邊的女人層出不窮,他最終伸手指向了她,這一刻她以爲找到了幸福,滿懷期待嫁給他,可後來才知道,他要的不過是一份天價遺囑.
141.9萬字7.91 87363 -
完結49 章

寵壞
人人皆知的槐江19部BOSS沐則,清心寡欲,陰晴不定,二十八年來高嶺之花人設屹立不倒。 直到他遇見了檢察官沈夏時。 * 兄弟們玩真心話大冒險,問及沐則這輩子什麼時候最難熬。 沐則喝了口酒,想起昨夜的沈夏時。 她摟著他的腰,桃花眼水霧朦朧,出口的嗓音甜膩溫軟:“老公,抱~” 要他的命! 狂野桀驁的沐大爺遇見沈妖精 一身鐵骨,滿腔柔情 寵與愛都是她的 “她如煙似酒是禁果,萬分的著迷上癮。” 一個向野而生和柔情蜜意的故事 雅痞壞男人x辛辣小妖精
20.9萬字8 10637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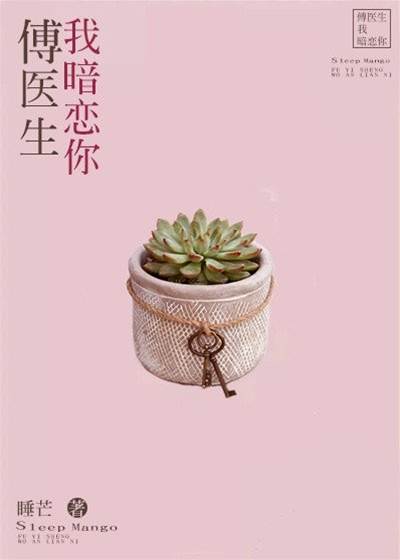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