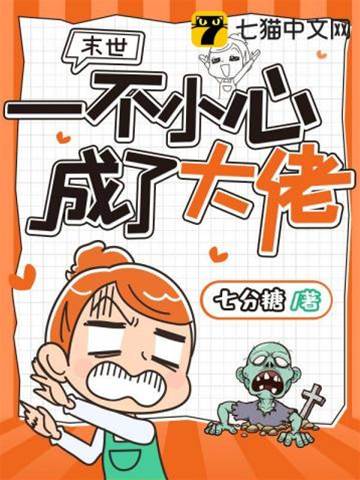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沾青》 第十四章
林瑯覺得冬天是個很奇怪的季節,它總能讓人下意識回憶過去。
也會想起一些過世的親人。
只記得外婆,所以最近常常想起外婆。
外婆說,興許是祖上沒給們積什麼德,所以沒人保佑,們祖孫三代才會都過的不如意。
外公是在林瑯媽三歲的時候離開的,和當時同在一個制廠上班的工人一起走的。
他們高呼真無罪,臨走前還不忘把家裏最值錢——外婆的嫁妝手鐲給走。
因為沒有父親管教,外婆忙著賺錢養家,所以林瑯的媽媽就變得不學無,初中還沒畢業就輟了學。
後來發生的事,也並沒有出乎誰的意料。
按照的格,好像這一切都是合理的。
唯獨林瑯的出生不太合理。
「我們小瑯會幸福的,肯定會幸福。」
外婆如此篤定。
黑的平治車,林瑯坐在副駕駛,著暖氣從腳邊往上涌。
徐初開車很平穩,幾乎不會出現突然急剎的狀況。
林瑯也能安心在他車上睡覺。打了個哈欠,拉過衛連帽蓋過頭頂,子弓了弓,整個人進車椅里。
像只慵懶的貓。
安靜的車,此起彼伏的,三道不輕不重地呼吸聲。
其中一道,來自坐在車后的蔣杳。
懷裏抱著包,那隻中古店淘來的Fendi托特包。
為了和那個男人離婚,把自己的全部家都快搭進去。
那是父親在進去之前留給的錢。
可是現在,一無所有了。
蔣杳眼神落在副駕駛座上,一種難以言喻的酸突然往上涌。
在國外的時候,反悔過很多次。
當初自己執意堅持要出國,和那個男人一起,徐初來找過很多次。
他每次也不說很多的話,只是告訴,那個男人不好。
Advertisement
男人看男人的眼,向來錯不到哪裏去。
可蔣杳不聽啊,是一生都被關在籠子裏的雀鳥,在家庭的束縛下溫順乖巧。
那個男人,是這輩子做過最叛逆的事。
像是把自己的所有勇氣都賭在了他上。
賭自己的叛逆沒有錯。
最後一次,是在決定了出國日期,並告訴好友,未來可能會在那邊定居,應該不回來了。
是在當天下午,徐初又來找過。
他那個時候年紀還小,上大學的年紀,一件深藍的牛角扣大,裏面是件同系的,頭髮打理的很短,甚至出了一點淡青的頭皮。
本該是青春洋溢的年紀,但他在那一刻,卻好像被什麼碎了脊樑。
眼睛暗淡無關,憔悴到好像下一秒就能倒下。
他問:「能不能不走?」
已經放棄勸說,那個男人不行。
而是求,別走。
蔣杳搖頭,沖他笑笑,說:「阿震,祝你快樂。」
現在想起來,如果當初能在他問出這句話的時候點頭,事的走向會不會發生改變?
也不至於落得如今這個境地。
是啊,就像徐初說的那樣。
太晚了。
是回來的太晚了。
兩人之間總有一條不過去的渠。
至於那道渠。
再次看向副駕駛,那個睡中的孩。
吃飯的地點是在徐初中途接到的那通電話后,修改了方向。
大約今天是誰的生日,徐初在電話中一直推拒,可又實在執拗不過。
對方一句:「我連阿都來了,你必須得來。」
周磽出了名的纏人,又鬧騰。裴清喜靜、討厭吵鬧,可是他又沒什麼脾氣。
能想到,他被纏到無奈,最後鬆口同意的神。
當然,徐初自然是同意了。
在徵求到林瑯和蔣杳的同意后應下的。
Advertisement
林瑯無所謂,去哪吃都一樣。
蔣杳更是樂意至極,先前那些名義上為接風的飯局上,不多都是些想以此為由,借當跳板往搭上徐初的微末人。
這次來的才是真正意義上,多年未見的朋友了。
車子拐進了一條安靜的道,路兩旁豎著的都是些老洋樓,門前還種著幾棵梧桐。葉子早掉了,看著空落落,為這嚴寒冬日添幾分蕭瑟。
看起來毫不起眼。
可路邊梧桐樹下停著的那幾輛林瑯說不出價格的豪車,好像給這地界兒抬了不價。
至於,是車給房子抬價,還是房子給車抬價。
林瑯這個沒見過世面的窮人也說不明白。
周磽今天過的是二十歲生日,要不是他老子停了他的卡,不許他鋪張浪費,他也不至於在他家
地過。
外面看著老舊,想不到裏面完全是另外一種模樣。
低調中帶著一種不刻意顯的貴氣。
周磽一見著徐初就跟見到親人一樣,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述說起他爸到底有多過分。
自己不就是飆車的時候不小心把人給撞了嗎,又沒死,賠點錢不就得了,至於還把他所有的卡都給停了。
他現在落魄到都快賣車了。
林瑯看著角落男混的場景,無聲的將眼神移開,改為去看牆上的那副畫。
周磽同樣也注意到林瑯了,一同注意到的,還有一旁的蔣杳。
早前他就聽誰提前一,聽說蔣杳回來了。
他本來還好奇徐初這個正人君子會怎麼理這段詭異的關係。
想不到這人居然直接給整「平衡」了。
周磽角著意味深長的笑,拍了拍徐初的肩膀:「還是震哥牛啊,我這麼玩的人都沒想到還可以兩個人一起。」
徐初眉頭皺著,手拿開他放在自己肩上的手。
Advertisement
被這麼冷淡的對待,周磽倒不意外。徐初這樣從小就這樣,一副好學生模樣。
他和他玩不到一塊去。
聳聳肩,臉上笑容仍舊弔兒郎當,轉頭又去調戲林瑯。
畢竟這兩個人在徐初的心中孰輕孰重,他們心裏可都跟明鏡似的。
蔣杳就是一朵誰都不得的花,在徐初那兒一整個乾淨白月。
誰他能和誰拚命。
自己還沒蠢到去他的逆鱗。
林瑯正看著牆上的畫發獃。
想不到這幅畫居然會出現在這裏。
當時流落在拍賣會上,開著電腦看完了整場直播。
只知道這副畫最後被人以三千萬的價格拍走。
是很喜歡,很喜歡的一個畫家。
比莫奈還要喜歡。
直到那個時候才慨,有錢真好。
周磽和搭話,對方卻一直沒回應,好像所有注意力都被放在了那幅畫上。
他覺得無趣,長得漂亮,格卻像塊悶木頭。
「這畫是別人送的,我七十大壽的壽禮。我是欣賞不來,不過老人家喜歡。」
周磽拿出煙盒,敲出一來,叼在裏。
林瑯這才肯給他一點回應,垂下了眼去看他。
周磽見這反應,突然樂了。
裏的煙沒叼穩,掉在地上,他有點兒潔癖,不許地上有任何髒東西,彎腰正要去撿。
門開了。
外面的冷風滲進來,像是一縷輕薄煙霧,只有短短的一截,沒過指尖,繞到耳後,便沒了蹤影。
比寒冷更讓人記憶深刻的,是足以讓喧鬧場子安靜下來的聲音。
時刻溫和,又帶著分寸的禮貌:「打擾您了。」
老婦人笑著央他進來:「回回來都這麼客氣。」
毫無意外,短暫的寂靜代表了所有人對前來之人的重視。
包括正和林瑯調侃的周磽,他一挑,歪歪頭:「送畫的人來了。」
Advertisement
然後熱過去,挽著男人的胳膊便不撒手:「大忙人啊,回來這麼久了,就這一回把您給請出來了。」
裴清並不擅長在這種人人都長袖善舞的地方社。
今天也是實在招架不住周磽的磨泡,才肯鬆口同意。
「工作有點忙。」他輕聲笑笑,然後不聲從他的臂彎中,將自己被抱的左手出。
簡單整理好剛才周磽一番作下來,扯歪的服領口。
與此同時,他的視線也落在了正好站在他對面的,林瑯上。
旁邊是紅牆,紅牆上掛了畫。
上世紀歐洲某位畫家臨死前最後一幅作品。
早年間裴清參加某場拍賣會拍下的。
林瑯大約是在好奇,這邊的靜,所以視線短暫移過來。
此刻就在他上,兩個人的視線恰好對上。
裴清因為這個視線,沉默了幾秒。
面上卻並無異樣,只是沖點了點頭,以此當作,最基本的招呼禮儀。
他確實是個進退有度的男人,哪怕再不喜,也不會過多表現出來。
這是林瑯從他剛才對待周磽的態度中悟出來的。
他看上去應該是不喜歡被外人這般親的,卻還是好脾氣的溫聲和他對話。
本場宴會最重要的人都到齊了,其他那些無關要的人便無人在意。
周磽跑樓下讓阿姨可以準備上菜了。
座位的安排像是有意為之,竟然分別將林瑯和蔣杳放在了徐初的左右兩側。
徐初是個斂子,鮮發脾氣,此刻卻黑著臉,與林瑯換了座位。
那邊周磽嬉皮笑臉道著歉,說是自己疏忽了。
被徐初一道冷冽眼風給嚇到不敢多,只得假意去和邊的妹妹親熱,藉此來緩解尷尬。
可是這種修羅場,哪裏是換座位能解決的。
林瑯和蔣杳坐在一起時,其實也沒多相似。
五雖然大同小異,可兩人風格全然不同。
蔣杳看著溫婉約,上有種象牙塔中長大的大家閨秀風範。
而林瑯,那雙眼睛空落落的,像是一汪不見底的清泉,無論什麼東西掉進去了,連個響都聽不到。
周磽之前還疑,這蔣杳都回國了,婚也離了,擺在面前的機會就等徐初一句話。
結果這人也不知道爭取。
以前那些付出都打水漂了?
現在看到替本尊,又突然明白過來他為什麼遲遲不肯和人提分手。
這麼好看的妹妹,而且還年輕,那小臉蛋,到好像手就能掐出點水來。
擱他,他也不捨得。
徐初給林瑯擺好碗筷,中途來了電話。
他最近在忙一個案子,所以電話不斷。
他出去接電話了,剛才顧及他在場不敢吱聲的人,此刻都像是衝破了牢籠的鳥。
問題那是一個接著一個。
尤其是周磽,他向來看熱鬧不嫌事大。
並且今天還是他的主場。
——他是壽星。
料想徐初到時候生氣,應該也不會多說什麼。
保姆拿著酒上來,周磽說專門給蔣杳調了一杯白蘭地庫斯塔,知道最喝的就是這個。
他又堆砌著笑去問林瑯:「我看林瑯好像也長了一張喜歡喝白蘭地庫斯塔的臉,所以就自作主張替你也調了一杯。」
這話隻字不提和蔣杳的事兒,卻都往那個痛上。
像是在反覆提及,徐初之所以和在一起,也是因為那張和蔣杳相似的臉。
林瑯沉默不語,安靜等著。
等著那杯白蘭地庫斯塔端上來。
有點冷,手指輕輕蜷著,微不可察打了個冷。
往日總溫和的聲音此刻雖然仍舊沒有多大起伏,但語調卻稍微往下沉去幾分。
引得席上眾人都不敢大聲說話,生怕把他的聲音給下去。
「天冷,給我來杯熱牛吧,麻煩了。」
這話是和負責酒水的阿姨說的,客氣禮貌。
他沖林瑯笑笑,「別人都喝酒,只有我一個人喝牛,好像有點奇怪,你要來一杯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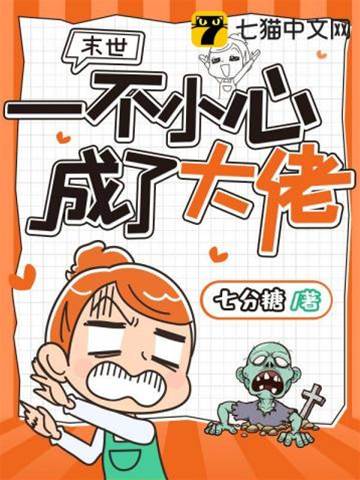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740 章

團寵大佬:真千金又掉馬了
林笙一出生就被扔進了大山里,被一個神秘組織養大,不僅修得一身好馬甲(著名設計師、格斗王、藥老本尊……),本以為有三個大佬級爺爺就夠炫酷了,萬萬沒想到,叱咤商場的殷俊煜是她大哥,號稱醫學天才的殷俊杰是她二哥,華國戰神殷俊野是她三哥,娛樂圈影帝殷俊浩是她四哥。某天,當有人上門搶林笙時:爺爺們:保護我方囡囡!哥哥們:妹妹是我們的!傅西澤一臉委屈:笙笙~我可狼可奶,你確定不要嗎?林笙:我……想要
131萬字8 269482 -
完結1602 章
丑妻逆襲夫人火遍全球了
云綰是被父母拋棄的可憐女孩兒,是她的養母善良,將她從土堆里救了出來。在漸漸長大的過程中,..
142.6萬字8.18 448598 -
連載424 章

咬色
爲了讓她乖乖爬到跟前來,陳深放任手底下的人像瘋狗一樣咬着她不放。 “讓你吃點苦頭,把性子磨沒了,我好好疼你。” 許禾檸的清白和名聲,幾乎都敗在他手裏。 “你把你那地兒磨平了,我把你當姐妹疼。” …… 她艱難出逃,再見面時,她已經榜上了他得罪不起的大佬。 陳深將她抵在牆上,一手掀起她的長裙,手掌長驅直入。 “讓我看看,這段日子有人碰過你嗎?” 許禾檸背身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笑得肆意淋漓,擡手將結婚戒指給他看。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71.8萬字8.18 13158 -
完結283 章

大佬的白月光又野又狂
不小心上錯大佬的車,還給大佬解除了三十年的禁欲屬性。盛晚寧正得意,結果被大佬一紙狀告,進了局子。她憤憤然寫完兩千字懺悔書,簽下絕不再犯的承諾,上繳五千元罰款……暗咒:厲閻霆,有種你別再來找我!……一年後。厲閻霆:“夫人,你最喜歡的電影今晚首映,我們包場去看?”她:“不去,你告我啊。”……兩年後。厲閻霆:“夫人,結婚戒指我一個人戴多沒意思,你也戴上?”她:“戒指我扔了,有本事你再去告我!”……五年後。厲閻霆:“夫人,老大已經隨你的姓,要不肚子裏的小家夥,隨我,姓厲?”她:“憑什麽?就憑你會告我?”……
72.7萬字8.18 132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