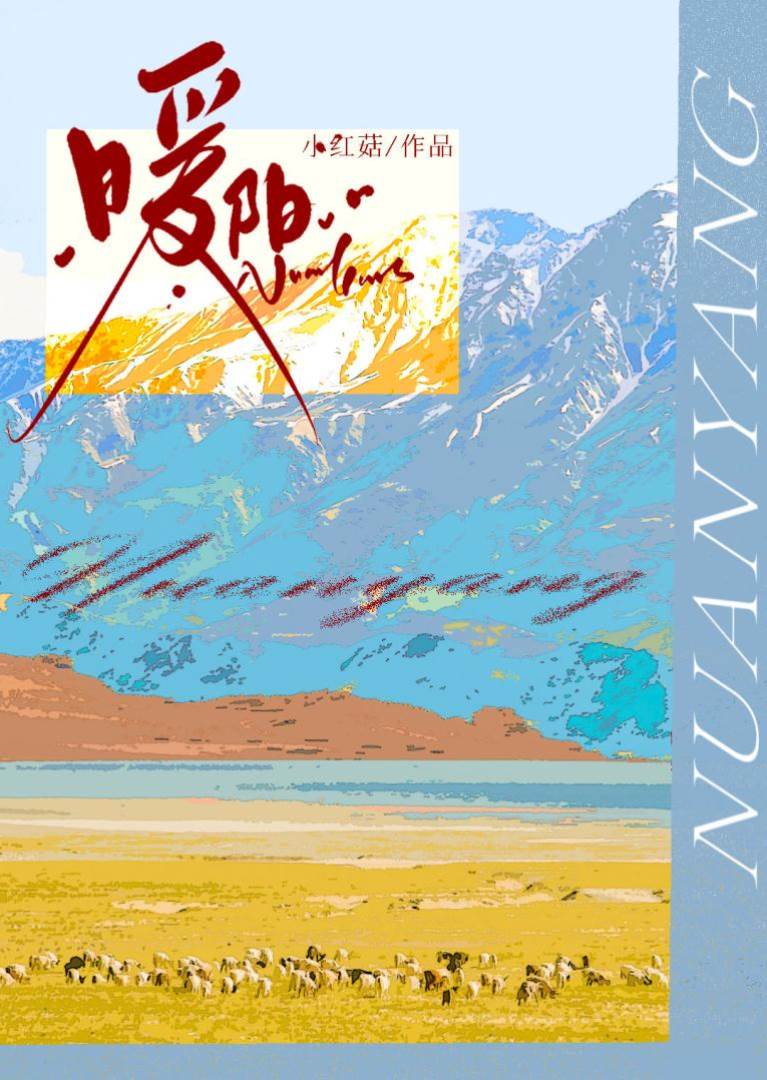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晨昏游戲》 第20章 第20章
雖然并不是實時通話,但是空氣里短暫的安靜還是讓懷歆不住了手機。
食指屈起,輕輕慢慢、有一搭沒一搭地在桌面上輕叩。
心口的躍維持在一種稍微有些急促的頻率,懷歆瞇著眼,沒有太多患得患失的張,更多的是來自終將要短兵相接的興。
給彼此留足了余地。
實在大不了就再換一部電影——片子這麼多,總能尋到稱心的。
而同時也在賭。
賭循序漸進的過程被拿住了節奏,他會縱容地跟著混淆了邊界,有意愿沉潛向更深的海域。
郁承留給懷歆自我揣測的時間并不長。
也就是幾分鐘的間隙,他撥了語音通話過來。
懷歆趴在床上,翹著小晃了晃,笑問:“怎麼樣,回想出來了嗎?之前看沒看過這片子呀?”
最關鍵之不在于看沒看過,而在于他們想讓彼此怎麼認為。
男人輕笑一聲,幾分興味:“我說沒看過,你信麼。”
懷歆一愣,邊弧度更上一層樓:“是嗎?還有Alvin先生沒看過的電影啊?”
他顯然諳于此道,不答反問:“那你看過麼。”
語氣輕快,斷然道:“當然沒有,不然剛才也不會問你了。”
郁承又笑了,對的說辭不置可否。他們在網上找到資源,懷歆還沒說什麼,他就開口問:“想看哪種版本?”
嗓音低緩,語氣還頗自然,仿佛真的只是簡單征求的意見似的,懷歆心中沒忍住一凜,而后反應過來,調笑道:“當然是未刪減了。”
有些嗔怪似的,好像他明知故問了。
他沒再說什麼。電影前奏響起,厚重的管弦樂鋪陳出20世紀40年代上海街頭的景,氛圍凝肅,人們面目疑詭,接著浮現兩個懸著的紅字。
Advertisement
戒·。
Lust,Caution。
懷歆還真沒看過這部電影。
準確來說,是不知道背景。
——上高中那會兒有次在閨家借住,趁著夜黑風高地搜了未刪減版來看。
當然,只看了床戲。
兩人躲在被窩里激地小臉通紅,大呼刺激。
想起來竟有點可笑,當時的注意點都放偏了,竟然完全沒留意這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那個年代戰爭不斷,民不聊生,黨派相爭,軍閥橫行。
絕不像表面上的平靜這麼簡單,在任何看不見的地方都有危機,波云詭譎就藏在人的笑靨里,每一出荒腔走板的黃梅戲里,每一張牌桌上的暗涌中。
每一個無聲的作,每一個意味不明的眼神都傳遞著語言。人心隔著墻,信任更稀缺,易先生從頭到尾都知道王佳芝是蓄意接近自己。
一個大學生偽裝闊太太,留下了太多把柄和。
易先生看破不說破,微笑著看拙劣地表演,看小心又謹慎地重復那些別有用心的謊言。與曲意逢迎,聲人間。
王佳芝是有天賦的,初游戲場,眼角眉梢的風卻能把握得恰到好。易先生原本不甚在意,卻也漸漸勾起興趣,想陪玩一局。
但時局,王佳芝沒能來得及施展任何,便錯失了良機。已經犧牲了太多,心有不甘,于是幾年后,重新回到易太太邊,更是借著這層關系住進易家。
早在三年前便開始的暗度陳倉兌現得水到渠。
第一場戲開始得猝不及防,但遠和懷歆記憶中的觀不一樣。
易先生并不溫,甚至十分暴。他用皮帶從后面捆綁住王佳芝的手腕,著的頭發,從頭到尾臉龐毫無半分,嚴酷冷峻到像是在行刑。
Advertisement
疾風驟雨,一場推拉到極致的試探,有一瞬間懷歆看到他的神皸裂出一罅隙,像是探下去,只看到深不見底的海面。
易先生冷漠地將風扔在王佳芝上徑自離開時,懷歆將一旁的薄毯扯過來蓋到自己上,覺得有點冷。
郁承的呼吸聲就在耳畔,時近時遠。
沒有人出聲。
易先生生多疑,為偽政府高,必須高度繃神經,和王佳芝之間也是你進我退,真真假假分不清楚。
王佳芝等了許久等來第二次。
灰的房間里,沉,抑,他仍舊掌控著,這次正面相對,他掐著的下頜,始終不讓擁抱自己。
他要看著,正如他從不將自己的后背給任何人。糾葛的肢語言,赤相搏并未帶來的愉悅,汗水淋漓的臉龐上替閃過猶疑和恐懼,手背上青筋迭起,強勢和脆弱只有一線之隔。
兩人隔著一段距離對視,那種眼神讓懷歆如墜寒窖。
——好痛。
痛和快在疊中綻放,最后的剎那,王佳芝不顧一切抱了他。兩人如襁褓之嬰的姿勢相擁,長時間的抖,息,流淚,像是兩尾快要旱死的魚。
相擁的那一刻,很短暫的間隙,易先生的神并未設防。而王佳芝的臉上也僅存空茫。
那瞬間忘了自己所承擔著的重負,忘了世事艱難,忘了自己被父親拋棄,忘了自己曾為傾心的男人付出過的不對等的。
懷歆裹了上的被子,蜷在沙發一角,慢慢地舒緩自己的呼吸。
頭被扼住,這樣骨的場景卻說不出任何撥挑逗的話來。
不知是在哪聽過的一句話,“相對的時候并不一定要心意互通”,但是的時候心靈也會在不知不覺中靠近。
Advertisement
第三場戲在某種程度上是殘酷的,將這種心理上的極致掙扎撕裂。槍就懸掛在離床不遠的墻邊,王佳芝用枕頭蒙住易先生的眼睛,他并沒有反抗。
只是頃,流出痛苦不安,像要不上氣似的。
懷歆覺得痛又覺得冷,不知道為什麼當初這樣年無知,忽略了這麼多的細節。理智與的強烈拉扯,不到答案的荒蕪,生逢世無無依的浮萍,只有相擁時的最覺真實。
郁承的吐息自耳畔沉沉地落下,很緩慢,像是重石投深海,懷歆一激靈,抱住自己的雙膝,想象著自己此刻也被人擁在一起相互取暖。
王佳芝在藝伎館為易先生唱《天涯歌》,“郎呀,穿在一起不離分”,易先生喝了遞過來的茶,沉默的對視中有久違的脈脈溫,也有閃爍的淚。
王佳芝在暗殺行那天將易先生放走了。出來的時候就知道自己難逃一死,步伐卻輕松釋然。其實易先生也給過很多次機會,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之間相隔著的終究是道天塹。
影片最后,是易先生對著王佳芝曾睡過的房間最后一回眸。
深沉難語,人間種種,皆在不言中。
終曲散了,影職人員表依次浮現。卻遲遲沒有人說話,只聞起起伏伏的呼吸聲。
懷歆發著呆,斜靠在沙發扶手,有點怔忡。
好半晌,那頭才傳來些靜。
“Lisa。”
郁承的嗓音有些啞了,可卻還是那麼好聽。
在此之前懷歆沒想過隨口胡謅的一個名字從他口中念出會是這樣的直達心靈。
“什麼?”也就跟著喃喃。
靈魂還漂浮在半空中。
“你真Lisa麼。”
Advertisement
這問句如當頭一棒讓懷歆清醒了些,但實在讓人措手不及,僅存的時間只夠發出一聲疑問音:“嗯?”
“我是說,你總該有中文名?”郁承頓了頓,低緩溫地問,“你的家人朋友不會也你Lisa吧?”
是調侃的一句話,可他沒帶浮笑的語氣。平靜的敘述,難得讓人有種認真的覺。
“當然——”懷歆咬著,尾音折回來,“不是了。”
終于揚起笑:“那你又真的Alvin嗎。”
仿佛有一弦在空中崩斷,不過安靜須臾,郁承輕淺的音從聽筒中傳來:“真的。”
“這樣哦。”懷歆眨著眼道,“那看來我們對彼此都很坦誠嘛。”
“是啊。”他嘆一聲,像是在悠悠地笑。
“……你過年有什麼安排?”擔心這話題轉移過度太生,懷歆補充了很多細節,“我學生剛放寒假,現在都在計劃要出去玩呢。剛還跟我打電話說課不上了。”
“是麼。”
郁承是個紳士。不管是否察覺到的意圖,都順著話往下講,“今年春節應該不一樣的。”
懷歆以為他說的是許久未遇的寒,附和道:“是得多加幾件服,別凍冒了。”
他緒不明地唔了聲,有思忖的意味。
“上次你說,計劃寒假去哪里旅游?”
“稻城亞丁。”懷歆道,“先從都開始,途經康定、新都橋和理塘,繞到亞丁那頭,最后再回都。”
“什麼時候出發?”
“不出意外的話是1月26日。”
“那還有一兩周。”
“嗯。”
頓一下,玩笑似地問:“問這麼詳細,是想和我一起去啊?”
郁承淡淡地笑,明顯沒把的話放在心上:“說不定呢。”
懷歆篤定了自己是在安全范圍活,刻意道:“你要真想來也沒事,我不介意尋找靈的旅途中多一位長得好看又會聊天的同伴。”
“你一個人去麼。”
懷歆有的時候是很喜歡他這種從不直給的虛與委蛇的,曖昧地模糊了重點,雙方都進退有度。
“是啊。”拉長語調。
“以前都是一個人嗎?”郁承漫不經意地問,“去那些荒郊野嶺的地方,也沒帶個男伴?”
“沒有誒。”
“不害怕?”
“怕是有點怕的,一開始。”懷歆倒也坦誠的,“但是次數多了就好了。很多地方民風淳樸,沒有想象中那麼危險。”
“這種事本來也是邁開第一步最難。但真正出去之后,你會發現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太值得了,只有自己,和自然的呼喚共鳴,千金難買。”
“……”
懷歆不過稍一停歇,又開始懶散起來:“更何況,我實在是想不出邊哪位帥哥應得這個和本人同游的榮機會。”
隔著話筒,郁承聽到幽幽地吐氣,問:“怎麼?你想當我的第一個男伴嗎?”
像是卡薩布蘭卡百合開花的聲音,甜膩而艷麗。
“……”
郁承笑了下。
張揚直白又有些目中無人,還是小孩,僅是呈口舌之快就得意地忘乎所以。
他也不能總做紳士。
“在向我邀約之前,你要考慮清楚。”郁承勾,屈指輕叩了下桌子,如警告也似提醒,“到時候我就不會只知道你的名字是Lisa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38 章
新婚嬌妻寵上癮
(桃花香)一場陰謀算計,她成為他的沖喜新娘,原以為是要嫁給一個糟老頭,沒想到新婚之夜,糟老頭秒變高顏值帥氣大總裁,腰不酸了,氣不喘了,夜夜春宵不早朝!「老婆,我們該生二胎了……」她怒而掀桌:「騙子!大騙子!說好的守寡放浪養小白臉呢?」——前半生所有的倒黴,都是為了積攢運氣遇到你。
245.9萬字8 30971 -
完結256 章

別和我撒嬌
痞帥浪子✖️乖軟甜妹,周景肆曾在數學書裏發現一封粉色的情書。 小姑娘字跡娟秀,筆畫間靦腆青澀,情書的內容很短,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 “今天見到你, 忽然很想帶你去可可西里看看海。” …… 溫紓這輩子做過兩件出格的事。 一是她年少時寫過一封情書,但沒署名。 二是暗戀周景肆六年,然後咬着牙復讀一年,考上跟他同一所大學。 她不聰明,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認識溫紓的人都說她性子內斂,漂亮是漂亮,卻如同冬日山間的一捧冰雪,溫和而疏冷。 只有周景肆知道,疏冷不過是她的保護色,少女膽怯又警惕,會在霧濛濛的清晨蹲在街邊喂學校的流浪貓。 他親眼目睹溫紓陷入夢魘時的恐懼無助。 見過她酒後抓着他衣袖,杏眼溼漉,難過的彷彿失去全世界。 少女眼睫輕顫着向他訴說情意,嗓音柔軟無助,哽咽的字不成句:“我、我回頭了,可他就是很好啊……” 他不好。 周景肆鬼使神差的想,原來是她。 一朝淪陷,無可救藥。 後來,他帶她去看“可可西里”的海,爲她單膝下跪,在少女眼眶微紅的注視下輕輕吻上她的無名指。 二十二歲清晨牽着她的手,去民政局蓋下豔紅的婚章。 #經年,她一眼望到盡頭,於此終得以窺見天光
45.4萬字8 21446 -
完結1693 章

離職后我懷了前上司的孩子
作為總裁首席秘書,衛顏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號稱業界楷模。 然而卻一不小心,懷了上司的孩子! 為了保住崽崽,她故意作天作地,終于讓冷血魔王把自己給踹了! 正當她馬不停蹄,帶娃跑路時,魔王回過神來,又將她逮了回去! 衛顏,怒:“我辭職了!姑奶奶不伺候了!” 冷夜霆看看她,再看看她懷里的小奶團子:“那換我來伺候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165.2萬字8.18 38138 -
完結201 章

雙時空緝兇
【01】南牧很小的時候就遇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他:絕對不要和溫秒成為朋友。 日長天久,在他快要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女生,那個女生叫做:溫秒。 【02】 比天才少女溫秒斬獲國內物理學最高獎項更令人震驚的是,她像小白鼠一樣被人殺害在生物科研室,連頭顱都被切開。
38萬字8 179 -
完結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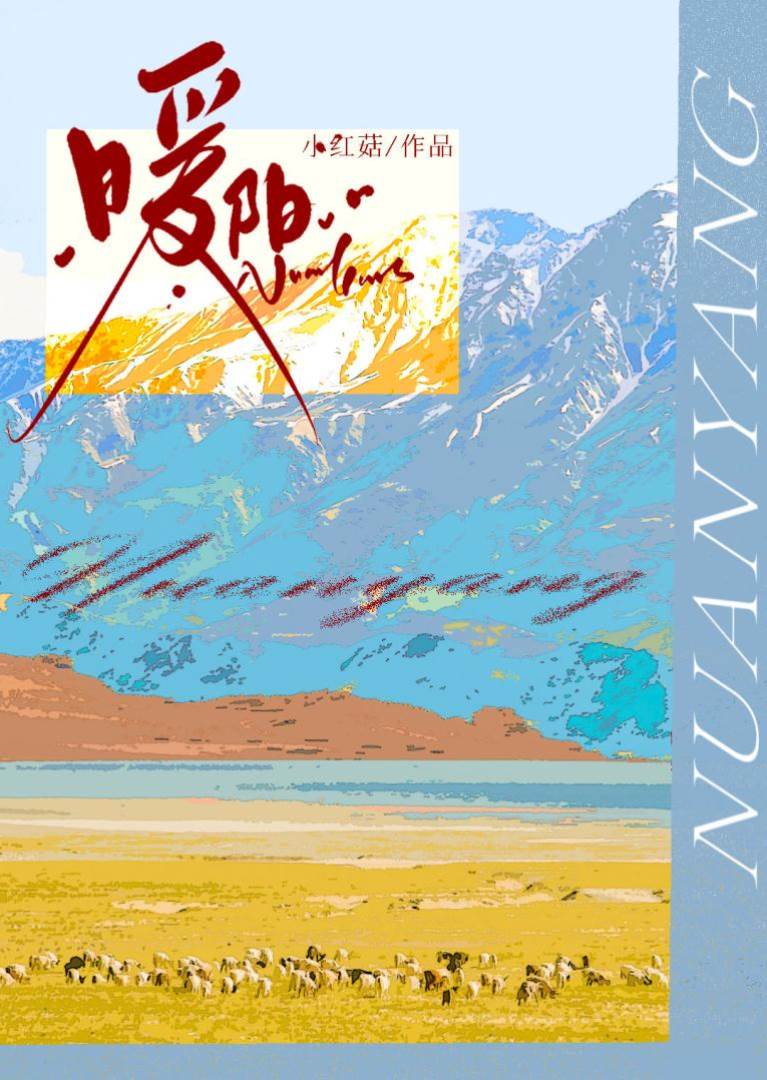
暖陽[先婚後愛]
文冉和丈夫是相親結婚,丈夫是個成熟穩重的人。 她一直以爲丈夫的感情是含蓄的,雖然他們結婚這麼久,他從來沒有說過愛,但是文冉覺得丈夫是愛她的。 他很溫柔,穩重,對她也很好,文冉覺得自己很幸福。 可是無意中發現的一本舊日記,上面是丈夫的字跡,卻讓她見識到了丈夫不一樣的個性。 原來他曾經也有個那麼喜歡的人,也曾熱情陽光。 她曾經還暗自竊喜,那麼優秀的丈夫與平凡普通的她在一起,肯定是被她吸引。 現在她卻無法肯定,也許僅僅只是因爲合適罷了。 放手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 *** 我的妻子好像有祕密,但是她不想讓我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他有點緊張,總覺得她好像在密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卻無法探尋。 有一天 妻子只留下了一封信,說她想要出去走走,張宇桉卻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讓她輕易地將他拋下。 張宇桉現在只想讓她快些回來,讓他能好好愛她! *** 小吳護士: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張醫生不正常。 小王護士:對,他以前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發朋友圈的,現在每隔幾天我都能看到他發的朋友圈。 小吳護士:今天他還發了自己一臉滄桑在門診部看診的照片,完全不像以前的他。 小劉護士: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張醫生在暗搓搓賣慘,應該是想要勾起某個人的同情。 小王護士:難道是小文姐?聽說小文姐出去旅遊了,一直還沒回來。 小劉護士:肯定是,男人總是這樣的,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纔會追悔莫及。
22.5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