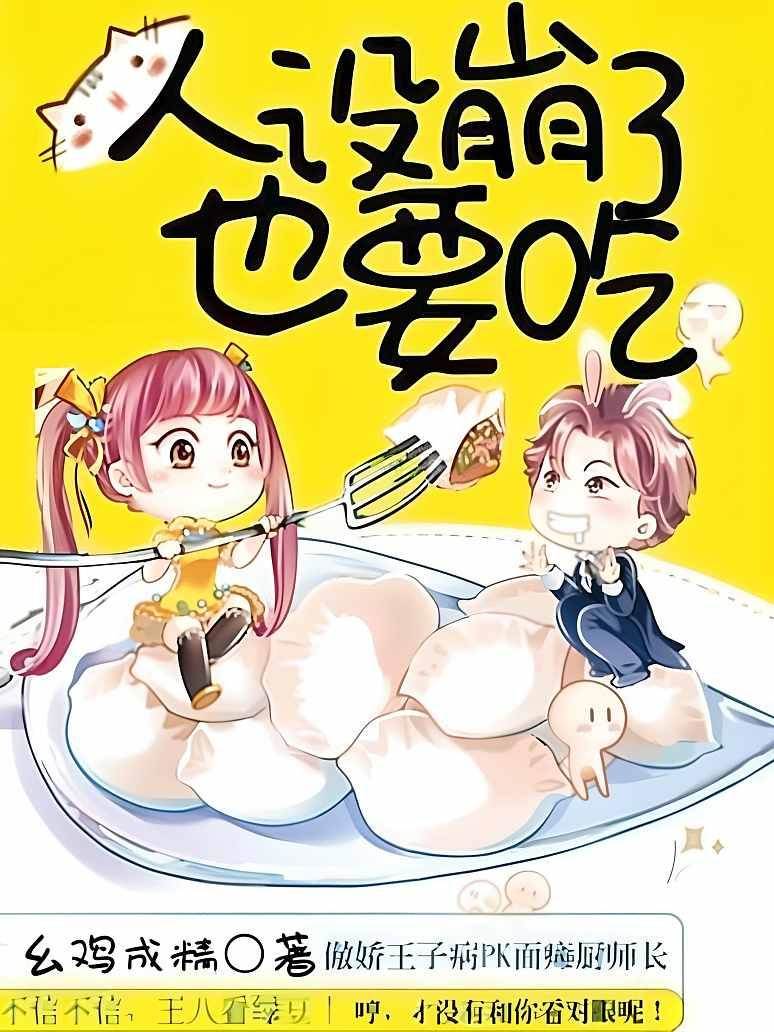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心跳陷阱》 第13章 第13章
林綿看到這行字,懊惱的不知道怎麼才好。
不過隨手發錯了圖片,江聿是發散思維怎麼猶如韁野馬,一頓拳打來——
林綿枯坐了一會兒,覺著不能就這麼占下風。
撈起手機,指尖在屏幕上輕點。
林綿:【你不是在喝酒嗎,怎麼還能管這麼寬。】
發完,揚起脖頸,重新拿起筆標記劇本。
江聿可能是被噎到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靜。
“滴滴——”
安靜的室想起突兀的開門聲。
林綿剛從浴室出來,淡淡的眼眸看向門口,作有一秒的遲鈍。
江聿推門進來,同時玄關燈帶被他按亮。
燈傾瀉,他上被描摹一圈和暈。
林綿薄溢出不太友好的問候:“你怎麼回來了?”
江聿角玩出淺淺弧度,他慢條斯理的掉外套,單手握著領帶用力拽了拽,原本板正的領帶,松垮凌地掛在脖頸間。
領敞開,結松開舒服,出脖頸小片,頗有幾分斯文敗類的模樣。
即便穿上這樣的服,偽裝外貌,但林綿過他最純粹的靈魂——不羈無拘無束。
他是一陣風,又是一朵云。
踩風來,隨風去。
他的靈魂是自由的,珍貴的,而不應該被西裝革履的裝扮束縛。
江聿晃去廚房給自己倒了一杯水,鋒利的結隨著吞咽鼓,他靠在中島看向過去,客廳一頂釣魚燈,一束暖黃燈直直打在臉頰,眼底氣未散水盈盈的,頭發半干窩在肩頭,看樣子只是匆匆吹了一下。
睡調偏淺,像是自帶濾鏡,不余力地飾的清冷漂亮。
“太太盛難卻,我要早些回來,豈不是不識抬舉。”他輕扯角,回答的問題。
Advertisement
“那個圖我發錯了。”林綿糾正他。
江聿抿了口水,嗓子浸潤的清冽稍揚,嗤了一聲,“嗯,你偏偏就錯發給我了。”
他拖著漫不經心的語調,林綿還是聽出了奚落。
“我真的只是發錯了。”
江聿深深看著,似乎在審視說的是真是假,幾秒后,他牽薄,語調下沉:“那你原本打算發給誰?”
林綿坦白:“黎漾。我閨。”
江聿覺著名字悉,在腦子過了一遍,想起黎漾是喻琛那死對頭發小。
慢悠悠飲完最后一口水,也像是將沒來由的壞緒平息,他不不慢地來到邊。
“手給我看看。”他一進門就注意到拆了紗布,水泡消掉后痕跡很明顯。
林綿以為他要追究,“沒事了。”
江聿有時候強勢,比如此刻,他不會聽取林綿一面之詞,“林綿,你說謊的樣子還是很拙劣。”
他牽牽起手,左右檢查了一下,忽地蹙眉看:“暫時還是不要水。”
這次,他沒用紗布,找了枚防水創可上,瞥見半干的頭發,他拿過吹風筒,連上座。
林綿被他的舉弄得不知所措,他們關系不尷不尬,但也沒還沒到讓對方吹頭發。
想手拿回來,江聿偏頭避開,勾著,像是在挑釁:你怕嗎?
“坐好。”
“我自己來。”
江聿沉默反倒變得強勢。
林綿害怕他這種稔的親,呼呼地熱風拂在耳側,順著耳朵涌進大腦里一樣,意識變得恍惚。
閉上眼就能回到三年前,被江聿抱著坐在洗漱臺,握著牙刷幫江聿刷牙,江聿赤著上半,站在跟前,握著吹風筒,耐心地給吹頭發。
牙膏泡沫弄到了角,江聿只會笑,按住頭頂輕晃。
Advertisement
一睜眼,畫面與過去重合。
他站著,燈照亮他半個肩膀,他垂著眼睫,神專注,即便善于偽裝,可他的骨子里矜傲,還是通過細枝末節展幾分。
耳廓被指尖了一下,輕輕抖,小心避開。
頂傳來懶散嗓調,像是被熱風吹過一般,燎人:“你的耳朵怎麼紅了?”
林綿睫輕泄的張,推開吹風機,“好了。不用吹了。”
江聿關掉吹風機,回林綿手里。
滾燙的機還纏綿著江聿的手心的溫度。
出于禮貌,也帶著劃清界限的目的,淡聲道:“謝謝——”
江聿輕哂一聲,不接的道謝,轉回臥室。
林綿猜測他洗澡去了,在客廳多磨蹭了會兒,才慢吞吞收拾劇本回臥室。
避免在床上不聊天的尷尬,決定在床上看會兒劇本。
推開門進去時,江聿已經洗漱完,靠在床頭支起一條,拿著的平板上顯示麻麻的字,估計是在看文件。
然而下一秒,林綿就被他旁邊枕頭上放置的兩張票吸引視線。
“你弄來的票?”林綿不可思議地捧著話劇票。
這場的票早售空了,正發愁找什麼渠道買票,沒想到不過半天,票就躺到了的枕頭上。
江聿從平板抬起視線,轉過臉,語調輕松隨意:“不然呢?”
“多錢,你能不能賣給我?”林綿輕聲跟他商量。
江聿略不爽地抬頭看向,順手走兩張票,清冽冷漠:“不賣。”
他將兩張票放回床頭柜,然后繼續看文件。
與心心念念的失之臂,林綿到憾,但有什麼辦法呢,那票是江聿的,他不賣,也不能強買。
含著失落緒,林綿做了個不太好的夢,以至于一上午緒都不太高。
Advertisement
黎漾興高采烈通知生日會地址。
林綿打開擴音放到沙發上,支著頭心不在焉地嗯了一聲,又聽黎漾說“可以帶家屬”瞬間否決了這個提議。
黎漾聽出端倪,調侃:“喲,這是新婚夫妻吵架了?”
林綿否認,那不算吵架。
“我早說了,你們不和諧,早晚要出事。”黎漾用詞大膽,“要我說,你先爽了再說,三年前你都會,三年后你怎麼慫了?”
林綿抿,阻止繼續胡說。
黎漾只當害,故意用夸張的語氣說:“綿綿沖鴨!拿下江聿!”
一道清列玩味的嗓音突然闖耳朵:“拿下誰?”
林綿轉頭臉,與扶著門的江聿視線相,眸閃了一下,作很快地按滅了黎漾的電話。
黎漾估計是聽見了什麼,回撥了過來。
林綿沒敢接,任由手機振。
江聿來到邊,抬抬下示意:“怎麼不接,讓我聽聽你準備拿下誰?”
林綿良好的職業功底讓一點也不怯場,清冷漂亮的臉上從容鎮定,牽紅,“你聽錯了。”
“是嗎?”江聿玩味地提了提角。
“你不用去公司嗎?”看著他返回臥室,很快又折返。
兩張話劇的票輕輕落在手心,江聿淺瞳仁靠近,清冽的香氣快速占據的呼吸,耳廓被熱氣,往后退。
下一秒,被江聿握著手肘抓回來,聲音靠的很近,“這就給你一個機會搞定我。”
還祈禱江聿剛進門,什麼都沒聽見,沒想到黎漾的話全被他聽見了,林綿尷尬地別開視線。
“江聿——”
“你離太近了。”
本以為江聿會為難,沒想到他一聲不吭退開,垂眸看了一眼腕表,啟催促:“還有一個小時停止場,你到底要不要去?”
Advertisement
哪有放著門票不去的道理,林綿做不出暴殄天的事,所以不用考慮,已經和江聿坐在了劇場。
江聿這兩張位置相當有約,劇場的二樓的貴賓間,隔著一堵玻璃墻,能將場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來時,劇場的人親自接待的,順著電梯直接上樓,途中保極強。
工作人員離開,林綿指尖勾著口罩摘下來,直直地看向舞臺。
江聿對話劇天生不興趣,開場半個小時,他便沒骨頭似的窩在沙發里,低頭玩手機。
偶爾抬眸,能看見林綿角浮起淺笑,亦或者跟著劇,無聲落淚。
真有這麼好看嗎?
江聿放下手機,坐直了,手肘支在沙發上,重新看向舞臺。
劇進行到一對深的人因為戰爭要分別,兩人在站臺擁抱接吻,燈昏暗,緒飽滿滾燙。
江聿心臟被牽了一下。
他轉過臉看向林綿,眼角的,泛著薄薄水,可見是為熱分別而落淚。
“林綿——”
林綿陷在緒里,悲傷席卷了大腦,連聽覺也遲鈍了半拍。
“你當初為什麼不辭而別?”
江聿的嗓音輕輕敲在神經上,似乎是在意志力薄弱的時候深究真相。林綿的心臟跟著收,呼吸變得不平穩,但表面仍舊佯裝鎮定。
目向舞臺,眼神有些放空——
“沒有為什麼。”
江聿收回目,隨之暗淡,他重新將視線投回屏幕,眉頭始終蹙著。
后半場,劇可能太,林綿一直無聲流淚,燈照片半張側臉,眼淚晶瑩剔,江聿放下手機,盯著看了幾秒。
有的人連哭都像仙,漂亮的像一幅畫。
江聿了紙按在眼角,不輕不重地拭走眼淚,“你哭過嗎?”
當初離開時像話劇的主人公那樣不舍嗎?
會落淚嗎?
林綿意識到失態,眨著紅的眼睛,“我去洗手間。”
剛起,手腕倏地被扣住,溫熱的溫織,被力道帶著穩穩坐在江聿面上,耳畔拂來他低聲含糊的語調,“別去了。”
林綿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眼睛被溫熱的掌心蓋住,男人薄微涼,輕而易舉捕獲的,清淺的薄荷強勢占據呼吸。
驀地睜大了眼睛。
本能地想推開,卻被牢牢扣住后頸。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155 章
她不乖!要哄
【爆甜輕松 雙潔治愈 野性甜寵 校園】【嬌縱隨性大小姐x邪妄傲嬌野少爺】“疼!你別碰我了……”季書怡微紅的眼圈濕霧霧的瞪著頭頂的‘大狼狗’,幽怨的吸了吸鼻子:“你就會欺負我!”都說京大法學系的江丞,眼高于頂邪妄毒舌,從不屑與任何人打交道,只有季書怡知道背地里他是怎樣誘哄著把她藏在少年寬大的外套下吻的難舍難分。開學第一天,季書怡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惹了江丞不爽。所有人都以為她要完。可后來眾人看到的是,大魔王為愛低頭的輕哄:“小祖宗,哪又惹你不高興了?”季書怡永遠記得那個夜晚,尋遍了世界來哄她的江丞跪在滿地荊棘玫瑰的雪夜里,放下一身傲骨眉眼間染盡了卑微,望著站在燈光下的她小心翼翼的開口:“美麗的仙女請求讓我這愚蠢的凡人許個愿吧。”她仰著下巴,高高在上:“仙女準你先說說看。”他說:“想哄你……一輩子。”那個雪夜,江丞背著她走了很遠很遠,在他背上嬌怨:“你以后不許欺負我。”“好,不欺負。”——————如果可以預見未來,當初一定不欺負你,從此只為你一人時刻破例。你如星辰落入人間,是我猝不及防的心動。
24.2萬字8 17171 -
完結1206 章

相親當天,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甜寵+先婚后愛+傲嬌男主】 相親當天就鬧了個大烏龍,安淺嫁錯人了。 不過,錯有錯著,本以為一場誤會的閃婚會讓兩人相敬如賓到離婚,安淺卻驚訝地發現婚后生活別有洞天。 她遇到刁難,他出面擺平。 她遇到不公對待,他出面維護。 安淺天真的以為自己嫁了個錦鯉老公,讓她轉運,卻萬萬沒想到,自己嫁的竟然是億萬富翁!
192萬字8.18 17167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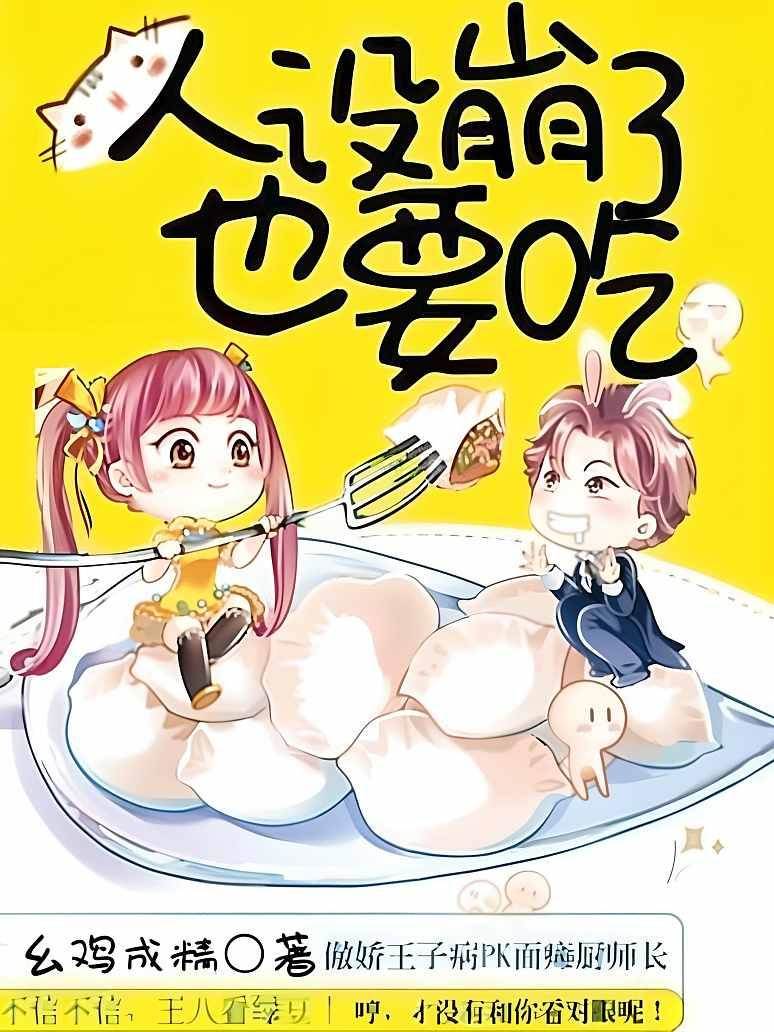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