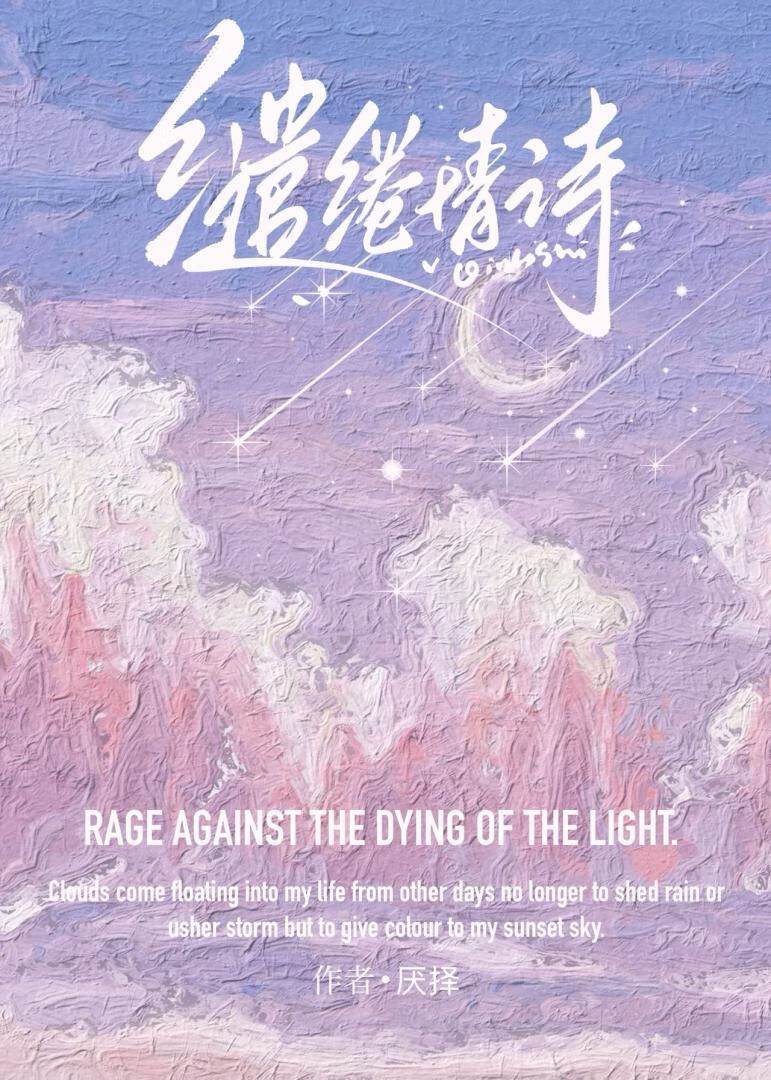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親昵》 第24章
特種軍的素質常人沒法兒比, 服藥拉通睡一宿,次日,秦崢便完全恢復。
六月份,空氣里的燥氣更重,宿舍院兒里, 蟬鳴一陣接一陣,日頭火辣辣的, 溫度接近三十一。
他著膀子躺床上,須臾, 點了煙, 面無表, 左手無意識地把玩那個浮雕打火機。
蓋帽兒甩開,扣上, 扣上, 甩開,往復循環, 脆響叮叮。
不知過了多久,秦崢仰頭, 濃白煙霧從鼻腔里呼出, 彌散在眼前。視野模糊了, 所有景都似隔了層輕薄白紗, 他目冷靜,穿濃煙落在未知的遠。
這個火機是別人送他的,算生日禮。
Zippo簡單的一款, 不貴,也沒什麼特。可一晃多年,他幾乎從沒離過。
良久,煙盒空了,煙灰缸滿了,秦崢的神思徹底清明,翻坐起,隨手套上件軍用背心下了床。
中午景,有人家開始搗騰午飯,飯菜香味飄得滿院兒都是。他走到客廳,余掃見飯桌上擺著的東西,瞇了瞇眼,緩慢踱過去。
兩個煎蛋,一份三明治。
秦崢在原地站片刻,手背了下碗沿,溫度冰涼,顯然,準備這些的人早已離開許久。側目,又注意到裝蛋的碟子底下還著張紙條,拿起來一看,寫著:粥在鍋里,我熬的,早說不是難事兒了吧。
窗外風在吹,飯菜的香味兒送進來,愈發濃,夾雜鍋鏟翻炒的約聲響。
這些配桌上的早餐,很居家平常的一幕,于秦崢而言卻陌生。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日子對分作兩半,一半兒在山里練兵,一半兒在各地出任務,營地,戰地,食堂,宿舍,嚴謹規律,單調充實。而在自家吃飯的機會,細想來,竟幾近于無。
Advertisement
秦崢垂眸,指肚刮過紙面上的那行娟秀小字,眉峰斜挑。
隔著紙他都能想象那人得意洋洋的模樣兒。
小東西。
須臾,他拿起那塊兒冷的三明治,剛送到邊兒,大門被人從外敲響,“砰砰砰”。
秦崢作稍頓,“誰?”
門外響起一道嗓音,輕聲的,和的,屬于一個人:“是我。”
他擰眉,咬了口三明治,過去開門。
門開了。
秦崢沒什麼語氣:“有事?”
屋外,軍裝筆的軍端然站立,白瘦高挑,氣質極佳。軍營是最磨煉人的地方,從軍的人,無論男都自帶氣場,可卻刻意收斂了幾分英氣,溫婉擔憂,“崢哥,你好些了麼?”
秦崢極其疏離,“沒事兒了。”
陳梳揚起角,“你沒事兒就好,我還擔心你一個人在家沒人照顧,會不會出什麼問題呢……”說著頓住,忽然想起什麼,“哦對了,給你的藥你收到了麼?”
秦崢靜了靜,想起那袋兒被余兮兮得稀爛再扔掉的東西,點了下頭,“嗯。”
陳梳笑,“收到了就好。”稍停,語氣里多了一試探意味:“昨晚我來找過你,你不在,所以我就把給你帶的藥給了余兮兮,請轉來著……”
他面無表地打斷:“你來這兒找我,什麼事?”
“……”陳梳笑容一僵,有些尷尬:“其實,其實也沒什麼事。昨天你不是淋雨了麼,我來看看你。”
秦崢目冷淡掃過的臉,“謝謝組織關心。現在是工作時間,尉回去吧。”
陳梳說:“中午有兩小時午休。”
“所以陳尉沒別的事兒干?”
“……”
這道逐客令很直接,一點兒也不婉轉。陳梳皺了皺眉,不甘心就這樣回去,于是道:“你應該還沒吃午飯?要不,我陪你下樓隨便吃點兒吧。”
Advertisement
“不用。”那男人隨意抬了抬手,拒絕得很干脆,“有吃的。”
陳梳視線掃過去,見他手上拿個三明治,有點無語,“就吃這個麼?”
“鍋里還熬了粥。”
陳梳抿。
這人說話不給人留后路,也不顧及一人的面子,實在過分。可轉念一想,他們認識多年,秦崢倒一直都是副拒人千里的冷漠子,并不只針對誰,于是只好嘆了口氣,“好吧。”又半開玩笑道:“我大老遠來看你,秦校都不請我進去喝杯茶麼?”
秦崢說:“不好。”
一來二去,全是拿熱臉冷腚,陳梳也覺得沒意思了,點點頭,“行,那我走了。”說完,轉下樓梯。
秦崢卻忽道:“陳梳。”
角勾了勾,站在樓道上,回頭挑眉,“怎麼了?”
他臉上的神冷漠:“以后有事兒在單位上找我,別上這兒。”手指了下樓上,面無表,語氣極淡,“我那媳婦兒得很,怕誤會。”
話音落地,陳梳臉上的神瞬間大變,幾乎不可置信:“……你媳婦兒?”
“嗯。”
陳梳靜默,遲疑道:“余兮兮麼?”
“對。”
聞言,怔怔失神,低下頭,忽然笑出一聲來,意料之外又意料之外。一面覺得驚訝,一面又覺自己可笑。過去數年,對他一直有好,雖明知他有“未婚妻”,但卻一直抱存僥幸心理:娃娃親訂下的婚約,哪個年人會真當回事?
腦海中浮現出一個人影,纖細窈窕,白艷,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那種和軍的颯爽截然不同,弱,氣,張揚明。秦崢被吸引,似乎也在理之中,畢竟男人的好奇心重,總喜歡接近與自己完全相反的事。
Advertisement
新鮮作祟罷了。
秦崢什麼人,一個空有臉蛋的富二代,拿什麼跟他比肩?
“……”陳梳側頭,深吸一口氣吐出來,笑笑,“嗯,你說的我都明白了。聽政委說,新的任命文件已經下來了,這周之應該就會派你去石川峽。好好休息吧。”
話說完,士軍靴帶起的腳步聲漸行漸遠。
整個世界安靜下來。
秦崢臉上淡淡的,把剩下的三明治全塞里,左腮鼓起,咀嚼,漆黑眼底沒有一波瀾。
石川峽,云城軍區特種大隊“拂曉”的駐地。
安逸日子過了那麼久,也是時候回他該回的地方了。
余兮兮今天有些倒霉。
昨晚一夜未眠,今早不到六點就起來了,想起昨晚拿了秦崢的鑰匙還沒還,于是下樓還鑰匙;還完之后見時間還早,干脆又順手給那“病人”準備了份早餐。
煎蛋的時候,滾油濺在手背上,起了個水泡,火燒火辣地疼。無語,隨便了點牙膏抹上,然后便出門上班。今天周四,云城某區開招商會,各都堵得水泄不通,因此坐地鐵的人比往常多了一倍,頭趟地鐵沒上去,到基地時已經遲到二十分鐘。
好巧不巧,之前主任剛好來科室找余兮兮要資料,轉一圈兒沒見著人。
然后,余兮兮就挨了頓批。
一上午過去,余兮兮的心有些郁悶。中午12點多,廣播里開始放下班音樂,拿上飯卡準備去食堂,門外一個聲音響起,問:“余醫生,吃飯不?”
抬頭,見是李和另外幾個認識的軍犬兵。
出笑容,“剛準備去呢。”
李說:“正好,一起吧。”
余兮兮應了聲兒,關完電腦起走出,和幾個年輕士兵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
Advertisement
“來辦事兒麼?”
“嗯。”李點頭,語氣稀松平常,“山狼的責任醫師不是要換你麼?我來辦公室找點兒它的資料。”
“……”余兮兮當即愣住,半天才說:“山狼的責任醫師要換我?什麼時候的事兒,我怎麼不知道啊。”
李笑了下,“剛下來的消息,你們主任估計還沒來得及找你。”
“真的假的?”
邊兒上一個小戰士接話,“當然是真的。山狼是有一等功的軍犬,更換責任醫師可是大事兒,要出紅頭文件的,李能拿這個開玩笑?”
余兮兮皺起眉,覺得有些不對勁,“可是我才剛來幾天,都還沒轉正,按理說沒資格負責犬只吧。”更何況,還是山狼這種重點軍功犬。
那小戰士說:“這就不太清楚了。不過文件一下來,咱服從命令就好,至于首長們怎麼安排就不是咱們能過問的了。”
余兮兮說:“但也不能糊里糊涂的吧。”
聞言,李在邊兒上笑起來,著嗓子道:“你要真想弄明白,干脆問問秦營長去。”
“……”余兮兮眸一閃,然后抿了抿。
秦崢?
怎麼差點兒把他忘了。
昨晚那人高燒沉睡,直到今早走的時候都還沒醒,也不知道現在起床了沒?病怎麼樣了?
琢磨著,余兮兮從兜里出手機,略略遲疑,然后撥出去一個號碼。
幾秒鐘后,接通。
一貫低沉的嗓音從聽筒里傳出,慵懶隨意:“怎麼?”
心跳莫名加快,清清嗓子,道:“嗯,那個,你……你起床沒有?”
“嗯。”
“那,”輕輕咬瓣兒,“頭還疼麼?”
“好差不多了。”
“留的東西吃了麼?”
“嗯,味道不錯。”那人隨口應著,又低聲笑,“你第一次熬粥,這水平還可以。”
聞言,余兮兮有點兒得意,輕哼了聲:“也不是什麼難事兒。”
那頭,秦崢勾角,掃一眼外面兒的太,“這會兒干嘛呢。”
說:“哦,準備去食堂吃午飯了。”
“一個人?”
“唔……”余兮兮看了眼旁邊的幾個同路戰士,答:“不是,還有李和另幾個同志。”
臥室的窗簾朝兩邊兒大開,旭日暖傾瀉進來,照在秦崢上。他角掛一抹寡淡隨意的弧,彎腰,把各式軍刀匕首裝進行李箱,換了只手拿手機,“多吃點兒飯。”
“哈?”不解。
秦崢的語氣淡:“你太瘦,不好。”腰那麼細生生的一條兒,又又弱不風,每回抱他都不敢用力氣,生怕掐斷。
臉微紅,小聲嘀咕地爭辯:“……我吃得也不吧。當每個人都和你一樣麼?飯量能頂頭熊。”
電話那邊兒,秦崢瞇了下眼:“你說什麼?”
“哦,”余兮兮若無其事地答話,嗓門兒別提多洪亮:“我說我爭取多吃點兒,長一頭熊。”
秦崢:“……”
旁邊幾個戰士:“……”
說著話,一抬頭已經到食堂門口。于是清了清嗓子,接著道:“好了,我要吃飯了。要沒什麼事兒就先再見。”
秦崢說:“五點半下班?”
稍頓,點點頭,“嗯。怎麼?”
他出煙叼里,點燃,挨個兒給那些軍刀抹刀油,作隨意卻利落,極有章法,“我忙完來接你。”
余兮兮眸閃爍,連忙說:“不用了,我坐地鐵就……”
秦崢像沒聽見,淡淡的,“別跑,嗯?”
兩手絞服下擺,半晌,輕聲應了:“……好吧。”
他勾,“乖。”
“……”
“行了。去吃飯吧。”
“那……再見。”聲音愈發小。
他沉沉嗓音里多了笑意,“嗯。”
掛斷電話,余兮兮著手機,莫名覺得心跳飛快。李神狐疑地打量,奇了怪了:“余醫生,你跟秦營長打電話呢?”
一下回過神兒,“啊,對。”
李盯著瞧:“你很熱麼?”
“怎麼這樣問?”
李抬手指指,“臉好紅啊。”
“……”余兮兮一滯,用力咳嗽一聲,干笑,“哦,夏天嘛,熱的。嗯……這食堂空調好像壞了啊,呵,我先打飯去了。”說完腳下生風,跑開了。
李困不解,站原地,拿手撓撓后腦勺,咕噥:“空調沒壞,涼快的啊。”
后頭一個圓臉戰士拍他肩,湊上去,“誒,我說對了吧,秦營長和余醫生不錯。”
李皺眉,“怎麼看出來的?”
圓臉戰士翻白眼,“真笨,難怪沒姑娘跟你好。”
李:“……”
下午上班之后,余兮兮果然被主任了過去,說山狼現在的責任醫師手上的犬只太多,經組織研究后,決定把山狼另外幾只退役犬分到手上,希好好努力,認真工作,對軍犬們負責,不辜負基地領導的信任。
余兮兮心頭一喜,“主任放心,我會好好干的!”
五點半左右,衛生隊準時下班。角彎彎,挎著包走出辦公樓,到基地的大門口等秦崢。
沒站多久,汽車引擎聲便從前方傳來了,黑吉普馳視野。
余兮兮拉開車門坐進去,一邊兒哼歌,一邊兒給自己系安全帶。
秦崢點煙,抬眸,從后視鏡里看一眼,“心好?”
點頭,笑盈盈的,“對啊。”
秦崢轉頭,夕的余在側臉上鑲了層邊兒,皮白的緣故,下,細膩得能看清皮下脈絡。在笑,風在耳邊吹拂。
他盯著,手里夾煙,半天都沒一口。
這人像有魔力,一顰一笑都能牽人心。
良久,秦崢收回視線,單手握方向盤把車開進大路,道:“為什麼這麼高興?”
余兮兮說:“基地給我分犬只了。”
他點煙灰,“的確是好事兒。恭喜。”
“……”側目看他,嘀咕:“切。還說我,你不也喜歡裝傻麼。”
秦崢眉峰斜挑:“我裝什麼?”
須臾,余兮兮收斂了笑意,表嚴肅:“我問過李,實習期的助理醫師是不能帶犬的,我是首例。所以,這件事又是你幫的忙,對麼?”
話音落地,他靜了靜,忽然一彎,黑眸直勾勾瞧,半是戲謔半是認真:“是又怎麼樣?想報答我?”
“……”余兮兮默。
“真要報答也行。”他輕佻淡笑,看的目卻再無半分玩味,只余專注深沉,“余兮兮,你很清楚我想要什麼。”
車里忽然安靜下來。
余兮兮無意識地咬瓣兒,良久,清了清嗓子,盡量很平穩地說:“別的不行。但是,我勉強可以考慮……”
后頭話音戛然而止。
突的,不知看到了什麼,臉大變,喊道:“停車!快!快停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91 章
閻王愛上女天師
白梓奚只是隨師父的一個任務,所以去了一個大學。奈何大學太恐怖,宿舍的情殺案,遊泳池裡的毛發,圖書館的黑影……白梓奚表示,這些都不怕。就是覺得身邊的這個學長最可怕。 開始,白梓奚負責捉鬼,學長負責看戲,偶爾幫幫忙;然後,白梓奚還是負責捉鬼,學長開始掐桃花;最後,白梓奚依舊捉鬼,然而某人怒摔板凳,大吼:哪裡來的那麼多爛桃花,連鬼也要來?白梓奚扶腰大笑:誰讓你看戲,不幫忙?
33.8萬字5 34513 -
完結1074 章

我渣了死對頭的哥哥
司西和明七是花城最有名的兩個名媛。兩人是死對頭。司西搶了明七三個男朋友。明七也不甘示弱,趁著酒意,嗶——了司西的哥哥,司南。妹妹欠下的情債,當然應該由哥哥來還。後來,司南忽悠明七:“嫁給我,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子,作為嫂嫂,你管教小姑子,天經地義。讓她叫你嫂子,她不聽話,你打她罵她,名正言順。”明七:“……”好像有道理。司西:“……”她懷疑,自己可能不是哥哥的親妹妹。
90.2萬字8 35281 -
完結462 章

傅爺的王牌傲妻
寧洲城慕家丟失十五年的小女兒找回來了,小千金被接回來的時灰頭土臉,聽說長得還挺醜。 溫黎剛被帶回慕家,就接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告。 慕夫人:記住你的身份,永遠不要想和你姐姐爭什麼,你也爭不過。 慕大少爺:我就只有暖希這麼一個妹妹。 慕家小少爺:土包子,出去說你是我姐都覺得丟人極了。 城內所有的雜誌報紙都在嘲諷,慕家孩子個個優秀,這找回來的女兒可是真是難以形容。 溫黎收拾行李搬出慕家兩個月之後,世界科技大賽在寧洲城舉辦,凌晨四點鐘,她住的街道上滿滿噹噹皆是前來求見的豪車車主。 曾經諷刺的人一片嘩然,誰TM的說這姑娘是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哪個窮鄉僻壤能供出這麼一座大佛來。 兩個月的時間,新聞爆出一張照片,南家養子和慕家找回來的女兒半摟半抱,舉止親暱。 眾人譏諷,這找回來的野丫頭想要飛上枝頭變鳳凰,卻勾搭錯了人。 誰不知道那南家養子可是個沒什麼本事的拖油瓶。 南家晚宴,不計其數的鎂光燈下,南家家主親自上前打開車門,車上下來的人側臉精緻,唇色瀲灩,舉手投足間迷了所有女人的眼。 身著華服的姑娘被他半擁下車,伸出的指尖細白。 “走吧拖油瓶……” 【女主身份複雜,男主隱藏極深,既然是棋逢對手的相遇,怎能不碰出山河破碎的動靜】
176萬字8.46 260012 -
連載120 章

限時閃婚:傅少追妻不要臉
閃婚一個月后的某一晚,他將她封鎖在懷里。她哭:“你這個混蛋!騙子!說好婚后不同房的……”他笑:“我反悔了,你來咬我啊?”從此,他食髓知味,夜夜笙歌……傅言梟,你有錢有權又有顏,可你怎麼就這麼無恥!…
20.6萬字8 11589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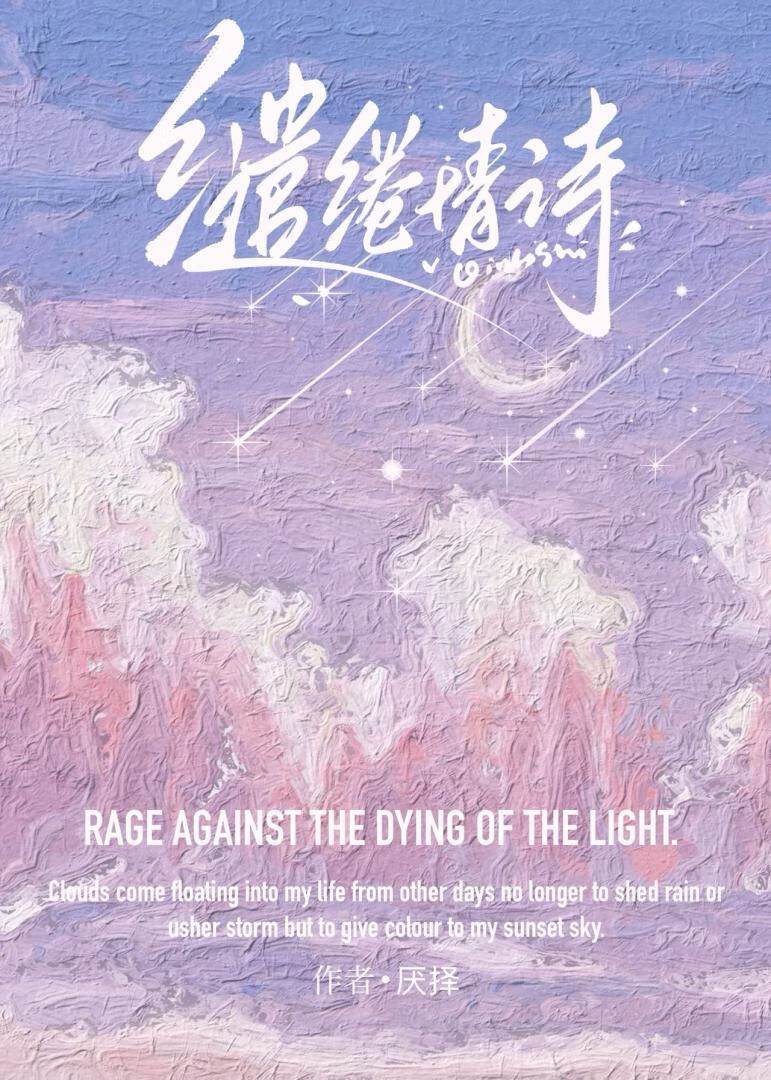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